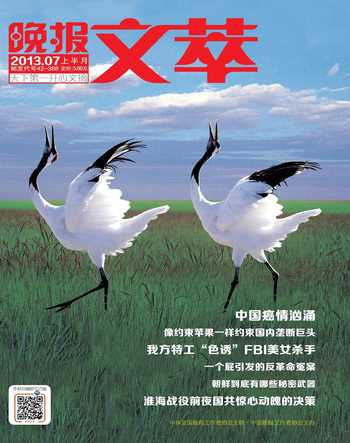有一種死亡不堪祭奠
西風
清明時節,亡靈在世界那頭,我們在世界這頭。我們祭奠亡靈,是補償未盡的緣分。這種祭奠,是讓死亡變得有尊嚴。
但是,有一種死亡不堪祭奠。那就是當死亡在我們看來,充滿著屈辱和殘缺。
湖北巴東,被水泥罐車碾壓致死的44歲農婦張如瓊,那個幾乎被碾碎的軀體,刺痛了我們的眼睛。她是為了自己房屋的權益,與強大的高速公路施工方發生了沖突。她的死亡,在某些人眼里,有點“螳臂當車”的悲劇味。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關注,她可能就像一只被踩死的螞蟻,死得無聲無息,毫無尊嚴。
河南中牟,倔強的農民宋合義也死在高大的鏟車下。他也是因為自己家的承包田被開發商占用,相關的補償沒有談攏,以血肉之軀做抵抗。他哪里是機器的對手?在自己的田里,他用鮮血做了最后的捍衛。
在《新聞1+1》的節目里,主持人白巖松用了一句話表達自己的憤怒:看到開發商笑著談農民死后被檢出酒精含量多少多少,我渾身感到發冷。
白巖松的冷,是對肇事方的冷漠的反應。因為這種冷漠不是沖著其他,而是沖著一條人命。
我們當然也會感到冷。當生命不再具有本質上的至尊價值,當發展的車輪隨意碾壓人的基本尊嚴的時候,我們不禁為死亡如此降臨而悲慟。
這兩起事件間隔不到一周,沖突的模式如出一轍,結局高度相似。都是以死亡為代價,暴露出農地強征的利益分歧。一方以工程正義的名義具有強有力的財富地位和權力背景,一方依托唯一的生存資源企望獲得經濟補償。本來這是一個可以正當博弈的過程,但由于兩者的不平等,最終以奪命來解結。肉體消滅,正在成為一些開發商鋌而走險的“捷徑”。這種危險的邏輯在于:農民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橫豎都不認,哪怕以死相逼。錢,就是他們的命。
對農民生命的輕視乃至怠慢,造成了多起開發悲劇。
但這條暴力開發、草菅人命的道路并未驚醒開發商背后的地方主政者。據報道,盡管肇事者曾稱受人指使,內幕待查,但當地政府都匆匆忙忙進行了“成功”的調解工作,受害者家庭得到了“最高”的賠償。原本悲痛欲絕的家屬竟然一夜之間“諒解”了對方,盡管至今他們也沒有收到一句像樣的道歉。
權力成為“私了”的掮客,生命果然輕易被金錢和權力贖買,死亡在那一刻變得像紙幣一樣的輕薄。九泉之下的張如瓊和宋合義,能否就此瞑目?
政府主導具有高效的和解機制,但在面對民眾生命權的時候,應保持起碼的敬畏。發展確實需要犧牲一些東西,但絕不能拿群眾的軀體作奠基。把奪命之罪當作施工之禍,可能會慫恿那些急功近利的開發商不惜玩弄“死亡游戲”。
如果死亡都不能制止什么,那發展的車輪,還怎么回到正確的軌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