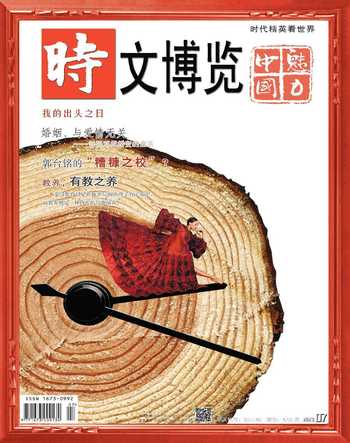內森,你怎么知道的?
蔻蔻梁
One
國家地理的攝影師紅石跟我說:“黃石公園是一個可以去上100次的地方,無論什么季節。”
已經是1月份了,一行人縮著脖子哈著手跺著腳出門,內森和他的妻子卡娜已經如約在門口等待我們。他們穿著厚厚的印第安人的厚呢夾克,戴著毛線的帽子,兩人臉上有一模一樣的淳樸笑容。
他們身后是帶我們出發的小卡車,發動機沒有關,轟隆隆地響著,在雪地里冒著白色的熱氣。內森掏出名片,上面的頭銜很有型:狼跡追蹤者。
今天,這對在黃石公園里土生土長的夫妻負責帶領我們去尋找黃石公園的狼。
進黃石公園不久就看到一群野牛在沒膝的雪地里,艱難地翻找雪地底下的草料。這是它們的艱難季節:草料難尋,氣候惡劣,還得提防灰狼。體格健壯兇猛的野牛在黃石公園什么都不怕,就怕灰狼的聯合作戰。
60多年前,黃石公園的狼太多,野牛瀕臨滅絕。因為名聲太差,于是黃石的狼遭到大規模的驅散和射殺。在1884年到1918年間,僅僅蒙大拿州就消滅了8萬只狼。死的死,逃的逃,黃石的狼從此滅絕。
正如笑話里調侃的:如果壞人都死光了,警察就失業了,生物鏈條果然也同樣不可人為干涉。自從沒了狼之后,那些草食性動物簡直在黃石里鬧翻了天,消耗了大量植物資源。而沒了天敵的野牛更得意了,黃石里不夠撒野,就跑到附近私人農場去騷擾,給家畜們帶來大量病菌。沒辦法,公園只好重新引入灰狼。
內森一邊開車,一邊跟我們講述黃石狼的歷史。他的眼睛就像裝了GPS(全球定位系統)一樣,能在廣袤得讓人恐懼的雪地和森林當中指出野牛、麇鹿、狐貍、大角羚羊等動物的蹤跡,然后停下來指給我們看。那感覺就像一個人走進一個1000平方米的大廳,然后指著墻角一處告訴你說:“看,這里有個螞蟻。”
每次他指出遠方有某個動物在活動的時候,我都使勁兒瞇了眼睛去找,最終幾乎都要靠了望遠鏡才能找到他所說的那些動物。
“內森,你怎么做到的?”我放下高倍數望遠鏡,實在沒辦法理解他是怎么發現那只幾乎和巖石顏色一模一樣、臥倒在地的大角羚羊。
他靦腆地說:“這里看起來跟以前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可能會有個動物。”
他妻子看我滿眼疑惑,解釋說,這所謂的“不一樣”指的是:“例如遠處那片雪地里以前只有47個大小不一的石頭,現在有48個了,那個原本不存在的,就是個動物唄。”
對內森來說,黃石的一切都是他家門口的一切,從小看慣了,那些“不同”就像眼睛里揉了沙子,馬上就能感覺到。
Two
車走到一個拐彎處,一個雪堆上站了四五個人,都舉著望遠鏡朝某個方向掃視。領隊是內森的朋友,另外一個狼跡追蹤專家。內森下車和他聊了兩句,招呼我們:“全部下車,架望遠鏡!動作快,小聲,噓!”
我們又緊張又興奮地架起望遠鏡,小心不發出任何聲音,卻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在怕驚動什么,大家都往同一個方向觀看。
“有狼嚎。聽見了嗎?是不同的兩群狼相遇了,在森林那邊。”內森指著三四公里以外的林線說,“別吵,狼很警惕,一點聲響,或者聞到味道不對,立刻就會逃走。”
狼嚎?除了在動畫片和狼人電影里,我從來沒有聽過狼嚎,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啊嗚—”地叫,然后背后升起巨大月亮。
冷風吹得臉都疼,我瞪大了眼睛,把耳朵從帽子的護耳里撈出來聽了半天,什么都沒有。
我們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雪堆上,把眼睛貼在望遠鏡上,胡亂調整焦距,左右亂掃,露著凍得發麻的耳朵,一直等,等了20多分鐘,終于冷得熬不住了。抬頭看看內森,他還在耐心地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動著他的望遠鏡。好半天,終于嘆了口氣說:“太遠了,看不見了。走吧。”
往前走,路邊有條狼狗一樣大小的動物在撕咬一具看起來很新鮮的羚羊尸體。見車過,翻起三角眼,惡狠狠地盯著我們,咬緊口中的尸體,一副對抗但又隨時準備撤退的模樣。
“狼!”我們在車里低聲喊叫起來。內森看都不看,說:“不是,是郊狼。狼根本不可能讓人距離那么近,而且它們要漂亮得多。灰狼高大,健壯,有非常漂亮的毛皮。”
內森描述狼群的時候用的是family(家庭)這個詞語。他說狼一旦選定配偶,一般是終身相伴,可以共同生活10多年,和后代一起組成一個大家庭。每個家庭有一頭母頭狼,它們有自己的領地,有時候黃石的狼也會為了爭地盤而發生口角以及爭斗—“剛才我說有狼嚎,可能就是兩群狼發生了領地之爭。”
Three
途中我們又停下來兩次,又是緊張興奮地架望遠鏡,哆哆嗦嗦地尋找,等待,一次無功而返,另外一次只在望遠鏡里看到幾個比螞蟻還小的黑點。內森說那是狼,雖然我心里認為它可以是任何東西。
“真是無聊的工作啊,尋狼,沒有想象中的刺激呢。”我對內森說,“人家肯尼亞草原上,獅子可是隨便就看到一大群的。”內森只呵呵地笑,說是啊是啊,狼不好追蹤,有時候一整天找不到它們也是常有的事情。
內森是在紐約完成了動物學的博士學位回來的。紐約一點都不值得他懷念嗎?我問內森,一輩子在黃石公園里會不會偶爾也感到寂寞。內森搖搖頭說:“不會。我已經見到足夠多的人了。村子里冬天有800人,夏天到了會有3000人呢。很多朋友,不寂寞的……大城市,啊,真可怕啊。”
到了午飯時間,內森從車的后尾箱搬出兩大箱食物。從餅干到零食,從水果到芝士,林林總總幾乎有40種。為了表達對他的感激,我們把他替我們準備的食物掃蕩得干干凈凈,而他則在一旁為大家架好望遠鏡。
“瞧,三頭小狼。”內森興奮地告訴我們。招呼我們到望遠鏡前看。這次看得清清楚楚的,三頭年輕的小狼,肥嘟嘟、圓滾滾地在雪地上翻滾。中午是一天溫度最高的時候,它們身邊有一具分不清形態的尸體,想必是飽餐過了,進入了玩耍時間。稍遠處是一匹成年的大狼,足有一個成年人的尺寸,懶洋洋地臥著,臉筆直地沖著我們。有好幾次,我十分懷疑它透過望遠鏡看到了我的眼睛。
“它們的媽媽最近才跟它們團聚……她被她自己的妹妹逐出了狼群,霸占了她的狼群和丈夫,還有她的孩子……不過幸好啊,她把它們偷出來了,瞧,它們又團聚了。她多美啊。”內森像講述鄰居家八卦那樣講著這幾匹狼的家長里短。
“內森,你怎么知道它們誰是誰啊?”我忍不住想問,但又收住了口。
我想,黃石公園里長大的內森其實也很難向一群活在鋼筋叢林里的人真正解釋他到底是怎樣跟那些狼交流的,為什么會知道它們的生活和舉動。即便他告訴我說,每天下午三點三刻的時候他會挨個狼群去探訪一次,吃點小鮮肉做下午茶,或者說它們每天傍晚都到村子里和他開個碰頭會,說說次日的行程……我也一定會相信吧。
(選自《如果你在就好了》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