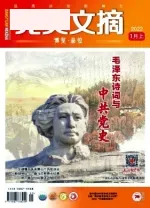愛孩子無需勇氣
原編者按:詩人藍藍不久前發(fā)起了一次網(wǎng)絡教育調查,并給教育部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雖然經(jīng)過一輪網(wǎng)絡和紙媒的集中報道,但仍是無結果。她為什么一個人去進行孤獨的教育調查?請聽聽她“救救孩子”的呼吁——
我為什么給教育部寫公開信
2012年11月19日,我在微博上給教育部發(fā)了一封公開信,敦促改革現(xiàn)行的應試教育體制。我為什么會寫這封信,最早的起因,是十年前我朋友的孩子因為作業(yè)沒有完成,在家上吊自殺,令我震驚且深思。
其后這么多年,經(jīng)常看到中國的學生因為作業(yè)壓力自殺的報道,而且是越來越多。
2011年9月20日,江西九江廬山區(qū)賽陽中心小學三女生孔歡、黃婉婷、王歡,因為作業(yè)太多,不堪重負,手拉手跳樓自殺。有記者采訪被送去醫(yī)院急救后獲救的孩子,問她們?yōu)槭裁匆詺ⅲ⒆诱f:“死了就可以不寫作業(yè)了。”
2012年1月5日,廣州番禺中學高二學生阿梅,疑因作業(yè)常做不完、學習壓力大而跳樓自殺。
2012年3月4日,河南鞏義一中女生倩倩,因為作業(yè)沒完成被罰寫兩千字檢討書,服毒自殺。
2012年6月3日,江蘇無錫初三女生小施跳樓自殺。她的母親陳女士回憶:“女兒對我說的最后的話是,我死也不去上學,我不要罰抄,我不要罰站!”
2012年7月6日,山東青島13歲初一女生孫正雯因為少做了作業(yè),被其父掌摑,跳樓自殺。孫正雯在遺書中寫道:“我死后,請把我的遺體(器官組織均可)捐獻出去,捐給那些需要的人。還有,請把我的壓歲錢捐給山區(qū)的孩子們,讓他們過得好些。再就是我的那些圖書課本也捐了吧,會有人喜歡的。除此之外,把屬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
…………
我在網(wǎng)上搜到的、媒體公開報道的近年因作業(yè)問題自殺學生的信息多達上百條,最小的孩子只有八歲。被老師罰跪不堪受辱自殺,作業(yè)寫不完被親生父親活活溺死,各種慘劇令人毛發(fā)倒豎。
貴州大學法學院李建軍先生在《青少年自殺低齡化的歸因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國每年自殺的兒童約為2580余人,平均每天有七人自殺。其中,學習壓力大占據(jù)兒童自殺原因的第一位。心理學家葉一舵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小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為20.1%,中學生為43.8%,高中生高達52%。
一位資深教育家說:“在教育部門,學生自殺是個忌諱的研究話題。”
那些日子,我深深陷入憤怒和無奈的痛苦之中。
2009年秋天,我和幾位詩人到瑞典參加一個詩歌節(jié)。詩歌節(jié)結束后,我在斯德哥爾摩一位詩人朋友家小住。他們夫婦每天要送兒子去上小學,學校離家很近,步行也就十分鐘。我看到很多孩子在校園里跑著玩,滑滑梯、打球的也不少。我翻看朋友兒子的課本,發(fā)現(xiàn)只有語文最厚,上面全部是童話和故事,圖文并茂。我問語文作業(yè)可有“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朋友哈哈大笑,連連搖頭。
日本NHK電視臺在中國的學校錄制過一個節(jié)目,他們發(fā)現(xiàn),中國初中數(shù)學的課程比日本高中的課程還難。北京一所重點學校的英語老師說,北京中考的英語試卷題型,居然是美國田納西州七年級的英語考題,而人家考的是他們的母語!
我似乎回到做記者時的狀態(tài)
“為什么要布置這么多作業(yè)?”我問一位認識的老師。
“別提了,”她擺擺手,“升學率。你帶的班,考試平均分要排名,升學率要排名。獎金先不說,你知道什么叫績效工資嗎?就是和升學率掛鉤的。領導向你要升學率和考分,你管誰要?還有一個詞兒,叫‘末位淘汰,如果你的課平均考分排在年級最后,你連飯碗都沒有了。”
“為什么要給老師那么大的壓力?”我問一位認識的校長。
“這個呀,”他“嘖”了一聲,嘆息道,“教委一開會,以前是公開給各學校排名,哪所學校升學率高,就排在前頭。現(xiàn)在不公開說了,但表格列在那里,一目了然。你當校長的,領導看著你,你怎么辦?”
“永遠都會有排在最后的。”我說。
“你幼稚了不是,”校長說,“這么跟你說,你這個學區(qū)升學率高,這算是教委、教育局的政績……你還不明白?”
“死了那么多孩子,這也算政績?”我有點兒忍不住。
校長急了,兩手一攤說:“你以為我愿意啊?學生負擔重,說這么多年了,誰能動得了?重點學校都到各個學校初中‘掐尖,把好學生都收了,它們當然永遠是最好的。普通學校怎么能和它們比?有錢的可以拼爹,去重點,沒錢的干瞪眼。教委的頭頭們不是吃干飯的,別看我是一校之長,升學率上不去,被拿下也就一句話。”
那些天,我似乎回到了當年做記者時的狀態(tài),白天出門“采訪”老師、家長,晚上回來抱著電話,“采訪”家長和學生。
一個家長對我說:“我孩子班上有個學生,一進教室就發(fā)抖,精神出問題了。沒辦法,家長領回家,休學。”
有個老師說:“我們學校有個班,走了六個,都去上國際學校了,受不了現(xiàn)在的教育,以后要到國外上學。有兩個學生家庭經(jīng)濟條件不好,人家父母說就是賣房子、借錢也不能讓孩子待在中國受罪了。”
還有一個老師說:“哪個家長不是望子成龍?他們誰不想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布置作業(yè)少了,家長還不愿意!作業(yè)寫不完,打罵孩子的家長有多少?這都是以愛的名義在逼孩子。”
一個大學教授接了我電話后說:“你還關心這事兒啊?你沒看有點兒辦法的家長都把孩子送出去了。別在這兒用孩子的身心健康給應試教育陪葬了,一個字,走!”
一位常年反對教輔的網(wǎng)友說:“教輔公司和教育部門有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聯(lián)系。很多試題超出課本內容,學生不得不去課外班補習。據(jù)說有些考題就是教輔公司的人出的。”
我問過的所有學生都痛恨作業(yè)多,有的孩子甚至說:“我永遠也不會當老師,招人恨!”幾乎絕大多數(shù)家長都叫苦連天,埋怨應試教育帶給孩子的壓力。一些教師更是坦言:“上級向我們要升學率,家長向我們要分數(shù),我們夾在中間怎么辦?”
幾位教育家說:“高考評估制度不改變,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教育行政化不去除,中國教育沒有希望。”
他們尤其強調:教育必須去行政化,這是改變教育現(xiàn)狀的唯一關鍵。
公開信沒有得到回音
下雨了。
站在窗前,
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滴,
慢慢流淌下來,
像一道道淚水。
有誰能知曉這種無可奈何的痛苦?
——我想起了詩人伊凡·哥爾的詩句。
如果說這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那么,投票軟件是否能收集一下全國各地網(wǎng)民的意見?
我想知道,現(xiàn)行的應試教育體制在中國有多少人反對,多少人支持。我絕對不是反對讀書、學習知識,我反對的是現(xiàn)行應試教育非人性的那一部分,違反教育規(guī)律的那一部分。正是這一點導致中國教育“反智化”和“應試”。
2012年11月2日,我第一次找到了微博投票的網(wǎng)址,設置的題目是:“現(xiàn)行教育是愛護學生還是戕害學生”,投票選項分別是:一、呼吁取消應試教育、廢除擇校升學考試、施行12年義務教育制;二、繼續(xù)支持現(xiàn)行教育體制。投票時間為一周。當日22點30分發(fā)出,11月9日22點30分投票結束。
數(shù)據(jù)顯示,有7223位網(wǎng)友參與投票或轉發(fā),其中,97%贊同“呼吁取消應試教育”一項,3%表示繼續(xù)支持現(xiàn)行教育體制。在投票者中,在校學生、家長、一線教師占據(jù)了相當數(shù)量。數(shù)據(jù)說明“應試教育”不得人心,其危害在人們心中引起了廣泛而深重的憤怒。
我抱著不管有多少人參與此事,都會給大家一個交代的想法,在投票一結束,便開始著手起草給教育部的公開信。為什么給教育部寫公開信?我的第一個理由,教育部作為服務全國教育的行政部門,應該對現(xiàn)行教育體制負責任,作為一個公民、納稅人和學生家長,有權利向教育部問責。這么做不是求救于“權力”,恰恰是要教育部把教育的權力放手回歸教育本身。要求教育去行政化,這是公開信的主旨。第二個理由,關鍵詞在“公開”,公開我所知道的事實和我所持的態(tài)度。
由于微博投票,我在網(wǎng)上認識了很多一線教師、教育家,他們深諳教育體制的弊病根源,在我擬公開信的這段時間,給了我非常多寶貴的建議。我曾花很多時間,瀏覽教育部官方網(wǎng)站,認真“學習”各文件內容;也曾將草稿發(fā)給好幾位我信任的教師和教育家,請他們提意見。讓我深感欣慰的是,幾乎所有和我交流溝通的教師、教育家都支持我的看法,有一位教師不但給了我很多建議,甚至愿意和我一起署名。
我從來沒有如此謹慎地寫過稿子——因為事關兩億多兒童,每句話都要有出處、有根據(jù)。前后修改八次,這封公開信才最終定稿。
11月19日上午,我在微博上將這封給教育部的公開信發(fā)出,同時也發(fā)給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員會。
迄今,我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做這樣一件事情難嗎?不,愛孩子無需勇氣。
(摘自《發(fā)現(xiàn)》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