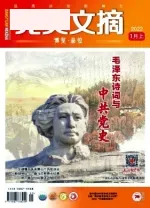影響中國的三次調查研究之風
山旭
“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調查研究無疑是一個極具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詞語。調查研究曾經幫助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革命的任務。而回顧1949年以來的歷史也可以發現,它屢次在緊要關頭幫助執政黨修正自己的失誤,甚至最終促成了改革開放這樣重大的方向轉變。
用“解剖學”反冒進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在1956年前后。自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劃到此時,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55年開始提出新的發展目標,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四十條”中規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務,提前至5年甚至3年內完成。同時,中央對農業合作化、私營經濟改造等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這樣,在高層領導之間出現了后來被稱為冒進與反冒進兩種思路。而其爭論焦點,就是能否完成較高的計劃目標,以及如何評估當時農業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領導們紛紛走出北京。
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陳云在1955年初回到故鄉上海青浦進行調查研究。陳云下火車后直接到村莊里座談,了解到確實存在比較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其原因則是上年統購中購了“過頭糧”,挖了口糧。由此,他向中央建議,糧食統購統銷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力求消滅購“過頭糧”等。
陳云通過與農民和基層干部算細賬,他發現由于國家向農民多征購糧食,農民對糧食統購統銷有顧慮,出現了缺糧農民買糧、不缺糧農民也買糧的情況。他由此采取返還“過頭糧”等修正辦法。
陳云一直很重視調查研究。毛澤東也說,陳云之所以對經濟問題懂得特別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而陳云有一個著名觀點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
調查研究為反冒進提供了有力支持。在黨的八大召開期間,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見《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后收錄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提出,像黨的總書記這樣主要的領導人,要親自動手,了解一兩個農村,爭取一些時間去做。而黨的領導機關,“包括全國性的、省的和縣的負責同志,也要親自調查一兩個農村,解剖一個個‘麻雀,這就叫做‘解剖學”。
調查研究的結論是冒進帶來的負面效果無可辯駁。薄一波后來評價說,“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進,是我們黨依靠集體領導和集體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重大失誤而載入黨的史冊的”。
1961年,調查研究年
1960年夏,農業大幅度減產,而“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中央急需一個改善的根本辦法。
在同年12月24日召開的北京工作會議和1961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還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后,毛澤東派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位秘書各帶一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好的生產隊,為期10天至15天。
1961年1月26日,毛澤東乘火車從北京前往廣州,沿途聽取了河北、山東等七個省委和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的匯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話。
3月,有中南、華東、西南三個大區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同志參加的“南三區”會議在廣州開幕。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寫了一封信,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毛澤東說,“提出的問題是有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一篇文章《關于調查工作》(原題目《調查工作》,在編入1964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時,毛澤東又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大家對中共中央的信和《關于調查工作》一文反響強烈。
此后,中央領導分赴各地進行調查研究。
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進行了44天的調查。在天華大隊,他用化名和“分隊長”的公開身份,住在養豬場。
周恩來、朱德分別在河北、四川、河南等地農村進行調查。
鄧小平、彭真在北京順義縣調查后,在聯名致毛澤東的信中講了社隊規模、糧食征購、余糧分配、供給制、食堂和家庭副業等問題。
一直到6月中旬,中央在發出的指示中仍要求,中央及省級領導“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調查研究。地、縣兩級的領導人員也應該這樣辦”。
省委書記的改變
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開始恢復工作。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不由自主地用習慣的調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觸的民眾生活。
習仲勛于1978年4月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用他自己的話說,此前已有16年沒有工作了。他到廣東后,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逃港問題。當時由于內地生活水平低,自1954年至1978年,廣東全省出逃56.5萬人次。一直以來,中央及廣東都對逃港采取嚴厲措施,但屢禁不止。
1978年7月初,習仲勛乘坐一輛七座面包車前往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一路上只見雜草叢生,十分荒涼,耕地丟荒很多。他到達當時還是寶安縣城的深圳后,沒有先聽地方干部匯報,而是直接走到村莊里與農民、村干部交談。
習仲勛其實本來也抱著傳統想法,在收容站還勸導被抓回的外逃農民。但是,當他考察了省港邊界線上的羅芳、蓮塘,又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親眼目睹了香港的車水馬龍后,若有所思地說:“解放那么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習仲勛在這個夏天走了23個縣。除了研究逃港問題的根源,習仲勛還在調查研究中為土地沙化嚴重的珠三角找到了出路:他在調研中走到了沙頭角的塑料花廠、皇崗的假發廠,這是中國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后來,這種模式由廣東推開,并遍及中國的南方地區。
在安徽,1977年6月,萬里任省委第一書記。他回憶說:“我又不熟悉農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農業、看農民。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萬里下去調查一般是一部小車、兩三個人,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直接進村到戶。“那幾個月,我不開會,不作指示,不提口號,只是看、聽、問”。
當時安徽最嚴重的是外出討飯問題。在鳳陽縣,萬里就親眼看到過農民扒車外流討飯的情景。后來在一次省委座談會上,有人提到,鳳陽農民有討飯的“習慣”,萬里氣憤地說:“我們的農民是勤奮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臉面的,只要能夠吃得飽,他們是不會去討飯的。”他接著說,問題是那里條件并不壞,他們為什么吃不飽飯?而這個關系全中國農民生活的疑問,也在調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來從安徽的實際情況出發,最重要的是怎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一切無從談起”。這樣,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的《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在安徽出臺。在這份文件中,提出了加強經營管理,建立生產責任制,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尊重生產隊自主權等諸多原則,就此拉開了安徽以及整個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伊始,老干部們就這樣奔走于山水之間,用他們自三四十年前就倡導的工作方式,為中國的發展尋找著出路。
(殷欣奎、張源、高良槐、邱寶珊、林賢焜、李云貴薦自2013年5月1日《黨史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