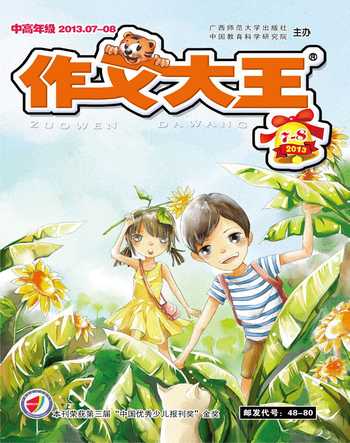平凡之中見偉大
白雪
2004年,一篇題為《瘋娘》的小說在網上瘋傳,國內外數十家中文網站轉載,創造了網絡史上的最高點擊率,讀者們被感動得熱淚滿面。母愛的偉大、人性的光輝、小說語言的質樸無華,是這篇小說贏得讀者的主要原因。
小說寫到娘的兩次出場,兩次退場。第一次出場,娘還年輕,“流落到我們村,蓬頭垢面,見人就傻笑,且毫不避諱地當眾小便。因此,村里的媳婦們常對著那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婦還上前踹幾腳,叫她‘滾遠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著在村里轉悠。”娘的身世無從考究,此前的生活更是空白。她一出現,便是這樣一個悲慘的形象。因為瘋、傻,“我奶奶”動了心思,收留她給又窮又殘疾的“我父親”做了媳婦,然后,生下了“我”。但是,娘的悲慘生活并未從此結束,“我一生下來,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從不讓娘靠近” 。
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給,給我……”奶奶沒理她。我那么小,像個肉嘟嘟,萬一娘失手把我掉在地上怎么辦?畢竟,娘是個瘋子。每當娘有抱我的請求時,奶奶總瞪起眼睛訓她:“你別想抱孩子,我不會給你的。要是我發現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攆走。”奶奶說這話時,沒有半點兒含糊的意思。娘聽懂了,滿臉的惶恐,每次只是遠遠地看著我。盡管娘的奶脹得厲害,可我沒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匙一匙把我喂大的。奶奶說娘的奶水里有“神經病”,要是傳染給我就麻煩了。
這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為她的瘋傻,她被剝奪了撫養自己孩子的權利。這里描寫娘的語言(她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愿)、神態(吃力地喊、滿臉的惶恐、遠遠地看著我),這樣的情景,讀來令人揪心地痛。描寫人物,需要有事情來表現,作者在這里把瘋娘這一形象放在“不能喂養自己的孩子”這一絕境之中,“瘋娘”這一形象強烈地沖擊了讀者的心。
然而,由于家里實在是窮得揭不開鍋,奶奶還是狠心地把娘攆走了。在被趕出家門之時,娘近乎本能的母愛再一次顯露:娘似乎絕望了,連那半碗飯也沒吃,踉踉蹌蹌地出了門,卻長時間站在門前不走。奶奶硬著心腸說:“你走,你走,不要回頭。天底下富裕人家多著呢!”娘反而走攏來,一雙手伸向婆婆懷里,原來,娘想抱抱我。
奶奶猶豫了一下,還是將襁褓中的我遞給了娘。娘第一次將我摟在懷里,咧開嘴笑了,笑得春風滿面。奶奶卻如臨大敵,兩手在我身下接著,生怕娘的瘋勁一上來,將我像扔垃圾一樣扔掉。娘抱我的時間不足三分鐘,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將我奪了過去,然后轉身進屋關上了門。
“娘第一次將我摟在懷里,咧開嘴笑了,笑得春風滿面”,讀到這里,讓人不由得熱淚盈眶。這是以喜寫悲的成功典范。娘這時候的喜,更強烈更深刻地襯托出人物的悲劇感。一是時代的悲劇——窮;二是人物的悲劇——娘的瘋、傻,然而我們看到的,她對自己的兒子只有愛,這種愛強烈到近乎本能,強烈到絕望,純粹到不摻一點雜質;三是人性的悲劇——奶
奶把瘋娘趕出了家門。
這是瘋娘的第一次退場。
瘋娘的第二次出場,已經是五年之后,那時候“我”已經六歲。這五年里,娘去了何方,如何活下來的,經歷了怎樣非人的苦難,一概無從知道,只能留給讀者想象。雖然在這五年里,“我”非常想念她,但她真的來了,卻并沒帶來喜悅,悲劇仍在繼續:
那天,幾個小伙伴飛也似的跑來報信:“小樹,快去看!你娘回來了,你的瘋娘回來了。”我喜得屁顛屁顛的,撒腿就往外跑,父親和奶奶隨著我也追了出來。這是我有記憶后第一次看到娘。她還是破衣爛衫,頭發上還有些枯黃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哪個草堆里過的夜。娘不敢進家門,卻面對著我家,坐在村前稻場的石磙上,手里還拿著個臟兮兮的氣球。當我 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時,她急切地從我們中間搜尋她的兒子。娘終于盯住我,死死地盯住我,咧著嘴叫我:“小樹… …球……球……”她站起來,不停地揚著手中的氣球,討好地往我懷里塞。我卻一個勁兒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沒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這樣一副形象。
“破衣爛衫,頭發上還有些枯黃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哪個草堆里過的夜”,這個形象,讀來令人流淚,但那時候卻使“我大失所望”。年幼無知的“我”,心里只有面子,又如何能理解母親的痛苦與悲劇?母親雖然瘋傻,卻還是在時隔五年之后記得孩子的家門,從小伙伴中認得出自己的孩子。她“手里還拿著個臟兮兮的氣球”,“死死地盯住我,咧著嘴叫我:‘小樹……球……球……她站起來,不停地揚著手中的氣球,討好地往我懷里塞”。原來,不知道她從哪里撿到了這個氣球,心里惦著的是拿給兒子玩。“急切地”“搜尋”“死死地盯住我”“咧著嘴叫我”“不停地揚著手中的氣球”“討好地往我懷里塞”,這里,一系列的動作描寫與神態描寫,把母親那純粹到令人揪心發痛的母愛,毫無裝飾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以細節寫人物,平凡中見偉大,短短的一段文字,有著豐富的信息,人性的矛盾與美丑,在這里也有著強烈的表現。
母親這一次回來,奶奶良心發現,留下了她,而“我”卻不認這個娘,“因為娘丟了我的面子”。
我從沒給娘好臉色看,從沒跟她主動說過話,更沒有喊她一聲“娘”。我們之間的交流是以我“吼”為主,娘是絕不敢頂嘴的。
娘就在這樣的情境中艱難生活下來,沒有生存的能力,一次次出錯惹禍,但她對兒子的愛,卻是只能用“濃烈”與“純粹”來形容。她知道護著兒子,知道在風雨中給兒子送傘。終于有一次,她為了保護“我”,把欺侮“我”的孩子丟進了水塘,闖下大禍。
娘為我闖了大禍,她卻像沒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復了一副怯怯的神態,討好地看著我。我明白這就是母愛,即使神志不清,母愛也是清醒的,因為她的兒子遭到了別人的欺負。當時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聲:“娘!”這是我會說話以來第一次喊她。娘渾身一震,久久地看著我,然后像個孩子似的羞紅了臉,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天,我們母子倆第一次共撐一把傘回家。
“即使神志不清,母愛也是清醒的”,這是“我”第一次對母親有了認識,對母愛有了認識。“我”第一次叫了聲“娘”,“情不自禁”這個詞,正寫出了“我”內心對母愛的感動,從內心里認可了這個娘。這是一個感人的場面,母親的反應,她的笑,是整篇文章里真正令人喜悅、沒有悲劇襯托、最為明凈的場景。
經過一系列的“事件”,母親真正成了家里的一員,艱難的生活仍然艱難地繼續。終于到了“我”讀高中,奶奶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難,住宿生自己從家里炒點咸菜帶到學校下飯,母親承擔起給“我”送菜的任務:
每次總是隔壁的嬸嬸幫忙為我炒好咸菜,然后交給娘送來。20公里的羊腸山路虧娘牢牢地記了下來,風雨無阻。也真是奇跡,凡是為兒子做的事,娘一點兒也不瘋。除了母愛,我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在醫學上應該怎么破譯。
路途是如何艱難,這里一筆帶過。這里難得使用議論性語言,給母愛下個評語,使全文有水到渠成之感。貌似一切都在朝 好的方向發展,希望就在前面。但是,正是母愛的無往不顧,導致瘋娘最后一次退場離開,并且是以死亡的形式。
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個星期天,娘來了,不但為我送來了菜,還帶來了十幾個野鮮桃。我拿起一個,咬了一口,笑著問她:“挺甜的,哪來的?”娘說:“我……我摘的……”沒想到娘還會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揚她:“娘,您真是越來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
這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所以作者精確地把它寫出來,而不是用“有一天”這種模糊的表達。“我”的笑,我對娘的“表揚”,都是發自內心,娘的笑也沒有了過去的“怯生生”。但也正是因為“我”的表揚,使得娘把摘野桃給兒子吃當成了第一要事。
娘臨走前,我照例叮囑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應著。送走娘,我又扎進了高考前最后的復習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課,嬸嬸匆匆地趕來學校,讓老師將我喊出教室。嬸嬸問我娘送菜來沒有,我說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嬸嬸說:“沒有,她到現在還沒回家。”我心一緊,娘該不會走錯道吧?可這條路她走了三年,照理不會錯啊。嬸嬸問:“你娘沒說什么?
”我說沒有,她給我帶了十幾個野鮮桃哩。嬸嬸兩手一拍:“壞了壞了,可能就壞在這野鮮桃上。”嬸嬸幫我請了假,我們沿著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確有幾棵野桃樹,桃樹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幾個桃子,因為長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來。我們同時發現一棵桃樹有枝丫折斷的痕跡,樹下是百丈深淵。嬸嬸看了看我說:“我們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說:“嬸嬸你別嚇我……”嬸嬸不由分說,拉著我就往山谷里走。
事件急轉直下。對于正常的人來說,母愛有時都是盲目的,對于又瘋又傻的瘋娘,除了母愛更無其他,孩子的表揚成了她最幸福最放在心上的事,于是摘桃子成了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去做的事,何況,也許她并不一定能意識到危險。她是帶著怎樣的心理去摘桃子?怎樣跌下懸崖?這些都留給讀者去想象。
娘靜靜地躺在谷底,周邊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還緊緊攥著一個,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得五臟俱裂,緊緊地抱住娘,說:“娘啊,我的苦命娘啊,兒悔不該說這桃子甜啊,是兒子要了你的命……娘啊,您活著沒享一天福啊……”我將頭貼在娘冰涼的臉上,哭得漫山遍野的石頭都陪著我落淚……
娘的離去,與娘的第一次出場形成強烈對比。對母親最后的面貌的描寫,她手里緊緊攥著的桃子,電影特寫鏡頭一般沖擊著讀者。“我”的悲痛與哭喊,與小說中我一直對娘的不公,也形成對比。偉大的母愛消融了因為人性自私帶來的隔閡。
《瘋娘》在網上很容易搜到全文,這里就不再分析。
我常常對同學們說,細節就是力量。寫人,一定要注意細節,把人物放到事件中去寫,寫出細節,就寫活了人物。至于用語言描寫,還是動作描寫,還是其他的描寫方式,根據細節描寫的需要來選擇。《瘋娘》這篇小說,正是這樣做的。這篇小說打動讀者的力量不僅僅在這故事的曲折悲慘,更在于這些能夠深深表現母愛與人性的細節。喜與悲,傷與痛,傻與純,這些強烈的對比,一個個細節,給了讀者強烈的沖擊。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次考試,如同一場戰斗。勝敗乃兵家常事,要勝不驕敗不餒,因為驕傲是失敗的根源。淚水沖淡了我的驕傲自負,卻沒有沖垮我的自信堅強,沒有沖跑我對考試的無所畏懼。
3111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育才實驗小學602班 李 珂《那次我哭了》指導老師 錢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