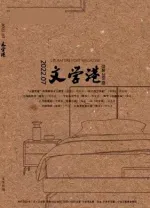山村行走(三題)
葉喆斐
老村長
老村長姓汪,從村辦退下來那會正趕上古村旅游熱。他家后山腰上修筑了步行道,大批背包客慕名而來,成群結隊地徒步上山,轉一圈回來,天已擦黑,沒過足癮的就想住下來,次日繼續爬行進山。頭腦活絡的汪村長,在游客一進一出間看到了無限商機。他辦完退休手續,就直奔鎮上,報名參加了農家樂經營管理高級研修班。等他拿了證走出研修班走回熟悉的村莊時,精神抖擻得像出征的將士。整個春天,他都專注于他的農家樂休閑旅店,信心百倍意志堅定地在他自家的灶口上重新上崗,當上“火頭軍”總司令。
老村長捏過鋤頭撥過算盤珠的手,也就從那個春天起,操起了菜刀揮起了大勺。他麻利地在灶臺前揮舞著,所過之處,色香味一一呈現。青菜葉綠油油的,菜幫子白白胖胖的,剛剛從自家菜地里拔出來,帶著“活靈”。老村長左一刀右一刀下去,綠白相間的小青菜頃刻之間四分五裂,從案板上輕輕一劃,吱的一聲全部倒入熱油鍋,竄出一尺高的火苗,映紅了半間灶房。老村長的心比油鍋還熱火,比火苗還亮堂。這年頭,城里人大老遠趕來,除了看看山里洗過一樣的天,看看桃紅柳綠、油菜花開,聞聞四季氣息、泥土芬芳,還有不就是沖著農家樂里鮮綠的葉,拖泥帶水的根還有那份沒打過農藥的踏實嗎?
一大早,老村長便站在自家一樓客廳的旋轉樓梯口,用他十分熱情十分洋溢的眼光掃視了洗漱的打包的繞到灶房吃早飯的客人,又抬頭透過旋梯扶手掃視了樓上樓下整個空間,大約發現客人基本都起來了,便清了清嗓門,開問:“中午回來吃飯么?想吃什么菜?”大家起床后,進進出出打他身邊過,十分忙碌。有說白天去爬山,中午自行解決,但晚上想吃土雞。老村長聽了忙解釋道:“禽流感來了,土雞沒得吃了。”唉聲嘆氣中少不了幾分遺憾。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去年秋天,我和一幫驢友第一次來,都點著名要吃土雞的。這屋前屋后蒼翠欲滴的濃綠,千回百轉越嶺而來打門前過的溪流,在這樣優美的環境里,小雞小鴨吃著五谷和小蟲子,都是天然、無污染的食料,長出來的不是細皮嫩肉才怪呢。老村長說:“不吃土雞是暫時的,現在可以吃毛筍啊,還有透骨新鮮的倭豆煲。”客人一聽來了食欲,七嘴八舌地點開了,村長一一應答著,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記全。不過我想象得出,那股認真勁與當年在村委會開會,解答村民這個那個問題時的神態是一樣的。
記下所需菜單,老村長直奔停放在門外操場上的三輪摩托,插上鑰匙,突突突發動起來。他跨上去,摸了摸衣兜。先去哪里呢?猛然想起前兩天鄰村大阿妹來過電話,她的地瓜粉絲曬干了,讓他去取。路過山頭順便還要掏幾顆毛筍,那是剛才我們點的。
三輪摩托沿著村道,麻利地拐過一個溪坑橋,一支煙的功夫,已在一排老屋群前停住了。這組老屋由坐西朝東的三間老屋與坐北朝南的五間屋構成,明堂和明堂相接。老村長的大阿妹家就在這組屋群里,老屋大門朝東,圍墻是用舊瓦爿和碎石頭壘起來的,墻頭隔檔放了幾只小瓦罐,里面橫七豎八種了一些大蒜和小蔥,在山風中搖擺。厚重的兩扇木門,被歲月蝕成褐色,坑坑洼洼露出一根根木筋。老村長一腳跨進石頭門檻,迎面是一個長方形天井,天井中央擺著幾只圓形竹編篩子,上面鋪陳一盤盤地瓜粉絲。
地瓜粉絲,是我最喜歡吃的食品之一,超市里有,但做工完全不一樣。臨時攤販叫賣的粉絲擔心不衛生,是不敢嘗試的,有人說吃它等于吃編織袋。眼下有些食品真不是做給人吃的。相比之下,山里人家自己做的粉絲就相當稀罕了,地瓜都是去了皮的,切出芯子那一塊,軋碎打漿,濾去水分沉淀成粉,是不加任何添加劑的,土灰色的粉倒入加工廠的和面機里,拉出一根根土灰色半透明的絲,灰撲撲的,賣相不甚好,但絕對是綠色環保產品,久煮不爛,一口下去筋斗滑爽,口感柔軟。
老村長大阿妹家的粉絲是不外賣的,自己留著食用,之余再送些親朋好友,尤其是那幫上海遠親,特別喜歡地瓜粉絲之類的土特產,越天然的越好,越綠色的越好。老村長是她阿哥,阿哥開門做生意,打的都是天然的綠色牌子,粉絲、淀粉、青菜蘿卜芋艿頭毛竹筍,小到大蒜小蔥,都由大阿妹特供。
從大阿妹家出來,老村長的三輪摩托后翻斗廂里多了兩大包粉絲,老村長捋捋褲腳管,又上路了。繞過彎彎曲曲蛇形山路,在一個干涸的山溝邊停下,前面有個沙堆,對面有一條狹長的山谷,不是很寬但很長,綿延幾公里。村長想跨過山溝,到山谷上方的自家竹林挖幾顆毛筍,可又放心不下車兜里的兩大包寶貝,情急之下,從山道雜樹叢中揪下一大把雜草,蓋在上面。有了雜草作掩護,老村長放心大膽地向毛竹林走去。
村長老婆
在老村長家灶房間吃早飯,一股嗆人的煤煙味從門邊飄了進來,這股怪味很難聞,但卻是久違了的。
這種味兒是和我兒時記憶聯結在一起的。那時老家沒有煤氣,燒菜煮飯全靠一只煤球爐。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爐子。將爐內隔夜的煤灰清空,用廢紙點燃,把碎木塊放進爐內,木塊燃著后蓋上煤球。這時嗆鼻的煙味就會從爐內冒上來,嗆得兩眼通紅,淚水直流,不得已只好“請”它去了弄堂口。遇到刮風落雨,木柴受潮不易點燃,就給爐子戴一頂“高帽子”——鐵皮煙囪,弄堂口擺攤的老鐵匠定做的。小喇叭似的煙囪能拔風,能讓火苗竄高些,能讓生爐子的速度快些,罩在爐口也不用擔心爐火被雨淋滅。那時候,每當傍晚,弄堂里的煤球爐子便排起了長隊,整個弄堂到處飄散著爐煙。雖說嗆人,但那時煤球爐是與吃飯連在一道的,對我來說就有了幾分誘惑。
現在城市都用上了液化氣天然氣,這味兒也只有偶爾在賣羊肉串攤位前聞得到。在山區,多數人家還是習慣燒煤爐,柴禾是現成的,出門就有,比起液化氣,點火生爐子,是有些不方便,但成本低,節儉的山里人家會用液化氣炒菜,煤爐燒水做飯,冬天取暖。
門外生爐子的是村長老婆。入住他們家,很少聽到她開口講過話。入住第一天,我們在里屋吃飯,老村長就在灶房喊老婆去端菜,她應聲而出,客人不禁一怔,大伙嘻嘻哈哈地與灶房里的“火頭軍”總司令開起了玩笑。村長老婆讓人立即聯想到傳說中的賢妻良母。她低頭出,低頭進,一直在餐桌與灶頭之間悄無聲息地來回跑動。有性子急的,不停催她快上菜,熱乎乎的農家菜,都有點等不及了。村長老婆勤快地應答著,小碎步邁得更緊密了,但沒有發出什么聲響,和她的說話聲音一樣很小,很柔和。
后來發現她一直是笑瞇瞇的,笑瞇瞇地端菜送飯,笑瞇瞇地講話,笑瞇瞇地掃地。走路說話都輕手輕腳地低著頭,只有和我們客人打招呼時,才會禮節性地抬下頭,還沒等看清她的臉,早又低下去了。和陌生人打招呼,有點怕難為情,溫順害羞的樣子,讓人覺得她不是一位老婦而是一個羞澀的小姑娘。晚上,客人打麻將,三缺一,村長被叫去補位,留她一人在廚房打掃“戰場”。整個拾掇過程都是按她每晚原定的程序有條理地進行的,一個小時后,灶房又恢復原樣,干凈整潔,一掃剛才老村長大刀闊斧輾轉于此的混亂場面。老村長是個牌迷,上手就剎不住車,一圈接一圈,快到半夜了。她拿著掃帚與畚箕,從廚房到客廳,來來回回打掃,有好幾個回合了。我瞌睡得不行了,上樓回房前勸她先去睡覺,她照例笑笑,沒吱聲。我上樓洗刷完畢,順樓道瞄了一眼,看到樓下麻將桌邊,她依舊安靜地坐著。
薄霧籠罩了整個山村,夜間氣溫較低,空氣中的水蒸氣在田野里結成霜。初春,山村的早晨依然有幾分嚴冬的寒冽。村長老婆點著了煤球爐在院子里撲打身上的灰塵,拎著爐子回屋,爐膛火紅,映著她紅彤彤的臉。她給客人悉數倒水沏茶,順手灌了一壺熱水給我,一起遞過來的還有一小包茶葉,裝在一個透明的塑料袋里。“這是野生茶葉,很香的。”軟軟綿綿的聲音充滿疼愛。真是一個細心的女人,知道我好這一口就特意留著。昨晚也不知道她幾點睡下的,反正一大早就在掃屋掃院洗衣拆被生爐做飯,里里外外支應,勤勞如蟻。
老人們的村莊
沿著盤山公路,一直走到路盡頭。迎面是一個大山坳,坐北朝南,像一把巨型太師椅,四平八穩,橫放在我們面前。
七零八落的小村莊都安放在這把“太師椅”里。村子依山而筑,村道從山腳一直伸展到山腰,阡陌交錯。抬頭仰望,“太師椅”后背險峰層疊,綠林盡染,與這美景不相宜的是灰暗衰老的小村子掩映在綠蔭中,顯得破敗沒落。村子很小,沒有店鋪,沒有學校,卻有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建起來的老式大禮堂,一個破敗不堪的軋米廠,灰撲撲的夾在民屋群里,外墻上還隱約可見“文革”時期的標語。軋米廠已經廢棄多年了,屋頂漏洞百出,不知怎么也沒拆。禮堂偶爾還辦個喪事,但也年久失修。
小村子幾乎沒有一幢新房子。老房子的外墻多半已經坍塌,長出了大量雜草,陽光穿過斷墻,滿目瘡痍。倒掉的部分還是馬頭墻,以前都是大戶人家,老房子屋檐木刻,馬頭墻特有的青磚依稀可辨。大戶人家曾給村子增添過旺盛。人氣最旺時村子有數百人,炊煙繚繞,童聲喧鬧。現在村子靜極了,靜得有點殘忍。年輕一點的男人,女人,孩子連同他們的家,都去了山外面的城市。
通往村莊的公路,只有陰歷逢三或逢七,才有班車來。山下來串門的親戚,城里探望父母的子女,會乘車上來,逗留不到一天,就走了。老人們也會搭坐班車下山,買回一些油鹽。
村口,掛在老樹上的廣播喇叭每天響著,準點播報。樹下那間村辦活動室,里外坐著幾位老人,大的近百歲,小點的也過花甲。房子是磚瓦結構的平房,有了年份,昏暗的屋里擺著兩張牌桌和一些板凳。從早到晚,老人們幾乎都聚到這里,打牌,聊天,打瞌睡。
我們徒步進村,村外遇見一位老人。我們跟隨他在村道上前行,沿途遇到幾個熟人,他都開心地告訴人家,他們是從山腳下走上來的游客,那種興奮的心情,就像過節一樣。
山村太孤寂了,老人們太渴望有人進山來,講講話,聽聽聲音,有點人氣。
一位老太太拎著兩只熱水瓶,給我們的水杯倒滿水,看到我們拍照,一直怯怯地沖我們笑,我們提出和她合影,她像孩子一樣興奮,不停拍打衣裳上的塵土。我不知道她的家庭情況,或許她有很多子女,或許她的子女在城里富甲一方。只是她的眼里,充滿了落寞的神情。只有拍照的那一刻,她是開心快樂的。
離開時,老人們在村口站成一排與我們揮手,一口一個再會。
這些老人,我們還會再會嗎?這個地方,我還會再來嗎?
再來,他們還會在這里嗎?這么一想,心里就有了酸楚。人就是一個過客吧。多數人與我們擦肩而過,就永遠不再相見了。前行中,自己又何嘗不是別人生命中的過客呢。■
選自《鎮海潮》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