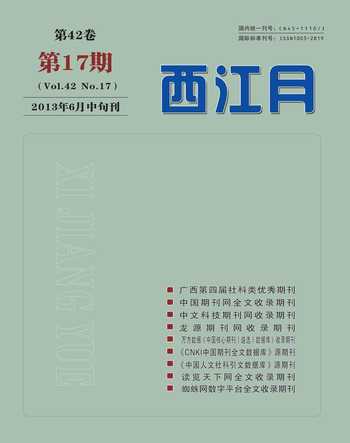《秦腔》人物語言的平常化
付新雅
【摘要】長篇小說《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再次顯示出賈平凹的寫作實力和才氣。《秦腔》語言獨樹一幟,特色鮮明,特別是小說中人物語言的平常化,既強化了人物的生動感又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也顯示出賈平凹文學創作中對語言的獨特天賦和審美追求,本文通過四個方面論述《秦腔》中人物語言的平常化。
【關鍵詞】秦腔;人物語言;通俗鄉土;直白顯露;簡約幽默
作為“當代鄉村變革的脈象,傳統民間文化的挽歌”,《秦腔》的蘊涵非常豐富,而表現和承擔這一切宏旨的是語言,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小說的載體,“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離開了語言,文學無以存在。”[1]小說人物語言即小說里人物的對話語言、獨白語言和心理語言。平常化即生活化、日常化,人物按照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生活原本的模樣說話,作為一種質樸本色的還原。
一、通俗鄉土的語言元素
我說:“天義叔,你眼鏡一戴像個將軍!”他沒理我,走出院門了,才說:“淡話!”
書正說:“天義叔,你真是個土地爺么,一輩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你不嫌潑煩啊?”
來順他不理解我,他講究會過日子呢,就是沒吃過一頓稠飯。
梅花喊:“翠翠,把廈屋墻窩子里的煤油燈拿來。”
“淡話”、“潑煩”、“稠飯”、“廈屋”都是商周地區的方言口語詞匯,分別是“閑話”、“麻煩”、“干飯”、“偏房”的意思,有效地吸收方言成份,可使語言具有特殊的表現力、特殊的美。這些通俗土語經過作者的靈活運用,顯示出特有的質感和鮮活,拓展和延伸了語言的表意內涵,同時也極大地增強了語感效果,拓寬和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表達功能,更顯出人物性格情感的真實性和形象的生動感,這些都使作品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域特色,讓人讀著有強烈的如臨其境般的感受。賈平凹小說在語言的構建上,從人物的文化背景出發,用家鄉人口語,其親切感使得人物形象與神韻躍然紙上,這也是汪曾祺所說的“語言和人物貼近”。[2]
二、直白顯露的語言形式
窯場的三踅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邊吃一邊說:清風街上的女人數白雪長得稀,要是還在舊社會,我當了土匪會搶她的!
狗剩是五十多歲的人,黑瘦得像個鬼,他把頭伸到老演員面前,突然說:“你是《拾玉鐲》”?老女演員愣了一下,就明白了,笑著點了點頭。狗剩說:“我的毬呀,你咋老成這熊樣啦?!”
“你咋不死呢?你被打死了我給你申報了烈士,可你好好的你把馬勺讓打砸搶啦,你讓我怎么給四叔交待?!”
“語言的形式符號不僅是語意的同時還是審美的形式符號”[3],農民的審美是“直線型”的,這也是直白顯見的思維與情感的反映,“語言和我們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織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同一回事。”[4]賈平凹的《秦腔》,描寫一群“真實”生活在清風街上農民,他說“當時寫文章就覺得,你就是走到啥地方,你農民最基本的那種東西,他還是在血液里,還是殘留了好多東西。小農思想就是農民那些東西,就是農民那種生存環境造成的那種文化、那種心理。”[5]農民的愛恨、不滿、感激、憤怒、世俗、粗鄙、苦楚都不會含蓄遮掩,不會“加工潤色”,帶有一些霸道、不討人喜歡、蠻橫、不識抬舉和不高尚,總有一些坦蕩生活的最真的可愛和殘忍。這就是農民的本色,是藝術和生活的真實,不作虛不摻假地本質的流露。
三、樸素真誠的語言情意
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風還會愛待白雪嗎?我會愛的,討來一個饃饃了,我不吃,全讓白雪吃!
還又一想,如果誰撞一下白雪也好,不要撞得太重,最好讓我看見,我就會豁出命去撲上去和那人打,我打壞了他,我英雄,他打壞了我,白雪就會心疼我。
四嬸、白雪和夏雨都驚愕地看著我,那一瞬間,我是多么得意,我怎么就能想到這一點呢,我都為我的偉大而感動得要哭了!
“文學語言遠非僅僅用來指稱或說明(defferential)什么,它還有表現情意的一面,可以傳達說話者和作者的語調和態度”,[6]文學語言的情意性,表現在通過構建文學語言深入傳遞人物的主觀態度和內心情感。“語言都是表情達意的工具”“凡言都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為不美”,[7]賈平凹的語言之所以是美的,也來自于他創作里,飽含愛情的傾訴與追求。《秦腔》中,張引生對白雪的愛是深刻的,然而這種愛情的表達之于一個年輕農民的他,又注定是“樸素”的,“吃饃”、“過河”、“逞小能干”、“耍小聰明”、“自造得意”等普通事物和平常話語,在這里都表現出張引生對白雪的,善良悉心,非常執著真誠、有埋怨又十分甘愿的愛情。
四、簡約幽默的語言風格
白雪白雪,這不公平么,人家夏風什么樣的衣服沒有,你仍然要給袍子,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顫哩,你就不肯給我件褂子?!
三踅說:“戰爭年代你狗日的是個逃兵哩!”我說:“戰爭年代?那我就提了槍,挨家挨戶要尋我的新娘里!”
鄉親們,雖然我們日子是艱難的,勞作是辛苦的,但理想卻是遠大的,等咱有錢了,咱去吃油條,想蘸白糖是白糖,想蘸紅糖是紅糖,豆漿么,買兩碗,喝一碗,倒一碗!
賈平凹筆下的幽默,時而輕松諧趣,時而隱射嘲諷,時而單純敘說,時而高調調侃,有張有弛,非常巧妙。“一切風格都是姿態,心智的姿態與靈魂的姿態”[8],幽默是賈平凹在創作中的超越苦難意識后的升華,是其千錘百煉后的深切感受和實際踐行。張引生的嫉妒和狂放的性格特征,在這些簡約幽默的語言對話中,顯得非常生動鮮明,它使得人物形象真實質感增強。
即便進城生活了幾十年的賈平凹依然說自己“就是農民”,[9]“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里的”,[10]他堅固自覺的農民意識使得小說人物賦有濃厚的鄉土色彩和傳統氣息,故鄉是他最擅長的文學背景,故鄉人事是他最親切的創作源泉。《秦腔》中作者“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清風街和清風街人們的日子,在作者那里,都有真實的來源和影射,“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里花”,“但水中的月鏡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賈平凹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11],他以自身獨特的語言把握能力和文學創作天賦,賦予作品鄉土地域的特色和鮮活豐富的情趣。
【參考文獻】
[1]李啟榮.文學語言學[M].人民出版社,2005.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卡西爾.語言與神話[M].三聯書店,1988.
[4][美]薩皮爾.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5]賈平凹.走走·賈平凹談人生[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6][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三聯書店,1984.
[7]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8]瓦爾特·羅利.風格[M].商務印書館,1986.
[9]賈平凹.靜水流深[M].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
[10][11]賈平凹.秦腔·后記[M].廣州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