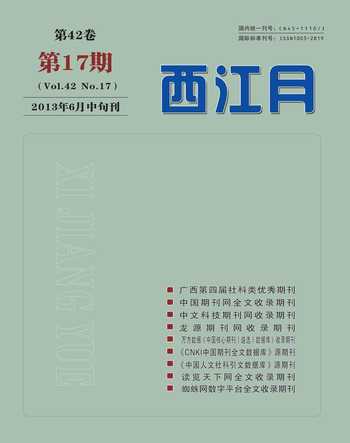城市文化映射之下人性的弱點
朱妍妍
【摘要】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蘇童的《米》塑造了兩個性格不同、命運卻極其相似的人物形象——祥子與五龍。祥子與五龍都是離開鄉間到城市去追尋夢想的年輕人,然而最終在城市經歷過坎坎坷坷之后,卻都一步步走向了墮落與毀滅。本文試從城市文化對人性的壓迫與摧殘的角度來分析祥子與五龍墮落的原因,揭示城市文化罪惡的一面,同時也揭示祥子和五龍人性上的弱點。
【關鍵詞】城市文化;祥子;五龍;欲望
老舍的《駱駝祥子》創作于1936年,蘇童的《米》創作于1990年,雖然創作于完全不同的兩個年代,但是這兩部小說卻書寫了兩個命運極其相似的人物。《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和《米》中的五龍都是失去了故鄉的土地而奔走到城市去尋找新的夢想和出路的年輕人,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一帆風順,兩人在經歷了相似的經歷之后,走上了殊途同歸的道路——墮落。混亂的社會的壓迫、喧囂的城市的誘惑、人性與性格中的弱點,種種因素導致了祥子和五龍的墮落,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究其根本,是城市文化使得祥子和五龍——兩個身上保留著鄉村文化的鄉下年輕人,與城市格格不入,也是城市文化誘發了他們人性深處的弱點,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墮落。
一、祥子的妥協與五龍的反抗
祥子“生長在鄉間,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里來”[1],他帶著鄉下小伙子特有的足壯與誠實,懷著憧憬與希望想要在城市扎下根,“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這座古城。這座城給了他一切,就是在這里餓著也比鄉下可愛。”[2]五龍的情況同祥子幾乎一樣,爹娘死于一場大饑荒,家鄉又發了大水,于是他坐著運煤的火車來到了陌生的城市。祥子與五龍命運相似,性格卻截然相反。
初來城市的祥子誠實、善良。在遇到比他還要悲慘的老馬和小馬兒時,一向對自己苛刻不肯多花一分錢的祥子,慷慨地為那祖孫倆買了十個羊肉餡的包子;在曹先生的宅子里被偵探訛詐去自己幾乎所有的錢財之后,還不愿意偷曹宅的東西,拼力維持著自己的清白;甚至想到自己牽來的幾匹駱駝想要賣高價就只能挨刀子,便覺得缺德。然而這樣一個善良、正直的祥子卻無法面對城市里的各種壓迫與誘惑。他辛苦了三年才買下的車被大兵搶去,第二次攢起來準備買車的錢被偵探騙去,面對這些,他無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他不小心被虎妞誘惑,又一步一步地被虎妞誘騙與她結婚,他明白虎妞“撒的是絕戶網,連個寸大的小魚也逃不出去”[3],但他仍然無力抵抗虎妞的誘惑,更無力反抗虎妞的誘騙與壓迫。“祥子不僅不能獲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無法拒絕自己所厭惡的。”[4]
祥子身上帶著鄉間小伙子的種種優點,但在面對城市里形形色色的誘惑時,他仍然做不到不心動。他的第一輛車被搶,自己也被拉去做苦力,在逃離軍營時他順手“牽”走了幾匹駱駝,“這次是他墮落的開始,因為他的人格受到損害,不完美了。”[5]之后,他“看別人喝酒吃煙跑土窯子,幾乎感到一點羨慕”[6],甚至想到“要強既是沒用,何不樂樂眼前呢?”[7]雖然還沒有付諸行動,但他已經動了這樣的念頭,我們也不難猜到他后來的結局。在被虎妞誘騙著結婚后,他完全可以離開虎妞,擺脫那樣的生活,但他仍然舍不得北平,“他不能離開這個熱鬧可愛的地方,不能離開天橋,不能離開北平。走?無路可走!他還是得回去跟她——跟她!”[8]此時的祥子已經無法拒絕繁華熱鬧的城市帶來的誘惑,他正在一點一點地向城市妥協,向誘惑妥協。小福子的死徹底打垮了祥子,他的確值得同情,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心靈的脆弱,“祥子的悲劇并不單是因為各種環境因素合起來害了他……一樣地也會打垮他。”[9]可以說,城市文化的侵蝕與祥子自身的脆弱造是造成祥子墮落的最關鍵因素。
和祥子一樣,五龍是個孤兒,又失去了鄉村的土地,于是遠離了貧困的屢遭天災的楓楊樹鄉村,來到向往已久的城市,這里有“雪白的堆積如山的糧食,美貌豐腴騷勁十足的女人”[10],這里“靠近鐵路和輪船,靠近城市和工業,也靠近人群和金銀財寶,它體現了每一個楓楊樹男人的夢想,它已經接近五龍在腦子里虛擬的天堂。”[11]然而天堂只是表面的,五龍生活的希望是可以吃飽飯,每一頓飯都可以吃到大米,但是污穢的城市卻一而再地帶給他壓迫、屈辱、孤獨和恐懼。與只知道一味忍讓妥協的祥子不同,五龍的身上充滿了抵觸與反抗。《米》的作者蘇童認為《米》所述的是“一個關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毀滅的故事”[12],主人公五龍“對抗貧窮、自卑、奴役、暴力、孤獨”[13]。誠如蘇童所言,五龍的確用盡了一身與一生的力量來對抗著城市帶給他的一切,馮老板和綺云對他的蔑視、織云對他的誘惑與拋棄、阿保對他的欺凌、六爺對他的恐嚇和威脅,碼頭兄弟會對他的背叛,城市的一切不斷激起他的仇恨,他將這些仇恨一一記在心里,并用他自己的方式還了回去:他氣死馮老板;先后娶了織云、綺云姐妹,將她們玩弄于股掌之間;向六爺告發阿保與織云的私情;裝神弄鬼地炸掉六爺的住所;最后以一張地契害死了碼頭兄弟會的成員。五龍在城市的壓迫中不斷地進行反抗與報復,他的心卻始終流連在遙遠的楓楊樹鄉村,他“作為楓楊樹的逃亡者,一方面始終懷有對農村根深蒂固的‘戀根情結,一方面對城市所發現的罪惡世界抱著對抗性的疏離”[14],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這米店的假人,我的真人還在楓楊樹的大水里泡著。”[15]盡管城市帶給五龍無窮盡的壓迫,但是他卻無法抵抗城市中糧食、女人、金錢和權勢的誘惑,“他的肉體卻在向他們靠攏、接近”。五龍一步步地在這個城市中得到女人、米店與碼頭,得到了他夢想中的金錢與權勢,得到別人對他的尊敬與畏懼,卻失去了自己健康的身體和單純的靈魂,最終染上性病死在了回鄉的火車上。
城市文化往往代表著先進與開放,鄉村文化則代表著落后與保守,于是大量的鄉村人懷揣著對城市的夢想而涌進城市,卻無法抵御城市中各種文化的侵蝕,城市中形形色色的壓迫與誘惑使得他們很容易就迷失了自己,最終陷入墮落的泥潭。無論是祥子的脆弱妥協,還是五龍的暴力反抗,似乎他們的結局只有那一個:墮落。
二、祥子的“車”與五龍的“米”
祥子的一生與“車”緊緊聯系在一起,買車“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16]。《駱駝祥子》中有兩條線索牽引著祥子的命運:一條是祥子買車的三起三落,另一條是祥子與虎妞之間不自然的結合,而祥子與虎妞的相識卻也是因為車,因此可以說“車”主導了祥子的整個命運。正如“車”是祥子的信仰,“米”就是五龍的信仰。大米的清香讓五龍感到親近與溫暖,他遠離家鄉之時隨身攜帶著家鄉生產的糙米,又跟隨著米店的板車來到米店,之后與米店一家糾纏了半輩子,最終載著一節火車車皮的米死在了回鄉的路上。“車”和“米”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祥子和五龍命運的主導,“車”和“米”是他們生存的關鍵,是他們內心深處鄉村文化的殘留,同時又是他們欲望的體現,是城市文化在他們內心深處的映射。
幾千年來農民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幾畝地上,只有土地和糧食能帶給他們生存下去的本錢,帶給他們安全感。祥子的“車”和五龍的“米”實際上是“土地”的化身,在城市中變成另外一種形式激勵著他們不斷為之奮斗。他們想融入城市,卻仍保留著鄉下文化的氣息,身體雖在城市之中,精神卻還是游離在城市之外,因而與城市格格不入。他們之所以生活得如此痛苦,“除了不得不忍受外界的壓迫剝削,還由于他們沒有擺脫作為個體勞動者的弱點。后者使他們的行動和反抗,常常帶有很大的盲目性。”[17]這樣的盲目性使得祥子在目睹了老馬與小馬兒以及二強子等車夫悲慘的生活之后,依然堅持著拉車、買車的夢,使得他明知道虎妞和他在一起是為了彌補她自己失去的青春,卻還是不得不依靠著她的錢買車、拉車,無法逃離那個漩渦。“車”已經由生存的必需品變成了生活中的壓榨物,甚至變成了祥子內心深處固執的欲望,他為此拋棄自己的道德和原則去和別人搶座兒,心里想著“要不是為了買車,決不能這么不要臉!”[18]為此拋棄娶個清白的姑娘的愿望心甘情愿地和虎妞生活在一起,“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19]。買車的欲望已經使得祥子喪失了自己最初的理想,也喪失了他從鄉間帶來的真誠與善良。
五龍的“米”更是代表了五龍赤裸裸的欲望。“米”最初代表的是五龍對生存的追求,在滿足了基本的溫飽之后,他渴望得到更高的滿足。在織云的誘惑之下,五龍釋放了自己壓抑許久的性欲,并一步步地先后娶了織云、綺云姐妹。有權有勢后就在城中找妓女,更養成了變態的性習慣——將米粒塞進女人的子宮。“每當女人的肉體周圍堆滿米,或者米的周圍有女人的肉體時,他總是抑制不住交媾的欲望。”[20]“米”已經成了五龍性欲的代名詞。除了生存欲望和性欲,五龍的權力欲也與“米”息息相關,他在碼頭兄弟會的地位最初便是靠一擔米換來的。“米已經不再是生存需求之物,而是整個生命內容、人性內容的荒誕因素”[21]。追求生存原本是人性之初,但在五龍“實現自己的追求與夢想的過程中,‘米逐漸成長為一株扎根在他心靈之上的惡之花,讓五龍體內惡的品性得到了培養,并最終導致他走向毀滅的深淵。”[22]對欲望放縱而無節制的追求,終于讓他失去了自我與人性,變得兇殘、暴虐,死于罪惡的城市文化手中。
祥子和五龍原本只是為了生存而執著地追求著“車”與“米”,卻不懂得讓自己更好的適應城市文化,甚至在城市的惡的文化影響之下,陷入了欲望的漩渦無法自拔,在追求失敗或者追求成功之后一味的放縱自己,喪失了人性。
三、結語
罪惡的城市文化帶給祥子和五龍無盡的壓迫與誘惑,對于來自鄉間的年輕人,無論是他們軟弱的承受或是盲目的反抗,都是他們與城市格格不入的表現,他們的精神只能游離于城市之外。然而他們卻也無法逃避和拒絕混亂的城市帶給他們的種種誘惑與滿足感,城市用它的形形色色誘發出隱藏在祥子和五龍人性深處的弱點——欲望。無論是“車”還是“米”,都是祥子與五龍內心深處欲望的體現,而對于欲望放縱地追求,必然會導致他們人性的喪失,他們只能一步步地走向城市的陷阱,走向墮落。
注釋:
[1][2][3][6][7][8][16][18][19]老舍.駱駝祥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0).
[10][11][15][20]蘇童.米[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12).
[4]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A].吳懷斌,曾廣燦.老舍研究資料(下)[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698.
[5][9]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節錄)[A].吳懷斌,曾廣燦.老舍研究資料(下)[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680,682.
[12][13]蘇童.急就的講稿[A].孔范今,施戰軍.蘇童研究資料[M].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21.
[14]鐘本康.兩極交流的敘述形式——蘇童《米》的“中間小說”特性[A].孔范今,施戰軍.蘇童研究資料[M].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180.
[17]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A].吳懷斌,曾廣燦.老舍研究資料(下)[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702.
[21]鐘本康.兩極交流的敘述形式——蘇童《米》的“中間小說”特性[A].孔范今,施戰軍.蘇童研究資料[M].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182.
[22]丁婧.宿命的惡之花——論蘇童《米》中“米”的主題意蘊[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