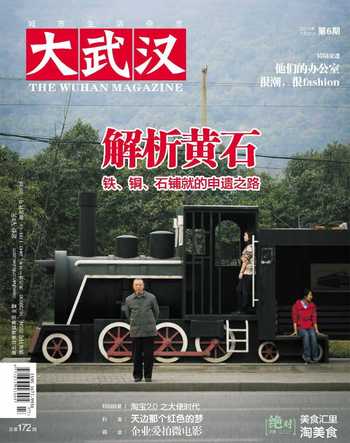地下60米,回望大冶鑄金
艾思思
公元前11世紀,中國商代晚期,荊州轄域一座名為銅綠山的礦山,一次進入山體的坑采完成,工人們掩埋住洞口后離開,將銅斧、木鏟等采礦工具遺留在礦道中。
公元197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4年,大冶縣銅綠山礦區正在緊張作業之中。機器電鏟揮舞著大手臂,一口就將山體啃下一塊,操控電鏟的礦工,在露出的山體中發現了十幾枚銅斧。
掩埋在泥土中的銅斧,沉寂了3000多年后重見天日。這是歷史創造的絕妙巧合,遠古與現代,因一枚銹跡斑斑的銅斧,進行了一次穿越時光的握手。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是此次黃石申請世界物質文化遺產中,唯一一處位于大冶的工業遺產。青銅與大冶,猶如水與魚的共生關系,相互依存了數千年。
因銅礦,大冶成
史前石器時代后期,青銅初現萌芽,古人已開始使用小件的青銅制品,將青銅鍛造成刀斧從事生產。
夏朝時,青銅被廣泛運用在祭祀與戰爭中,人類以青銅器的使用為標志,正式進入文明時代。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中國最大的銅礦帶,位于中原的國家權力中心,開始南下尋找銅礦,大冶銅綠山,因其產量大、品位高,成為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每到秋季,漫山遍野的銅草花開的紫紅;大雨過后,土石的縫隙中能隱約看見孔雀石,豆大一顆,隨著陽光映射閃著綠色的光芒,煞是好看。“銅草花,銅草花,有銅的地方就有它。”時至今日,每到雨后,稍有些經驗的礦工,都還能在銅綠山間撿到孔雀石。
從中原南下的商朝人,打開了銅綠山的資源之門。不僅開采銅礦石,并且就地冶煉,再將冶煉出的初銅運回中原。祭祀與戰爭,是一個封建王朝得以生存的必備活動,祭祀所用的禮器與戰爭所用的兵器,都需要大量的銅,在資源補給上,銅綠山功不可沒。
北方先進的制造工藝與文化,因為銅礦傳至荊楚,為了保證運銅通道的順暢,銅綠山周圍還建起了小型的城池,中原軍隊駐扎于此。
時間推移,此處因銅而興盛,直至宋朝,“大冶”之名正式確定,一座城市的名字,仍然與“冶煉”分不開。
偶遇古人坑采
1973年,黃功揚還是愣頭小伙一個,漢陽農村里出生,長大后離開武漢,在大冶一個銅礦里找了份差事,做了一名礦工。
“一鏟子挖出了青銅器”,隔壁銅綠山發現了古代采礦遺跡的大事,他還是從工友們口中聽說。當時的他沒想到,幾年之后,自己也成為了這件大事的親歷者,對于銅綠山的了解逐漸完整。而黃功揚的命運,也因為這座礦產豐富的山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今的銅綠山海拔53.8米,而據查閱史料與科學測算的結果,原始山體的山頂海拔在91.9米。失去的38.1米,是露天采礦的結果,一鏟子一鏟子挖下去的。看不見的山體內部,縱橫交錯著數不清的礦道,這是俗稱的“坑采”。現代技術下,坑采能夠深入山體兩、三百米,而古代技術有限,最多只能深入60米。于是,1973年的一次露天開采,在挖掘到60米的地方時,偶遇了古人坑采的痕跡,那些古老的作業工具被發現。
銅斧露面,挖掘停止,經過層層上報,驚動了當時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專家們,其中一位,便是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孔祥新。他們親赴銅綠山,將銅斧、木鏟等作業工具定下了時代:春秋時期,距今已有2700多年。又花了幾天時間,在銅綠山周邊走了一圈,驚訝地發現,這里漫山遍野都是古代的銅煉渣,并在煉渣堆里刨出了做飯用的陶器、生產用的石器等碎片。
有了采礦工具與煉渣,銅綠山的考古研究價值得以確認:這是一座春秋時期采礦與冶煉的大型遺址。這一發現,引起了湖北省文物界的極大重視,1974年,湖北省博物館考古隊前往銅綠山開始了考古發掘。隊長王勁,是當時全中國僅有的兩位女性考古學家之一,她成為了進入銅綠山遺址發掘的第一人。
古人的智慧
湖北省博物館考古隊在銅綠山待了整整一年,成功發掘出了兩個遺址點:一個是春秋時期,一個是戰國至漢代。發掘成果包括礦道遺跡、采礦工具和12只煉銅爐。
考古隊為時一年的發掘工作結束,隨后是歷時更久的古代采掘方法研究,全國最權威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派出專家隊伍,緊接著湖北省考古隊離開的步伐,進入銅綠山。
也是在這一次的行動中,黃功揚參與進來。為了擴大考古隊伍,湖北省博物館開設了一個培訓班,挑選其中的佼佼者加入銅綠山考古發掘的陣容中,黃功揚就是其中之一。從一名普通礦工到考古研究員,黃功揚說,因為銅綠山,他的一生都發生了改變。
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3000年前的古人智慧讓黃功揚甚為折服。將井口打在山坡上,利用水平高度差實現了自然通風;開采完畢的礦道即刻堵死,最大限度地保留住氧氣;橫向與豎向相互搭接的礦道,通過架設排水槽、用木桶逐層提升,順利將地下水排出礦道……在挖掘出的12只煉爐中取出的高溫耐火材料,竟然與現代高爐中的耐火材料成分大致相同。
保護比挖掘更難
引水用的木槽,挖土用的木鏟、木鍬,這些深埋千年的木頭,被山中的泥土吸盡了水分,變成極優質的木柴,用它燒出的柴火,顏色通綠,火焰旺的不得了,比如今的煤氣還好用,成為銅綠山周圍村落人們的“搶手貨”。村民們在一旁等著考古隊的收獲,挖出一批木頭便蜂擁而搶,考古隊苦勸無用,和村民發生了好幾次沖突。
一邊艱難的考古發掘,一邊與村民斗智斗勇。湖北省電影制片廠被請來了,在村里架起放映機,播放關于考古的電影,通過影片給村民們宣傳考古知識。黃石軍分區甚至排出了一個排,開赴銅綠山維持秩序。
考古發掘研究結束,銅綠山的12個礦體中,有7個均發現了古代采礦遺跡。甄選之后,留下了保存最完好、歷史最悠久的7號礦體遺址,在原地建起了一座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館藏有挖掘出土的青銅斧、采礦使用的木鍬、木鏟等珍貴文物,并在發掘出的采礦作業現場遺址之上,原地修建了保護性建筑。
12只完整出土的煉銅爐,均因為保管不善等原因相繼破損毀壞,黃功揚從一堆煉爐殘片中搶修出一只,如今安置在湖北省博物館楚文化展廳的進門處。
煉爐修復完成不久,遺址博物館面臨了更大的一場風波。銅綠山及周邊的一眾山脈,因豐富的銅礦資源聞名于世,歷經數千年的開采,至今仍是中國最重要的銅礦產地之一。遺址博物館的建立,意味著其所在山體將不能進行銅礦開采,對于礦山所屬公司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損失。“銅綠山遺址博物館下面,至少埋了200個億!”遺址保護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張國祥說。
有人提出了博物館的遷移計劃,將整個博物館東移400米,從山頂搬到半山處,避開銅礦開采區。為了保證館內古銅礦遺址的完好,有關人員甚至已前往俄羅斯考察搬遷技術。但是,搬走之后的古銅礦就不再是遺址,只能稱為文物了。礦山所屬公司將搬遷報告打到中央,湖北省人民政府為此召開的常務會議也報向中央,最終,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羅干定奪,保下了銅綠山古銅礦遺址。
最接近的一次申遺夢
1994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第一次申報世界物質文化遺產,這本是一件十拿九穩的事情,一經申報即列入了國家預備名單。
自上世紀70年代遺址發掘后,銅綠山在世界考古界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它不僅打破了國際上流傳甚久的“中國無銅說”,更以其完備的采、煉產業鏈條為世人所贊嘆,“從沒有過這么完整、規模如此巨大、采礦與冶煉并舉的遺址。”
世界教科文組織專門派來了專家考察,對銅綠山遺址本身無一異議,只提出了一個建議:改善一下遺址博物館的周邊環境,修幾條好路。要求不高,但實施起來卻不太容易,當時的銅綠山與遺址博物館,分屬黃石與大冶兩市管轄,一再磋商都未能成行。
幾年后,受到周圍開礦施工的影響,博物館出現了地表開裂和沉降,被迫閉館四年。“閉館了,也就意味著被取消了預備名單資格。”盡管在2010年,博物館經過大規模翻修后重新開館,再次申遺卻必須重新開始,而如今的申報門檻,比起10年前要嚴苛的多。
新一代大冶人:與銅無關的生活
“你去大冶街上看看,全是好車。”在黃石人眼中,大冶人很有錢。很長一段時間,大冶的銅礦支撐起了這座城市的經濟,但是如今富裕的大冶年輕一代,與青銅的關系卻不再緊密。
老一輩的大冶礦工,依然生活在礦業國企的體制之下,他們的子女,會得到一個頂替父輩名額進入礦山工作的機會,但是這樣一份現成的工作,也不太有人愿意去了。辛苦勞累的開礦活兒,大部分交給了來大冶打工的外地人,在這其中,以江浙人居多。大冶本地人,尋思的是如何包下一個小礦,或是倒賣礦砂,這可比當礦工賺的多。
更有一批人,走南闖北做起了“包工頭”,盡管大冶市區那些歷史悠久的老建筑已不多見,但是古城里出生的人們,似乎骨子里就有一份歷史情結。“你看全國到處都在興建的仿古建筑,好多都是大冶人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