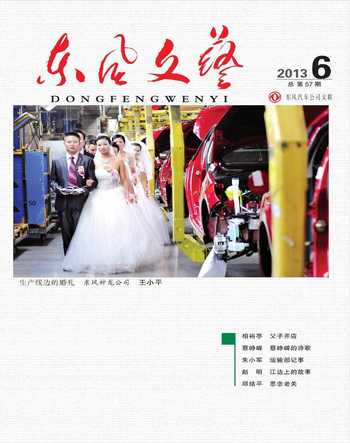我不是白璧無(wú)瑕的少年
王征珂
我不是白璧無(wú)瑕的少年,我也曾經(jīng)行為齷齪。那是初中三年級(jí),洪湖縣桃園中學(xué),中考備戰(zhàn),風(fēng)聲吃緊。一天晚上,晚自習(xí)結(jié)束了,同學(xué)們像一群飛鳥(niǎo),紛紛散去,返回安寧的巢穴,我卻鬼迷心竅,龜縮在校園的某個(gè)陰暗角落里。夜色漆黑漆黑,伸手不見(jiàn)五指,我心懷鬼胎,鬼鬼祟祟,翻窗進(jìn)入教室,偷走了男生甲遺落在抽屜里的《全國(guó)中考優(yōu)秀作文精選》。我以為我的偷盜行為神不知鬼不覺(jué),其實(shí)蛛絲馬跡已經(jīng)被人暗中掌握,學(xué)校那個(gè)花白胡子的看門(mén)老頭,平時(shí)總是喜歡點(diǎn)頭哈腰、弓腰駝背,那天晚上突然挺直了脊梁,一臉嚴(yán)肅,一身正氣,氣沖霄漢,向我的班主任老師檢舉揭發(fā)我的無(wú)恥行徑。那是一個(gè)令我們?nèi)颐尚叩囊雇恚猩缀退哪赣H急急來(lái)到我的家里,當(dāng)場(chǎng)截得贓物,完璧歸趙。
現(xiàn)在回想起來(lái),男生甲的母親多么含蓄,多會(huì)說(shuō)話呀!她見(jiàn)到我的母親,不說(shuō):“你家兒子偷書(shū)啦”,而是說(shuō):“你家兒子是不是拿錯(cuò)東西啦?”——她給我那目瞪口呆的母親留著面子。對(duì)于我犯下的錯(cuò)誤,我的母親當(dāng)然聽(tīng)話聽(tīng)音,心知肚明,臉羞成了一團(tuán)火燒云,人變成了一個(gè)啞巴子,她二話不說(shuō),沖到我跟前,“叭叭叭”就搧了我?guī)锥猓虻梦夷樀皟夯鹄崩保虻梦夷X袋瓜嗡嗡響,打得我仿佛一只人人喊打的過(guò)街老鼠,想要尋找藏身的地洞。男生甲和他的母親離開(kāi)我家以后,嚴(yán)厲的家庭懲罰仍然在繼續(xù):罰跪,面壁思過(guò),反復(fù)學(xué)習(xí)民間俗語(yǔ),沉痛檢討我自己:小時(shí)偷針,長(zhǎng)大偷金;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我的臉上濕漉漉的,眼淚混合著鼻涕;我的心頭灰蒙蒙的,自卑伴隨著懊悔。
我不是白璧無(wú)瑕的少年,我也曾經(jīng)使壞作惡。在桃園村的樹(shù)林那邊,長(zhǎng)著圓滾滾、甜滋滋的西瓜。看守瓜田的壯漢,那天中午回家吃飯去了,我長(zhǎng)出了豹子膽,竄進(jìn)瓜田,朝可愛(ài)的西瓜下手。那時(shí)的我,好像一只饞貓,嘴上流著甜蜜的汁液,心上敲著咚咚的小鼓。當(dāng)我正在狼吞虎咽,遠(yuǎn)處傳來(lái)了看瓜人沖天的大喊。我是他口里的“兔崽子”,撒腿就跑,腳下是嘩啦啦的瓜秧,頭上是火辣辣的太陽(yáng)。瘦骨嶙峋的我,跑光了力氣,差點(diǎn)跑斷腿子,跑不贏看瓜人。虎背熊腰的看瓜人,攆上我,抓了我的“現(xiàn)行”。那個(gè)看瓜人,像老鷹拽著小雞,把我拽到我家門(mén)口。在屋子里迎接我的,是父親眼睛里的熊熊火焰,喉嚨中憤怒的吼叫:“我們王家前世究竟作了什么孽?今世出了你這個(gè)不曉得羞恥的畜生!”
我不是白璧無(wú)瑕的少年,我也曾經(jīng)愛(ài)慕虛榮。雖然我生長(zhǎng)在江漢平原一個(gè)經(jīng)濟(jì)拮據(jù)的家庭,卻偏偏喜歡“裝酷”:我穿著粗布衣裳,想著華美的服裝;看著空空如也的手腕,想著風(fēng)風(fēng)光光的手表。那時(shí)我多想有一套中山裝呀!哪怕是半新半舊的;我多想有一塊“上海”牌手表啊,哪怕是人家用過(guò)多年的。
現(xiàn)在我還清楚記得,1986年夏天,洪湖縣大沙湖農(nóng)場(chǎng)的一個(gè)干部子弟,說(shuō)要帶我去趟省城,去“大漢口”逛逛,去開(kāi)開(kāi)眼界,見(jiàn)見(jiàn)世面。因了這個(gè)干部子弟的反復(fù)鼓動(dòng),更因了我的虛榮心作怪,我跟隨這個(gè)干部子弟一道,從大沙湖小鎮(zhèn)長(zhǎng)江碼頭出發(fā),乘坐輪船前往幾百里外九省通衢、五光十色的省城。
在熙熙攘攘的漢正街,在五彩繽紛的六渡橋,各種時(shí)髦服裝讓我眼花繚亂,我是一個(gè)鄉(xiāng)巴佬、窮光蛋,囊中羞澀。如果僅僅只是“過(guò)過(guò)眼癮”也就罷了,然而,私欲已經(jīng)充塞我心,虛榮已經(jīng)將我籠罩。和那個(gè)干部子弟分手以后,我被鬼使神差著,尋尋覓覓,汗流浹背,用了半天時(shí)間,終于找到我的舅舅。
我那年過(guò)半百的舅舅,早已經(jīng)從漢口鄱陽(yáng)街搬遷到青年大道。好幾年未見(jiàn),他已鬢染白霜,蒼老許多。對(duì)我的突如其來(lái)、只身前往,他先是很有些吃驚,接著就問(wèn)長(zhǎng)問(wèn)短:你媽媽身體么樣?家里莊稼如何?豬娃養(yǎng)了幾口?全家生活困不困難?三個(gè)兄弟學(xué)習(xí)成績(jī)可好?一口濃重湖南腔的舅舅,仔細(xì)詢問(wèn)。
面對(duì)舅舅的詢問(wèn),有一些小文采的我,充分發(fā)揮了語(yǔ)言表達(dá)能力,我說(shuō)家里艱難困苦,我說(shuō)高中缺少生活費(fèi)用,說(shuō)得我舅舅一臉沉重,淚水奪框而出。雖然我講的并沒(méi)有偏離事實(shí),但是用心一點(diǎn)也不單純。我一連串繪聲繪色的講述,很快感動(dòng)了舅舅:他摘下“上海”牌手表,堅(jiān)決戴到我的手腕上;他領(lǐng)我去中南商業(yè)大樓,給我買了一套新嶄嶄的衣服。
當(dāng)我從武漢回到大沙湖農(nóng)場(chǎng),從學(xué)校回到三十里外的家中,母親反復(fù)追問(wèn)中山裝和手表的來(lái)歷,我撒謊說(shuō),是那個(gè)干部子弟送給我的。母親怎么都不肯相信,硬是逼我說(shuō)真話。心虛氣短的我,交代了真相。母親聽(tīng)了,渾身不停顫抖:“丟死人!不要臉!小小年紀(jì),為么事這樣自私、下作?”掃帚,狠狠打在我的背上;斥責(zé),像鞭子抽打著我的內(nèi)心。
許多年了,雖然我早已經(jīng)改邪歸正,完成學(xué)業(yè),參加工作,成家立業(yè),父母還時(shí)常叮囑我,莫要貪人家東西、沾人家便宜,莫要愛(ài)虛榮、養(yǎng)成壞品性。今夜,在恩施州利川市,在湖北省青年作家高級(jí)研修班的宿舍里,我寫(xiě)下舊事二三,對(duì)自己再作一個(gè)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