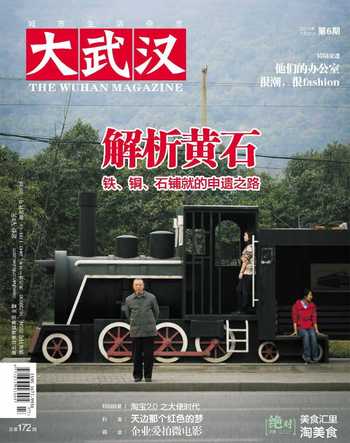張執浩專欄
張執浩,詩人,小說家。現居武漢。主要作品有詩集《苦于贊美》、《動物之心》、《撞身取暖》,小說集《去動物園看人》,及長篇小說《試圖與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隊》、《水窮處》等。
這算不算懺悔
隆冬的一天,兩個少年闖進了一座人去樓空的廠房里,無意間發現房屋的椽梁上棲滿了密密麻麻的黑點,細看才知是麻雀,一樣大小,一樣毛色,一樣驚恐如漫無目標的箭矢。那是知青們匆忙撤離時留下的一間儲存過糧食的房屋,地上散落著數不清的谷粒。屋頂足足有十多米高,靠外墻的一邊有數十扇覆滿塵埃的玻璃窗。當他們在“吱呀”聲中撬開房門時,原本安靜的屋子突然沸騰起來。黑壓壓的麻雀驚叫著,不顧一切地朝玻璃窗撞去,結果昏頭昏腦地落在了地上,它們就那樣翻滾著,抖動著細爪,撲打著翅膀,露出灰白相間的肚腹,眼睛依舊圓睜著,不甘心地留戀著這原本屬于它們的世界……少年在短暫的驚愕之后,很快就歡呼雀躍起來。他們飛快地將書包扔在墻根下,順手抄起地上的石塊、棍棒朝飛鳥們擲去。麻雀繼續像冰雹一樣落了下來,不一會兒,只剩下了稀稀落落的幾只躲在屋梁上,腳趾緊抓著冰冷的三角鐵。少年倒掉書包里的課本和文具,開始彎腰撿拾滿地昏死的麻雀,把它們一一裝了進去。之后,他們又從屋外找來長竿,企圖將剩余的鳥兒全部殲滅。直到精疲力竭,他們才看見玻璃窗上方有幾個破損的洞口,一只麻雀伺機飛了出去,接著,另外幾只也飛了出去。
在回家的路上,兩個少年不時地將手掌從緊扣著的書包口袋里伸進去,興奮地觸摸著麻雀們的身體。在黑暗中,這些凌亂的羽毛依然溫熱,散發著他們不熟悉的味道,那應該是天空的味道,只是他們那時還說不出來。麻雀在蠕動,但顯然已經喪失了掙扎求生的氣力,不久之后便完全放棄了任何動作,小巧的身體也慢慢變得冰涼起來。“你總共抓到多少只?”一個問另外一個,另外一個用手在書包里摸索著,然后回答:“58只。你呢?”在一番摸索之后,風中傳來這樣的回答:“67只。”“不公平!”兩個少年吵了起來,多的那個開始往前飛跑,少的那個跟在后面追。他們就這樣在隆冬的曠野里你追我趕,鼻尖上的汗水在向晚的清風中與稀薄的鼻涕混在了一起。當他們氣喘吁吁地跑下一段塘堤后,前面的那個停住腳步,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后面追來的那個說道:“跑不動了,來,來,我們平均分配吧。”他們將各自的書包扔在地上,將所有的麻雀一古腦地倒了出來,攏在一起,然后你一只我一只地分贓起來。總共125只,每人分得62只,多出1只。怎么辦?“把它燒掉吃了。”一個提議道,另外一個說好。但問題接踵而至:1只麻雀怎么夠兩個人吃呢?“這樣,我們每人再拿出2只,5只夠了吧。”他們決定馬上生一堆火,在天黑之前把5只麻雀烤熟吃了回家。
5只麻雀被串在一根棍子上,心平氣和地接受了烈火的炙烤,先是羽毛,然后是皮肉,最后,它們變成了5坨焦糊的鳥肉。兩個少年都是第一次干這活,他們對即將到口的麻雀肉是否好吃缺乏把握。他們各自扯下一條麻雀腿,放進嘴里謹慎地咀嚼著,發現味道不錯,事實上,豈止不錯,簡直鮮美之極。很快,他們就狼吞虎咽起來,甚至連內臟都沒有放過。然后,他們心滿意足地回家,將滿書包的麻雀作為這一天的額外收獲奉獻給了父母。
我就是這兩個少年中的一位。多年以后,每每念及那個隆冬的午后,內心里還會產生一陣悸動。這悸動近乎麻雀落到地上之后的抽搐,短暫而明了。
“我是一個自學成人的人。”在一首詩中我曾以此檢索過往的人生,得到了很多同道的呼應。在我的整個童年少年時期,從來沒有人教我該如何去尊重另外的生命。把一只螞蟻捏死,把一條蛇打死,把一只狗吊死,把一只烏龜燒死,把一條蜈蚣砸死,把滿樹的梨花搖落,把滿山的松樹鋸掉……我不知道,生命意味著什么,殺戮早已成為代代相傳,技藝越來越精湛的傳統,我只不過是順應了它。活著,吃,吃肉,吃稀有的肉……我曾親眼目睹大人們活捉豪豬,用力拔扯它身上豬毛的場景,又粗又長的灰白色豪毛被使勁拽下,豪豬在慘叫,我得到了一把沾滿血跡的豪毛,轉身拿去做了魚漂。
在我上學必經的路上有一片竹園,我時常側身而入,在里面轉悠。竹林高大茂密,有的足足有碗口粗細。我仰頭望著艷陽婆娑的竹梢,很快就看見了幾只鳥窩。我曾在同一只鳥窩里掏到過數枚鳥蛋,有一年暮春,我爬到鳥窩旁,看見里面有幾只新生的小鳥,我把它們裝進口袋帶回了家。雛鳥還沒有羽毛,除了一只長出了稀疏的絨毛外,其余幾只光溜溜的,肚皮渾圓熱乎。它們的皮膚真是輕薄啊,從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見它們的內臟,幾乎吹彈即破。當我把手指伸過去時,它們緊閉著眼睛,大張著柔嫩的口喙,唧唧喳喳地爬過來。我給它們吃從田間捉來的蚱蜢,以為能把它們養大。但沒過幾天,一只只都死掉了。而至死,我也不清楚它們是什么鳥。這樣的死亡或許是這世間微不足道的死亡,我不在乎,但卻長埋于我心間。
昨天晚上,一幫朋友在東北烤肉店閑聊,話題慢慢轉向了我記憶深處的那群麻雀,我見過的場景其實大家都見過。半夜回家,再次路過那一樹梅花,我在黑暗中怔怔地看著,再也不會走過去將它們搖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