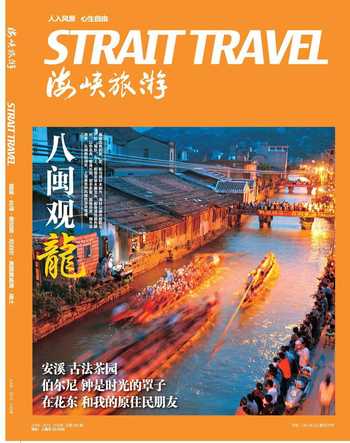耕園小老板的新瀉家鄉(xiāng)味
耕園的網(wǎng)評里,不少人提到人很好的日本老板娘和一道可口的蛋卷。然而當我坐進店里,88年生人的佐谷優(yōu)樹在我對面出現(xiàn)時,我還是小吃驚了下。
我指著吧臺邊笑咪咪的姑娘皮皮問:那這位老板娘是您夫人?
“不是,她是老板娘,但不是我夫人。”
在這個日本小伙子和我們談居酒屋文化前,我真想好好問一下,是不是有人和他傳達過錯誤的“老板-老板娘”關(guān)系鏈?
耕園與勝相比,少了幾分精致,多了些許日式的家常味道。耕園的店面一分為二,左邊供單獨或者少數(shù)結(jié)伴而來的好友用餐喝酒,狹長長一條,有居酒屋轉(zhuǎn)不開身來的意思;右邊則類似一個小包間,能坐下七八個好友大喝一頓。居酒屋墻壁上貼著的都是優(yōu)樹自己用毛筆寫的菜名,不知道不會用毛筆的他花了多少時間寫滿了這一整面墻。除了三名店員,優(yōu)樹也兼任了“廚師+服務(wù)生”的角色,而店里備受好評的蛋卷和芥茉章魚,都是優(yōu)樹從小和外婆一起生活偷師學來的。“我從來沒有專門學做菜,都是和外婆一起住的時候看會的,你知道新瀉嗎?新瀉的菜最好吃,我們家是新瀉人。”聽優(yōu)樹這么說時,新瀉突然就從一個平面的“東京-新瀉站”變得滋滋有味起來。或許真的是新瀉菜味道誘人,又或者只是想念故土一味家常的味道,耕園里日本的老客常常一周五天待在店里吃吃飯喝點酒,除了晚餐時間,耕園的熱鬧集中在晚上十點以后,微醺的客人們開始舉著居酒屋里兩只舊麥克風唱起K來,電視前放著的VCD都是些老歌,新不了情和紅豆據(jù)說是點唱大熱,一杯燒酒,一碟厚蛋卷和小章魚,在雨夜里有唱有和地來一首新不了情,實在不能再應(yīng)景了。
留學廈大學完中文的優(yōu)樹因為喜歡廈門而決定只身留下,并在廈禾路開起了耕園的分店主營料理。同在廈大的弟弟卻因為“個性完全不一樣”而想著一畢業(yè)就回家。面對日后要和“耕園”相依為命的日子,優(yōu)樹似乎并沒有覺得寂寞。“店里來了很多客人,各式各樣,你會看著一個男客人先是單身來喝酒,有一天突然帶著女朋友來了,再過一陣,他又換了個女朋友……還有一些單獨來的女客人,心情很不好,在店里喝多了,我們就會打給她朋友,讓人來接她回家。”中文不是特別順溜的優(yōu)樹只能說出幾個樸實得要命的故事,卻因為這個溫暖的小小居酒屋,讓這些表達不清的小故事,渲染上一層淡淡的人情味,毫不設(shè)防地穿插到你的記憶和人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