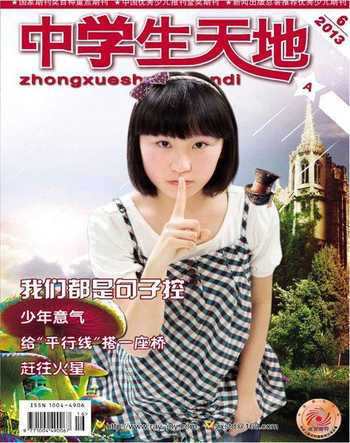趕往火星
李劍龍
1845年5月19日,富蘭克林爵士指揮著排水量都超過300噸的“幽冥號”和“驚恐號”起航,同128個隊員一起前往北極地區進行探險。船上裝備齊全,供給和燃料堆得像山一樣高,有精美的銀器、瓷器和玻璃器皿,甚至還有為制服的黃銅紐扣配備的磨光器。但人們再也沒能看到探險隊活著回來。
大不列顛海軍部提供了高額賞金,并不斷派出搜索隊尋找失蹤者的下落。經過了50多次遠航,失去了更多人員和船只之后,人們才從支離破碎的線索中得知,這支探險隊在兩年間耗盡了全部給養,最后在饑寒交迫中全軍覆沒。
富蘭克林的失敗在于,他試圖將歐洲舒適的生活環境原封不動地搬進北極。大約60年后,另一位探險家阿蒙森帶著6位船員重新踏上了富蘭克林的探險之路。阿蒙森吸取了前輩的教訓,采用了一種因地制宜的生活策略。他們像愛斯基摩人一樣,用馴鹿內臟和生鯨脂來對抗壞血病,乘坐狗拉的雪橇,制造冰屋,用鹿皮做衣服。于是,他們在富蘭克林探險隊覆沒的環境中活得生機勃勃,還獲得了不少重要的地理發現。1911年,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首次抵達了荒無人煙的南極點。
100年之后,火星成了人類下一個想要挑戰的目標。火星的公轉軌道比日地距離遠7000多萬公里。如果你乘坐時速300公里的高鐵,要經過28年才能走完這么遠的路。如果乘坐速度高達每秒27公里的太空飛船,這段旅途仍然要花費6個月的時間。注意,火星和地球都在繞太陽公轉,每過兩年才會相互靠近一次,太空飛船的軌跡不可能是直線。所以,如果探險隊員在火星安然著陸,他們必須在火星上堅持生活一年半,才能再次踏上回家的路途。
火星的環境比北極和南極更加嚴酷。雖然沒有冰雪覆蓋,但火星的平均溫度也只有攝氏零下60度。火星的表面重力只有地球的40%,但走起路來并不會感覺輕松,因為它的大氣壓強不到地球氣壓的1%,而二氧化碳卻占大氣成分的95%以上。這些不利因素使得造訪火星成了一個既燒錢又充滿悲壯色彩的任務。1989年,美國航空航天局的一份報告估計,登陸火星將花費4500億美元。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政府愿意為成本如此昂貴的探險計劃埋單。雖然荷蘭一家私人公司愿意通過商業運作籌措資金,有志在未來的10年內將人類送上火星,并建立永久殖民地,但他們直言不諱地說:“參與者都應該意識到,一旦這項計劃成功實施,他們就再也回不來了。”
這些困難看似不可戰勝,也許只是因為人們沒有靈活運用阿蒙森因地制宜的經驗。美國著名航空航天工程師羅伯特·祖布林博士在《趕往火星》一書中提出了一項名為“火星直擊”的絕妙計劃。顧名思義,這個計劃舍棄一切不必要的彎路,無需在近地軌道組裝飛船,無需在太空補充燃料,無需擴大空間站的規模,無需擴充月球基地。開發這項計劃的所有硬件僅需耗費300億美元,之后每次飛行只耗費30億美元。而且,宇航員可以重返地球,不必客死他鄉。
把宇航員送回地球的瓶頸在于燃料。若想讓45噸重的返地飛行器飛回地球,大約需要消耗96噸的甲烷/氧氣雙組元推進劑。但是,要將燃料和飛行器一起送到火星,又得再消耗額外的燃料,將這些額外的燃料發射升空又要消耗更多燃料……祖布林想,為什么不能像阿蒙森吃鹿肉、造冰屋、坐狗拉雪橇一樣,利用火星當地的資源呢?
在祖布林的設想中,首先向火星發射的,不是載人飛船,而是一個無人駕駛的返地飛行器。它沒必要攜帶全部返程燃料,只需要帶6噸的液氫作為原料就夠了。除了維生系統之外,返地飛行器還需要攜帶一個小型核反應器,一個自動化化學處理單元和一個壓縮機。一旦在火星表面平安著陸,一輛攜帶核反應堆的輕型卡車將緩緩駛出,在地球科學家的指引下來到火山口之類的凹陷處,開始將100千瓦的電力輸送至化學處理單元。
化學處理單元,其實就是一個“迷你化工廠”,它源源不斷地從火星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CO2),將它與自己帶來的氫(H2)結合,產生甲烷(CH4)和水(H2O)——這可不是什么高科技,人們早在煤氣燈時代就已在工業中運用這個簡單的化學反應了。甲烷儲存起來作為燃料,水則繼續裂解成氫氣和氧氣。同時,另一個設備也會將二氧化碳分解成氧氣和一氧化碳。氧氣儲存起來作為燃料,氫氣繼續進入化學反應的循環,而其余氣體則作為廢氣排放。經過6個月的工作,返地飛行器上就會集齊108噸燃料,除了用于返程,還多出12噸燃料可以留給后來的火星車輛使用。
又經過6個月的漫漫旅途,第一批四人一組的火星宇航員就會和另一個返地飛行器先后抵達火星上空。這個新的返地飛行器原本是計劃留給兩年后的第二批宇航員使用的,但是萬一第一批隊員沒能在第一個返地飛行器附近著陸,第二個返地飛行器就會立刻投入使用。
四位宇航員會在火星待上500天,經過緊張的科學實驗和野外探險之后,又會乘坐返地飛行器重新回到地球的懷抱。地球上的人們會像迎接新時代的哥倫布一樣歡迎他們的回歸。緊接著,第二批宇航員又踏上了前往火星的征途。
“火星直擊”計劃并非完美無缺。盡管美國之前發射的火星探測器在火星上毫無障礙地運行了數年,但誰也不能保證這么多高精尖設備絲毫不出現故障。畢竟,人類首次登月時,月球上的返回艙就險些無法點火。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的悲劇也都源于人們始料未及的小紕漏。但是正如祖布林所說,即使再等上一代人的時間,這些風險還是會存在。
“不冒險,不成就;無勇氣,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