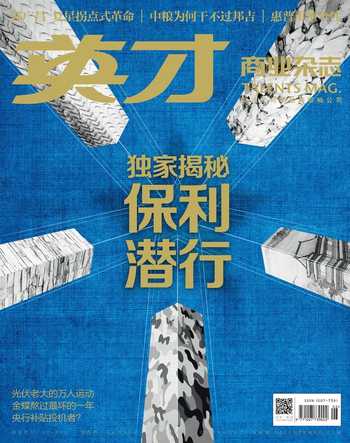需求管理已至末路
李揚(yá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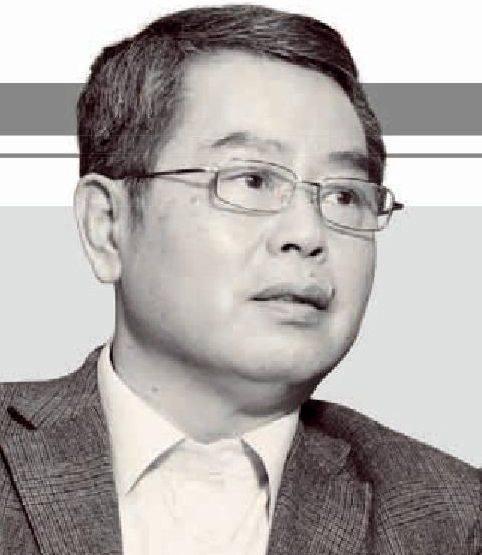
2013年一季度宏觀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顯示,GDP增速一下子降到了7.7%,社會(huì)消費(fèi)零售總額增長(zhǎng)率下降,PPI也下降了。這些都讓經(jīng)濟(jì)學(xué)界感到吃驚,但最讓人吃驚的是財(cái)政收入出現(xiàn)下降,其中中央財(cái)政收入幾十個(gè)季度以來(lái)首次負(fù)增長(zhǎng),這讓我們感覺(jué)壓力很大。
出口情況還可以,但是3月比2月下降3.6%,這也有點(diǎn)兒讓人吃驚。固定資產(chǎn)投資比較穩(wěn)定。總的來(lái)說(shuō),經(jīng)濟(jì)形勢(shì)在企穩(wěn),但有一定下降趨勢(shì)。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將在新的較低的次高速平臺(tái)上運(yùn)行,這將成為常態(tài),是經(jīng)歷過(guò)35年高速增長(zhǎng)后的正常調(diào)整。現(xiàn)在到了可以切實(shí)解決過(guò)去發(fā)展模式中存在的問(wèn)題的時(shí)候了。我們要更加追求沒(méi)有水分的增長(zhǎng)。
增長(zhǎng)中的水分大多與投資有關(guān),一邊是很高的增長(zhǎng)率,一邊是產(chǎn)能過(guò)剩,這兩種矛盾并存很長(zhǎng)時(shí)間了,并且愈演愈烈。這與傳統(tǒng)的投資帶動(dòng)的發(fā)展模式有關(guān)。現(xiàn)在到了改變這種發(fā)展方式的時(shí)候了。面對(duì)增速下滑的情況,有一些刺激經(jīng)濟(jì)的呼聲。我本人堅(jiān)決反對(duì)這種政策取向。
目前的財(cái)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jīng)是相當(dāng)擴(kuò)張的。財(cái)政政策方面,收入速度下降了,但是支出保持穩(wěn)定甚至有所增加,結(jié)果是赤字在增加,是積極的擴(kuò)張性的財(cái)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一季度M2增長(zhǎng)15.7%,貸款增長(zhǎng)14.9%,社會(huì)融資總量增加2.27萬(wàn)億,這些數(shù)字均超出預(yù)期。因此,從數(shù)量指標(biāo)來(lái)看,貨幣是擴(kuò)張的。此外,利率下跌,國(guó)債收益率下移,也是貨幣擴(kuò)張的明確指示。如果此時(shí)再放貨幣、壓低利率,在財(cái)政方面進(jìn)行擴(kuò)張,后果將非常嚴(yán)重,所以不宜進(jìn)行刺激。
面對(duì)這樣的局勢(shì),今后的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要進(jìn)行改變。我本人認(rèn)為必須立刻止住需求管理。這些年要刺激就出臺(tái)4萬(wàn)億、9.6萬(wàn)億貸款,以至于M2/GDP比重從1982年開(kāi)始不斷攀升,直到2005年才止住上升勢(shì)頭,2009年又跳躍上升,這是由于政策造成的,我們把需求管理用到了非常過(guò)分的程度。
事實(shí)上,金融危機(jī)以來(lái),全世界都在大劑量的使用需求管理。美聯(lián)儲(chǔ)多年維持超低利率;歐洲央行開(kāi)始擴(kuò)張;日本高調(diào)推行“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表示要搞負(fù)利率、正通貨膨脹,無(wú)限制購(gòu)買(mǎi)債券,導(dǎo)致日元貶值。
美元在泛濫、歐元在泛濫、日元在泛濫、人民幣在增長(zhǎng),未來(lái)會(huì)如何?現(xiàn)在誰(shuí)都不敢去做預(yù)測(cè)。引用資本論中“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世界各國(guó)都沒(méi)有明確的機(jī)制來(lái)回收貨幣。
需求管理變成一種維穩(wěn)手段,卻延緩了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而中國(guó)的問(wèn)題就在結(jié)構(gòu)和發(fā)展方式上,不調(diào)整結(jié)構(gòu),這個(gè)危機(jī)是過(guò)不去的,但是大劑量的需求管理使得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問(wèn)題無(wú)限度延后。
需求管理已至末路,必須排除萬(wàn)難把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放在第一位,宏觀政策轉(zhuǎn)向供應(yīng)管理,這已成為一個(gè)共識(shí)。總的來(lái)說(shuō),供應(yīng)管理要使得供應(yīng)機(jī)制市場(chǎng)化,政府少干企業(yè)多干,激發(fā)企業(yè)調(diào)整的活力,企業(yè)承擔(dān)調(diào)整的責(zé)任,同時(shí)獲得調(diào)整的收益。解放各種限制要素價(jià)格的束縛,勞動(dòng)力、土地、資金能夠自由流動(dòng),價(jià)格能反映供求。釋放改革紅利,這是供應(yīng)管理的關(guān)鍵,最重要的是劃清楚政府和市場(chǎng)的界限,市場(chǎng)能做的交給市場(chǎng),把政府的手砍斷裝上市場(chǎng)的手。(作者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根據(jù)公開(kāi)演講整理,本文僅代表個(gè)人觀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