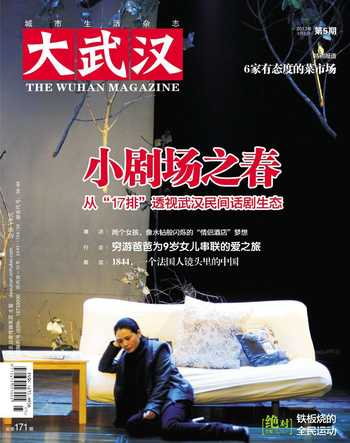“搭頭”生意
顏發順藥酒老店雖小,可是個獨立的鋪面,在大漢口還有比它更小的生意,是“搭”著人家做的。
鄒協和金號在成為金號之前,是搭在別人鋪子里,租半個門面開的銀樓房。
這種“搭頭”生意,一方面是當“搭頭”的老板本小利微,能力有限,租不起整個鋪面;另一方面是擁有鋪面的老板生意不景氣,租出半邊為自己省一點花銷。
這樣的“搭頭”生意門面,有許多是左半邊和右半邊八不沾邊,兩家“打鑼賣糖,各做各行”。
于是,各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搭配就出現在“大市長街”之上了。
有一家仁記面鋪,專營韭葉面、龍須面等各種干面條。生意興隆時各處的販子擠在他家三間頭的鋪子里,找板凳都要“前客讓后客”。后來生意蕭條了,他們家就讓一對老夫妻把香煙攤子擺在他家大門右邊的角上,讓煙攤應名有了一點鋪面的意思,他家也有一小筆租金聊作補充。
一家“炭圓鋪”(煤炭店)生意興隆時,又請人工又招學徒,鋪子后頭的“做場”一天不停地和料搖煤球,老板總說門面小了,恨不得找個地兒開分號。后來生意不行了,老板慌忙火急就把門面租了一半,讓人家開了個車木店,這一來這個門面就好看了:一邊擺的是車木頭的土機器和那些白白黃黃的木扁擔之類的產品,一邊是烏漆抹黑的煤球,兩種生意你看我、我看你,誰看誰都是別人的“搭頭”。
一家酒坊租一半給刻字匠,店堂里原本放張把桌子的地方沒有了,“酒麻木”們從前可以安坐一會,就地過酒癮的地方,此時只能讓他們站著喝了。日子一長他們就換了別家。這酒坊的生意就更加清淡了。還有更妙的:小百貨店租一半給了賣紙錢的,活人生意和死人生意混在一起做。參燕號租出一個角落讓別人賣黃松糕,街坊們評論他們的說法是:“賣補品的塌了架子,賣松糕的是個輕骨頭。”
這種為了救窮而形成的胡亂搭配,幾乎走一段路就可以發現一處,他們是為了救窮而“就”在一起的,在一處“就”得便極別扭,別扭一段便拆伙各奔東西了。
但大漢口到底是大都會,許多生意互相依存,使更多的搭配成為黃金搭檔。
中藥鋪在行內稱“飲片店”,它的大宗生意就在“照方抓藥”上,中醫師和中藥鋪在一起,那就說得上是絕配了。人們經常見到的是大中藥鋪必有“坐堂醫生”,他開方子柜上抓藥,配合得很是嚴謹,就像是一家人。有的小型中藥號本身就是醫生開的,開單子發藥更是一家人了。實際上有名醫坐堂的藥鋪,多數和醫生是合作關系,“生意搭伙做”。先坐或單收診費,或提成藥費,或自付租金自主操作。少數是雇傭關系,先生百事不管只管看病,按月在藥鋪拿工資。凡是有些本事的醫生,是不愿意這樣取酬的。不管他們如何搭配,能配得方便了病家自然就受歡迎。
解放前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種類很多,銀元、紙幣、外幣、雜洋,互相兌換就有些復雜,老跑銀行嫌太費事,數額少了又怕人看不起。于是換錢的小柜臺便應運而生。許多金銀首飾店的老板本來就和銀錢業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有的甚至開著錢莊、當鋪,與自家的金號形成一個完整的小金融圈。他們的親戚中有人兼營一些貨幣兌換的小生意,把錢柜擺在他們門面的一角,也是一種相得益彰。
搭配得比較理想的要數飲食行業。
武漢人愛吃糊湯粉,關鍵在于那糊湯是用小魚熬出來的(最初是鱔魚,因為早年極少有人吃它,買它熬湯成本就低了),吃著它有一種“湯湯水水好養人”的感覺。還有一個原因是吃它從沒有單吃的,再窮的人起碼也要搭一根油條,掰斷了一節節放進湯里泡著吃。那油條鍋就架在館子的店堂里,大約要占店堂的四分之一。炸油條的師傅都是行業高手,油鍋里除了油條還有油餅(夾層餅,不同于常見的油餅)、油饃、炸花卷,間或還有麻花、馓子,進來的客人一般都只會點糊粉加油條,其它品種是門口單賣的。對吃粉的人,跑堂師傅還是照一般館子的習慣,“唱叫”一番:“穿制服的光生兩碗四件哪——”這里面的“碗”指的是粉,“件”就是指的油條。
在食客看來,粉配油條,他們是一家。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兩家。因為吃的人掰扯不開,他們的合作也比較牢固。
有的米酒甜食店,自家只賣清酒糊酒蛋酒,那些做豆皮、炕餃子的,全是“搭”進來的。東西是各進各賬,攤位只向“酒老板”交租子就行了。
商業的發展,使很多行業還在小做的時候就懂得了“打伙賺錢”的方式。只有更小更小的老板們,才永遠只敢當散兵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