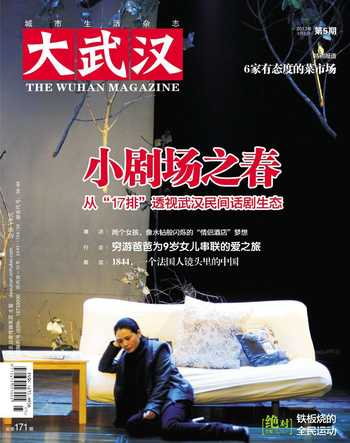雅集小趣
生活中,總會有一些聚會,因興趣愛好或聯絡情誼而集。有一陣子特別流行同學聚會,多是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同學在闊別多年后相約而聚,人生百態便可從這聚會中略見一斑。當時盛行同學聚會時,我們也常常找各種理由同學聚會,回家后時常還在興奮中,會不自覺的說我們女生怎么樣,男生怎么樣,家人忍受不了我的忘形,冷不丁會說上一句:你為什么不說,你們男孩子怎么樣?女孩子怎么樣呢?就這一句話,讓我倍受打擊。知道自己已不再是芳齡二八,痛定思痛后,再也不說男生和女生的事了。有一次特別的同學聚會,是和幼兒園及小學的同學相聚,我的一個男同學,和我幼兒園時就同班,我小時候的糗事,我已然沒了印象,他卻記憶猶新。那次聚會,我不知道怎么惹著了他,使得他手足并用的糗我。他說我假正經,說我小時候就很假正經,并學著我雙手擺正端坐時的假正經樣兒。說那時候如果想和我說句話,我一定會是很假正經的推開他,并警告他,不要影響我聽講和學習。他是借著幾分酒勁咬牙切齒說出來的,我一臉尷尬的聽。他后來說,想起我當年的假正經樣,就非常非常的生氣,憋了這些許年后,終有一吐為快的今天。最后他無不經典的說了一句我終生難忘的話,他說:“假正經個什么?告訴你,你三歲穿開檔褲時,就和我睡一張床,你忘了嗎?幼兒園中班睡得是統鋪!”對于他如此的記憶、如此的報復,我除了笑還是笑且只能笑,許多童年的趣事也自然浮現眼前。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在人生有了一些經歷后,倒如親人般,形成了另一種親情。這樣的聚會隨意、輕松、快樂。
后來的幾年,同學聚會少了,原因之一便是越來越重的世俗氣。同學聚會時的攀比炫富,多少讓人不舒服,而沒有人會吃飽了閑著去找不舒服。于是同學聚會就在不自覺間,冷淡了下來。大家又開始尋找一種聚會,各種雅集開始流行起來。
雅體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著某種愛好而聚集。剛開始聽到這個詞,很沒有文化的認為是新生的事物,后來怕別人笑話,還是偷偷的翻閱了一下資料,發現“雅集”一詞,最早源于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西園雅集”。據說在北宋年間,當時的文豪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等人常常集會于西園,寫詩作文,品茶尋韻。后來的文人雅士,由此而把這樣的聚會稱之為“雅集”。這樣了解后,我還真是感覺自己沒文化的可怕,所以,一聽說哪里有雅集,我便會跑去集,顯示自己的雅。與一群朋友,或聞香或品茶,或咬文嚼字對個聯子。總之,和這樣的一群朋友在一起,有特別陽春白雪的感覺,說話都怕大聲,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還學會了一些非常之雅的動作,如,展蘭花指泡壺好茶,像模像樣拿起壺蓋兒聞茶香。有時候,我在想,如此這般的動作,若被幼兒園的同學再次看見,不知道會怎么樣的鄙視我。這樣樂此不疲數次后,一日,友人發來一篇文章,題目為《雅集放屁》,我哭笑不得的讀完,卻是讀出幾分趣味與道理。再后來雅集,想著他所寫的放屁,就全然沒有了興致。
當然,不管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是生活的一種狀態。有時候,附庸風雅不見得是壞事,風雅的舉止本就是一個人的品格與才情的顯示。所以各種風雅,皆會被才情高潔者,自命不凡者趨之若鶩,我等凡夫俗子在趨之捧之時,總還是脫了些俗。風雅的舉止哪怕是裝出來的,總歸還是養了他人的眼,如若能做到人我兩忘,也不失為是一種境界。或許境界的高低不關乎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凡善的美的,總還是愉己悅人,只要是自己歡喜的,怎么樣都自在。
近日與琴友雅集,發現因著一張七弦琴,大家不管認識或不認識,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初識的一位琴友,不僅愛琴,且愛吟詩,席間詩興大發,七步成詩一首:岑樓聞妙音,泉涌絲竹琴,書不了此景,院深何處吟。這時的我非常想讓她知道,我如伯牙懂子期般懂得她的詩情畫意,于是八步成詩回應:妙音用眼聽,心靜八風停,美景伴七弦,吟唱有琴心。這一唱一和間,陌生人立即成了久違的老友,整場雅集絕對的左右相伴。這樣的雅集,大家其樂融融,旁人卻如喝了陳年的老醋,只有我們陶醉其間,感覺著舒暢與甜蜜。分別時都會惺惺相惜、依依不舍之態,約下次相聚的時間,只是,下次的雅集或者又有一個主題。
雅集其實也是個道場,每點小趣味如《妙法蓮花經》里的小譬喻,品味間總能感到幾分詼諧的驚覺。或許在某種特定的境況下,聽得懂你的琴不見得是知音。在我看來,真正的知音,是你不發一聲之時,能聽懂你心里的弦外之音。所謂大音希聲,不音之音,能聽懂者,一生一人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