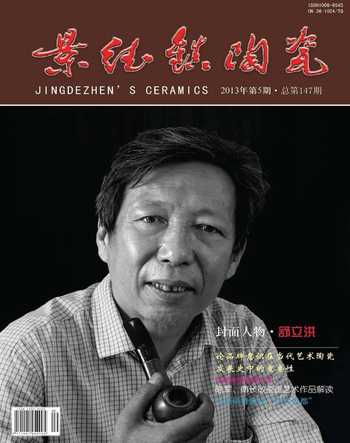試論徐熙畫風在北宋前期不被廣為認可的原因
楊冰 郭莉元
我們常常因為無法見到畫家的真跡而只能通過文字的記載來了解他們的風格。在宋代,對花鳥畫家的描述,一般總是稱其所畫花卉禽鳥如何栩栩如生。像黃荃所作仙鶴以假亂真,引得真鶴來之事的記載,可見花鳥畫的逼真效果是當時審美的主要趨向。公元965年西蜀被北宋滅,黃荃一直領導著西蜀皇家畫院歷經兩朝,于當年逝去,但他的兒子黃居寀入宋,后來得到太祖太宗的賞識,太宗讓其尋訪名畫,詮定品目。據書載,黃荃父子畫法自宋太祖和宋太宗以來,“為畫院一時之準,較藝者視黃氏體制為優劣去取。自崔白、吳元瑜既出,其格隨大變。”由此可見,自崔白等名家出現之前,北宋畫院中花鳥畫領域,基本上是黃氏風格一統天下。
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中說,“若論佛道人物,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樹石、花鳥禽魚,則古不及近。”這一論斷中包含了對五代和北宋中期以前中國花鳥畫發展成就的認識,而且還是一度不被彰顯的徐熙畫風的認可。雖然徐熙的畫風在宋代不受觀者采鑒,可是作為一種花鳥畫的獨特面貌并不會因此而消失。
盡管徐熙畫風曾備受宋太宗推崇,承有祖上之風的徐崇嗣在入宋之后,一時竟因黃荃認為徐熙畫風“粗惡不入格”,乃效諸黃之格,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直到與黃氏不相上下,才得以被認為是院品。黃荃之所以稱徐氏畫風“粗惡不入格”,問題的關鍵應該在用“墨筆”上,黃氏用線極為細淡,賦色與線融合,墨線并不明顯,后來竟不用墨線,直以色彩賦于其上,這種畫法更易于傳達富麗氣息,適于裝飾黃氏貴族的宮殿廳堂。黃氏父子因此得以成為宮廷中繪壁畫與屏風畫的專家。西蜀君王貴族尚奢華,宮殿、苑囿、池亭,世之罕見,黃氏父子入其皇家畫院供奉四十年,所圖繪的殿堂、墻壁、門幃屏風,不可記數。黃居寀以其四十年來供奉宮廷從事壁畫和屏風畫的經驗,入宋后,它所代表的皇家畫風又成為一時之標準,這對宋代畫院的裝飾性繪畫風格的形成產生莫大影響。
因為黃荃是一位御用畫家,所以表現題材、藝術手法都反映了宮廷貴族的欣賞要求。入宋后,黃荃在皇家畫院占優勢。黃荃因徐熙與自己的畫風迥然不同,出于偏見,將徐熙的畫說成“粗惡不入格”。黃荃之子黃居寀主持皇家畫院時,又專以黃氏體制為程式,獨步一時。直至徐崇嗣、趙昌、吳元瑜出,徐熙畫派才名震四方。在黃荃一派花鳥畫風靡之際,仍然能夠不隨流俗,獨具一幟,堅持自己的藝術道路和繪畫風貌,獨創“落墨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唐以來細筆填色表現奇花異鳥的格式,而有所創造,開創了一種水墨較多,兼用色彩的新面貌。
《圖畫見聞志》中論到南唐著名畫家徐熙的繪畫藝術時,曰:“江南徐熙輩,有于雙縑幅素上畫,叢艷疊石,旁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徐熙身為江南處士,自任高雅,終身不仕,因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之趣,故有“野逸”畫風之稱謂。北宋初年,宋太宗曾嘆曰:“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觀也。”并以徐熙的畫遍視群臣,以此為標準,然仍不被時人采鑒、稱頌。
黃氏父子畫風何以在宋代具有那么大的影響力,這要通過其繪畫的特點來認識。《夢溪筆談》描述說,“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這種畫法的顯著特色是逼真,黃荃曾在宮中一墻壁上畫了六只姿態各異的仙鶴,栩栩如生,竟引得真白鶴來。還曾經在墻上畫過一只野雞,被宮中白鷹連啄其壁,誤以為生禽。《姑溪居士集》記載還有“黃荃作夾竹桃花屏風,東川西川節度使廳皆有之。荃今不在,以真花片補其缺處,幾不能辨。枝上地下,相契不差毫發,天下傳以為工。”實際上畫史所記黃居寀“工畫花鳥翎毛,默契天真,冥周物理,”也是指其能得對象的形神與質感。在黃氏寫實精工方面,無疑是花鳥畫史上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進步。相比之下,徐熙那種帶有早期花鳥畫風貌的“不取生意自然之態”自然不被觀者采鑒,然而從社會的審美觀念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尚真的轉變。
除此之外,不應當忽視的是,黃荃父子花鳥畫的主要表現范圍與專尚富貴的社會習俗的投合。當時人們欣賞花鳥畫的審美心理定勢也可以從《宣和畫譜》中的記載所了解。曰:“詩之六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花之牡丹芍藥,禽之于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黃荃作為西蜀宮廷畫師,盡繪富貴之象,所作多是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用墨線,奇禽異獸,動靜都是栩栩如生,因而在宋代深受歡迎,以至于連徐崇嗣都改用黃氏之風格,顯然與黃氏畫中的“富貴”氣息有關。這一點正是畫史中記載徐崇嗣畫跡時,發現其前后所畫率皆牡丹、芍藥、桃花、海棠之類“富貴圖繪”的原因。查《宣和畫譜》可以了解,宋代花鳥畫寓意富貴的作品在各類題材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其中絕大多數應是裝堂鋪壁。在當時黃荃畫酷似物象的畫法,成了宮廷畫家表達富貴寓意所不可或缺的一項技術標準。所以才出現了雖然宋太宗曾以徐熙畫遍視群臣,俾為標準,然而在當時崇尚富貴的風氣之下,徐熙的墨筆草草、多狀江湖所有的“野逸”畫風,也因此不受時人采鑒,至于其作品的神氣俱現,妙參造化,號為天下之冠,直賴少數知者發現與欣賞。
在《題趙昌山茶》詩中說:“何須夸落墨,獨賞江南工。”梅圣俞詩中也說,“徐熙下筆能逼真,年深粉剝見墨蹤,描寫功夫始驚俗。”這些都是徐熙重筆勾勒的明證。因為花鳥畫自唐邊鸞至五代,沒有不精于設色的,重墨寫意是獨創的畫格,因它前無所師,所以容易受到排擠。徐熙的孫子徐崇嗣要想在畫院立住腳,就不得不放棄他祖父的畫風而學黃氏。畫史上確實說他“綽有祖風”,這或泛指他不墮家風,或說他早期的畫有學徐熙之筆,但從大量記載來看,他的畫風實在是學黃派而發展的。也正因他的畫“工與諸黃不相上下”,黃荃的兒子黃居寀才將他的《沒骨圖》定為上品。
徐熙與黃荃的作品,是中國10世紀花鳥畫發展成熟的標志,他們代表了在技法上重墨和重色的兩種創作傾向。此后的數百年中,徐黃二體的路線一直綿延不斷。重顏色的黃體花鳥,能深入對象特征,強調客觀真實和裝飾趣味的成分較多。后世的院體及工筆重彩花鳥,雖然發生變化,但始終沒有偏離這一傳統的基本精神。重墨輕色的徐派花鳥畫,能夠在表現風格上有更多的自由,技法上較為單純隨意,再加上其野逸的味道,很為后世文人所看重,成為后世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基礎。米芾認為“黃荃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可以說明這兩種畫風的特質及士大夫對他們所持的基本態度。
幸運的是,美術歷史并不是從犧牲一種風格的價值來保全另一種價值。到北宋中期以后,因文人畫的興起,不僅徐熙的野趣受到重視、推崇,而且整個畫壇日益開放,出現多元并存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