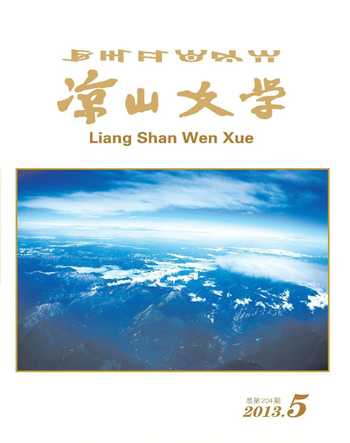隔壁有禪
陳阿依
瀘山位于西昌城南5公里,海拔2317米,有“半壁撐霄漢,寧城列畫屏”的氣勢,被譽為“川南勝境”。山上古樹參天,松樹尢其茂盛,濃蔭叢中掩映著漢、唐、明、清年歷朝修建的十余座古禪剎,還有別具一格的大型民族建筑群,依據(jù)彝族民居的建筑特點修建的全國獨一無二的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
涼山彝族奴隸博物館興建于1982年。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的館名,一直都讓人很糾結(jié)。彝族不乏開天辟地的敘事長詩,浩繁燦爛的神話故事,富有哲理的爾比爾吉和訓世箴言,形式豐富的音樂、舞蹈,匯集刺、繡、盤、嵌一體的服裝制作,還有稱得上是建筑刻畫符號的板居,更有源自漢代的十月立法、天文星象知識,生動有趣的生活習俗和日常行為,以及讓人目眩神迷的宗教內(nèi)容和表現(xiàn)形式。雖說民主改革前,其社會形態(tài)還處于奴隸制階段,社會成員的身份與身俱來,但人身隸屬關系和租佃關系也即剝削關系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各個家支成員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權益都由家族負責,沒有劊子手的角色,處罰死刑的人員都以服毒,上吊來自行了斷,生命絕非可以隨意殺戮。奴隸到了適婚年紀,主子不但要負責奴隸的結(jié)婚生子,還要給成婚的奴隸劃分耕食地,奴隸不滿意主子,也可以要求被賣,遠沒臆斷的那么血腥。故而,硬生生地套個階級來詮釋其社會構(gòu)架,不貼切也容易讓人誤讀。而且使用“奴隸社會”作為館名,很多時候便把鐫寫在羊皮和木櫝上,可以和半坡劃等號的幾千年文字,乃至它涵蓋的諸多厚重,輕薄地抹殺給了那些個,為了獵奇人皮鼓、頭蓋骨天燈而來,穿著拖鞋、沙灘褲,亂吐唾沫、口無遮攔,目光空洞,經(jīng)常在我解說時候,肆意揮灑傲慢和淺薄的嘻哈族。
奴隸社會的館名,加上曾經(jīng)售價不菲的門票價格,著實不知曾經(jīng)讓多少有求知欲望的觀眾望而卻步。能堂而皇之走進來參觀的,無外乎都是些吃飽了會議伙食、喝足了免費酒后,在展廳里指手劃腳走過場和冒充學問的。在現(xiàn)今這樣一個擁擠著功利和浮躁,有奶便是娘,有錢就是爺?shù)慕疱X社會里;在這樣一個舉國上下全民娛樂、惡搞至上,夸張、無厘頭可以讓全國上下瘋唱《忐忑》,世界各地狂跳《江南style》的簡愛時代中;在社會成員的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變化,x富,x二代比比皆是的前提下;在傳統(tǒng)的美德被拋到九霄云外,誠信拿來忽悠,真善美不敵假丑惡、會干的不如會舔的、尤物寄生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漂白成高干,只要心隨我動一切皆有可能的大環(huán)境里;在芙蓉姐姐、犀利哥、周立波、小沈陽之流的人物于一夜之間大紅大紫的時候,再把舊有制度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放在這般景色旖旎的地方講給那些:或者大腹便便、腦滿腸肥的飛黃騰達者,或者胸無點墨,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小癟三,或者尚需解決溫飽的農(nóng)民工人來聽,實在是落后于社會需要,博物館門前冷落車馬稀也就成為必然。
而與博物館同生共存于山巒秀美,樹茂林密,云霧繚繞的瀘山之上,掩映在秀山麗林之中,羞羞答答的不肯顯現(xiàn)真容的集儒教、道教、佛教一山共融的古禪剎卻門庭若市,一派繁榮。亭臺樓閣,高低錯落在山體上的梵宇、佛宮,體現(xiàn)了唐代武后“三教合一”的宗教懿旨。鄰居的香火裊裊,禪聲陣陣,鐘聲悠悠,并不悠遠卻清晰地敲打著我有些落寞的耳膜。禪剎的播放機里永遠流出的是讓人懨懨欲睡的大悲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疲不倦、無休無止。禪剎里的菩薩不但可以祈禱未來,還可以抽簽預知吉兇禍福,如有不測預示,自有“大師”可以撥亂反正使你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禪剎有茶室、書齋,既可以泡一壺香茗小憩品飲,亦可隨意閱讀、博弈,同在博物館里不得隨意喧嘩、只能看看圖片和實物、聽聽一成不變的講解相比,游客們似乎更樂意花上三五元的門票錢,進到廟里去拜拜那些泥塑的神仙、菩薩,吃吃和尚尼姑道士們吃的齋飯,坐著喝一喝茶水,或者吃一碗西昌人祖宗八代都沒吃傷心的“傷心牌”涼粉,既滿足了精神又呵護了身體。
伴隨時代的進步,搞活經(jīng)濟理念的深入,那原本只是祈求心靈安靜之地,卻派生了一些個神奇的功能出來。不但能夠負責人們的的今生來世、轉(zhuǎn)世輪回、生老病死,還負責人的富貴貧窮、仕途升遷、婚姻子嗣。沒錢的盡可來求錢,沒官的也可以來求官,真真是要風有風,要雨得雨。看著那些黃泥巴被人捏成了人形,供在廟堂里控制和主宰它的制作者時,真不知道是人的悲哀還是神的不幸?但不管你有錢沒錢,既然來求錢就都得給神貢獻公德錢,有官沒官的要進門來求官也得前倨后恭,一樣趴在地上給那堆泥土磕頭下跪。有了錢的期盼更加財源滾滾,有了官的希望繼續(xù)官運亨通,于是,許愿、還愿、再許愿、再還愿。禪房頂上的香煙滾滾升騰、生生不息。每到觀音誕辰、財神壽日、舊歷歲首,為了爭上頭一柱香,從頭一晚上開始,瀘山山道和博物館的停車坪上停滿的車輛,黑壓壓的一片,讓人想起了烏鴉啄食人肉的天葬。菩薩的恩德能應付得了這么龐大的群體?大肚男、脂粉女、一心向佛的虔誠信徒們,浩浩蕩蕩蕩地把整條通道淤塞得水泄不通,比回家給親娘老子拜年態(tài)度還虔誠、端正。這些頭顱里擁煩著世俗萬念的人們,因為車位爭吵打斗,每每需要警察出來呵護,便早就忘卻了佛寺清靜。那佛若有知,可會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經(jīng)濟搞活的好處就是,讓廟宇迎來了更多虔心禮佛的孝子賢孫,當然也包括了本就住在山下漁村里的阿貓阿狗們,不知道是頓悟了宗教的真諦,還是擔負不了人生所累,拋棄了妻兒老小都一股腦來到禪剎里誦經(jīng)打坐,個別因禮佛致富不但修得了身份的顯赫,還把那故園搖搖欲墜的舊居,修成了幾層樓房。雖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佛門亦絕非就是紅塵之外的清靜之地,廟里每一次替換主持時的明搶暗斗、勾心斗角之激烈程度,絕對的可以說是不見刀光劍影卻有殺人不滴血的慘象。我偶爾在山道遭遇那些個紅光滿面的禪僧之時,看著他們一個個都皮光毛亮、優(yōu)哉游哉,從他們那顧盼流轉(zhuǎn)的眸子里,看不到一絲一毫的自然平和就知道他們其實也一樣榮辱皆驚。
換了一屆又一屆領導,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會議,如今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依然還掛著開國元勛般的頭銜,和簡愛時代的很多國家博物館一樣,只能束手無策地依然拽著懷里的寶貝,靠著國家撥款這條臍帶茍延殘喘的維系著運轉(zhuǎn)著,吃不飽也餓不死。博物館里依然養(yǎng)著我等一大堆游手好閑,在瀘山的天然氧吧里曬太陽、諞閑話、打瞌睡的寄生蟲。館長本人還無可奈何地親自訕笑我像極了省博物館某川大研究生,整日間無所事事,只會做手工。我至今依然每天在社會主義和奴隸社會之間,穿越時光隧道忙碌著閑得不亦樂乎.
這個明顯已經(jīng)落伍了的館名,這個沒法彰顯古老文化,吸引觀客的彝族老房子,這個為了“文物”安全,不得不保守和僵硬于風景區(qū)的經(jīng)營,實在讓人糾結(jié)。博物館2006年再次改修,免去了門票,成了開放式的展區(qū),景色和建筑更上一層樓,為了滿足游客的審美情趣,還特意招聘了年輕的解說員,游客有事沒事都可以溜達進來,拍照,想看不想看地看看圖片文字,聽聽招聘的小姑娘吹噓如果有男人要娶她們,需要給付的身價錢。去年高速公路通車后,成都小市民們,每逢周末自駕來曬太陽,一大片一大片地像蝗蟲一樣,流竄在瀘山,濕地公園,邛海,博物館等風景區(qū),吃貴了西昌的蔬菜水果,塞漲了旅店賓館的房價,但是,博物館的興興向榮,人聲鼎沸,最終也只能集中表現(xiàn)在廁所的擁擠程度,已經(jīng)快要趕上了故宮。
很多時候,我可以容忍身邊周遭的淺薄和瘋狂,卻無力擺脫俗塵的糾纏與侵擾。我時常落寞地看著落日余暉中涼山之鷹那勢單力薄的身影,聽著隔壁禪剎內(nèi)的鐘磬齊鳴,無數(shù)次地幻想著,如果博物館弄個大篷車隊來表演些賞心悅目的艷舞,如果博物館販些這個包養(yǎng)那個寄生的圖片來展出,或者也學了那隔壁鄰居,顛覆一代彝族宗教祭司阿史拉者----一個肯定現(xiàn)世今生的幸福生活,從不宣揚懲戒之說,也不會描摹來世鴻蒙,絕不轉(zhuǎn)嫁自身災難和許諾的大宗,搞一個偽周剝皮和偽陳勝、吳廣的把戲來讓他老人家為香火包圍,是否可以讓彝族和博物館,再次實現(xiàn)一步跨千年的傳奇。
與神為鄰,隔壁有禪!不用青燈古卷、無需口誦佛經(jīng),也不會刻意參禪。今夜,沏一杯茶、點一支煙,捻筆鋪紙,我在心中默默為我的心中的族和館,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