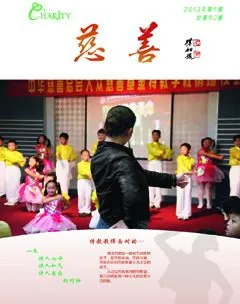玉樹情緣
韓春霞
“鈴……”,鬧鐘照例響起,我爬起床,關上鬧鈴,洗漱妥當,灌了一大杯涼白開,除去一大早惱人的燥熱感,左手隨手背起單肩包,右手拎上紅色小拉桿背包,就這樣出了門。
這一天又是一次出差而已,但心里又有那么點忐忑和興奮,因為這次是去海拔3800米的藏區——青海玉樹。會不會有什么高原反應呢?剛從國外回來時差還沒倒過來行不行啊?萬一反應很厲害完不成工作怎么辦?……因為是第一次的緣故,因此腦子里不停地閃過一個一個問題。想到瘦小的自己平時就被大家戲謔是個“林妹妹”,又剛到國外經歷了10天高強度封閉培訓,就情不自禁地自憐起來……可是對高原遼闊美景的憧憬,和感受藏地文化的期待,又忍不住無比激動和興奮,以至于差點把這次出差的工作都拋到腦后去了——對寶馬愛心基金今年的玉樹物資援助活動進行前期考察。
寶馬基金與玉樹的緣分源于2010年“4·14”玉樹大地震,而寶馬基金的成立也是始自5·12汶川特大地震。2008年6月28日,中華慈善總會寶馬愛心基金正式成立,寶馬(中國)和華晨寶馬共同捐贈1000萬元作為基金起始資金。基金主要開展社會關愛,即災難救助項目,除了緊急救災以外,在當時受災的四川、甘肅、陜西省開展了教育支持項目,如“點亮希望”貧困學生助學金資助項目、貧困教師資助項目以及教師培訓等。除了捐錢,寶馬還秉承了很強的參與理念,他們希望把愛心基金做成一個愛心平臺,能夠使寶馬公司員工、經銷商、車主以及其他社會愛心人士都成為志愿者,參與到基金的項目和活動中來。因此,愛心基金的項目做到哪里,這些志愿者的足跡就走到哪里。以四川平武縣為例,自從地震發生之后,這些愛心志愿者組成的車隊十余次深入平武,他們的足跡從縣城到中學再到孩子們的家,從剛剛地震完沒有道路,從成都需要開車步行幾天才能到平武,到后來道路重建完成,幾個小時就能抵達,一路上滿滿都是回憶……為了幫助孩子們心靈上的創傷早日平復,基金開展了“點亮希望”心靈陪伴項目,讓志愿者與孩子們自愿結成對子,鼓勵他們保持定期的溝通交流,使孩子們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愛。
2010年,是基金成立的第三個年頭。這一年,在青海省玉樹地區,又發生了一場始料未及的大地震,使本就偏遠的西部高原聚居區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正是那一年開始,結下了基金和玉樹三年多的情緣。三年多來,基金每年組織志愿者赴玉樹開展慰問活動,為當地藏民及藏族學生送去生活慰問品和學習用品。今年的慰問活動是在8月,這次上去正是前期溝通和學生家訪。
抵達西寧安頓好已是下午4點多了,適逢省里第二天要去玉樹考察重建項目,鄭秘書長開完會匆匆趕來,他也顧不上喝一口水,就加入到項目溝通會中,與捐贈方的代表一起就活動的安排一一確認。溝通充分而富有成效。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因為與漢民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文化信仰和習俗,因此在開展活動當中,也有著它的獨特性,也就需要我們前期做更多的準備工作和溝通工作,這一點,在我第二天在玉樹和藏族朋友親身接觸后,才有了切身的體會。本來打算好好睡一覺養足精神,因為時差作祟,幾乎又是一個不眠夜。
第二天一早我們坐上了飛往玉樹的飛機,沒想到竟是滿員,聽省里同行的同事說,現在從西寧到玉樹每天三班飛機,因為夏季是高原含氧量最高的時候,所以也是航空最繁忙的時候,幾乎班班都是爆滿。一下飛機,映入眼簾的是那分明的色彩,清透的藍天點綴著層次分明的云朵,四周被青山環繞著,近處則是遼闊的青青草原,淺淺的河水蜿蜒而過,有一種說不出的分明和純粹充斥在這個空間里,時間仿佛靜止了,只有當那星星點點正在建設中的重建民房映入眼簾的時候,才把我從那天堂般的景象帶回人間,恍如隔世一般,頓時明白了為什么那么多人對高原圣地充滿向往和魂牽夢縈。
光照很強,太陽光照在皮膚上有種被灼燒的感覺,輕輕地痛。回過神來的我,深吸了兩口空氣,感覺身體沒什么異樣,只是走起路來不知不覺地放慢了,有意或無意地,一步一步跟著來接我們的熱情的玉樹縣教育局的領導、學校校長走出機場。我們的行程只一天,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因此我們并沒有太多時間來調整身體狀況,馬上就要去兩戶學生家里進行家訪,然后去學校參觀。
第一戶的小女孩和奶奶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妹妹一起生活,他們還住在救災帳篷里,聽說天冷前他們就能夠搬進建好的新房子了,因為語言不通,男主人和我們的受助小姑娘都上山挖蟲草去了,我們只和媽媽奶奶進行了簡短的交流。
第二戶的小女孩叫桑吉,她家離第一戶住的帳篷不遠,是重建好的新房子了。從外面看,所有的重建民房都是一樣的,很整齊地朝向一個方向,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和內地的農村很像,只是我們到的這個鄉的重建民房都是在大草原上。我們下車,桑吉已經站在院門口等我們了,小姑娘瘦瘦的,扎了個馬尾辮,她很害羞,作為唯一的女團員,我徑直走過去拉住她的小手,跟她打招呼,她靦腆地笑笑,拉著我走進了院子。院子很大,四四方方,我們穿過院子,徑直走進了她家,桑吉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爺爺臥病在床,因為爸爸媽媽不在了,家里全靠奶奶一人維持生活。
爺爺奶奶都不會講普通話,桑吉的普通話說得不太好,在一旁的吉瑪校長時不時地要幫忙翻譯,在交談中,我得知她今年上三年級了,剛剛搬到新房子,奶奶每天給她梳辮子,她現在在放蟲草假,不用上課,可以和小朋友玩兒,也會跟著其他孩子一起上山挖蟲草,賺點錢貼補家用。當問到她喜不喜歡新房子,她很天真地回答:不喜歡,還是喜歡住帳篷。聽到這樣的回答,還真有些意外。在帳篷住了兩年多,肯定是有感情,要適應新環境看來還需要一些時間吧。
和桑吉告別后,我們又來到的巴塘鄉中心寄校是新落成的,比起民房,這里的學校是最先被重建好的一批工程項目,教育永遠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即使沒有像樣的房子住,也要先給娃娃們建好學校。
一路看下來,我的高原反應也冒了出來,胸口好像被人不停地擊打著,還伴著頭痛,不過比起腹瀉和發燒,我的癥狀還算不嚴重的,但是又是一夜未眠。同行的同事卻說能夠住到建好的酒店睡舒適的床,已經很幸福了。去年上來時,還在住板房,結古鎮也還是一片工地,今年都已經建好大半了。
第二天就要離開了,坐在汽車上,回想著這一天短暫行程中的一幕幕,讓我感受到這里與大城市的天壤之別——這還是個淳樸和純粹的地方,不摻雜對物欲的渴望與艷羨,依舊保持著對信仰的執著追求,過著物質貧乏但精神富足的生活;或者他們根本就不覺得自己的物質貧乏,因為他們有青山、藍天、綠水、白云,有肉吃、有房住、孩子們有學上,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信仰,所以,拋開世俗的評判標準,他們是比我們要富足的,他們還擁有更寶貴的自然之美和內心的純凈。
現在看來,究竟是我們在援助他們,還是他們在救贖我們呢?但是我清楚一點,我一定會再次登上這片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