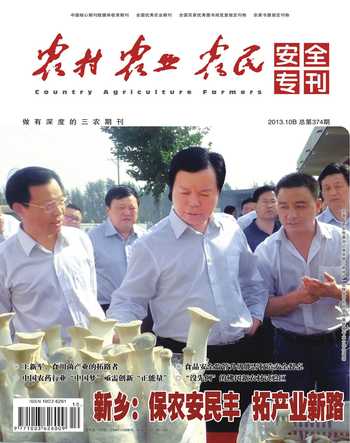種子企業發展商業化育種難在哪里
佟屏亞
2012年12月,國務院發布《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重點指出“引導和積極推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業化育種,促進種子企業逐步成為商業化育種的主體”。這是《規劃》的綱,綱舉才能目張。堅定地推進和實現這兩項關鍵任務,發展現代種業才有可能步入坦途。
商業化育種退出科研院所逐步進入企業,如同其他社會領域的改革一樣,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改革頂層設計”,觸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復雜,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商業化育種退出科研院所是一個難啃的“硬骨頭”。
企業發展商業化育種難在哪里?
第一,根深蒂固的“層級制度”。我國農業科研院所和院校長期實行的一整套體制,完全是從“蘇聯老大哥”那里照搬過來的。蘇聯已經沉沒20多年,俄羅斯可能也不搞這一套了,而中國經歷30多年的改革,農業科研院所依然沿襲行政體制的組建模式,依附于行政機構,賦予相對應的行政級別,“層級制度”與時俱進,愈演愈烈。農業科研人員和教師的技術職稱都要參照“行政級別”,享受同級政府公務員的級別,相應的獎勵、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某些有作為有能力的,還有掛冠院士,榮任所長、院長或政府高官的機遇。趨利爭名是人的本性,在這種誘惑下,還有多少科研人員愿意兢兢業業埋頭苦干呢?改革開放初期,科研體制內大批科研精英紛紛下海創業,而今,社會精英急切地向體制內回歸或靠攏,因為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沒有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迫使企業快出成果求生存的壓力。
第二,重大科研項目向“官學兩棲”人員傾斜。農業科研實行項目管理制,基本上由科研院所行政一把手(院長、校長、所長等)掌控,按官位分配科研資源和獎勵已經是不成文的規定。官員利用權力維護既得利益,壟斷人力、物力和財力為自己的“項目”服務,占科研人員不足10%的“官隊”掌控著90%的科研經費。行政權力與學術地位合而為一,讓體制內的科技官員身價陡增。現在的“官隊”掛銜首席科學家、首席研究員、學術帶頭人稱號,身兼立項決策人、項目主持人、課題發包人、成果鑒定人,還是評學銜、評職稱、評級別、評學術帶頭人等的委員,有位、有權、有錢還有名。查一查新近國家科技大獎的獲獎人,名次列前的多數是行政一把手。這無疑影響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特別是中青年創新能力的發展。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最大的難題就是去行政化管理,通俗地說就是去除“官本位”。
第三,農業科研資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農業科學屬于應用技術科學,它綜合運用基礎學科知識,以與農業生產有關的生物為對象,服務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以農作物育種研究為例,它是由若干技術環節組成的系統產業鏈條,包括規范種質資源、改良育種材料等,其中培育新品種是最接近市場的下游環節。現階段農作物育種工作有三個特點:90%以上的種質資源和育種人員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90%以上的科研經費投入到育種研究;90%以上的農作物品種是由科研教學單位選育的。新品種或轉讓進入市場,或自辦種子經銷處、開發部、服務點,大部分轉讓或經營收入進入院所“小金庫”成為職工福利、獎金,公共資源通過合法渠道“私有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科研院所管理體制被利益集團所操控,不但脫離社會發展和生產需求,并逐漸演變為與之對立的雙重利益集團。這種“雙軌科研體制”被認為是限制農業產業快速發展、抑制科技創新的主要障礙。
第四,農業科學研究財政投入多渠道。農業科研和高等院校長期在政府“管理主導型”模式下,存在部門分割、管理多頭、職能重復、雙重定位等問題。農業科研經費投入涉及很多部委以及地方部門,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農業部、教育部等。例如科技部、農業部主管部門實施的“項目”管理模式:你建一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我設一個國家作物改良中心;你設一個糧食豐產科技工程,我建一個作物產業技術體系;你支持一個“超級玉米”培育項目,我申報一個“超級水稻”認定推廣。戴頂“帽子”,掛塊牌子,各牽一條線,各管一大片。這種疊床架屋、錦上添花的重復設置,實質上是政府部門向基層延伸權力和利益的體現,“線官”拽一拽,“首席”團團轉。項目與經費掛鉤,權力與利益鏈接,這就出現了“跑部”、報表、總結、開會、游覽,各盡其職,各獲其利。科研人員整天疲于琢磨官員的心思,花費大量精力、金錢、時間跑項目、爭經費,疲于應付各類專題規劃、項目論證、評估招標、檢查驗收等活動,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時間不到三分之一。
第五,農業科研成果私有化取向。農業科研院所長期實行以項目或課題為研究單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題目個體化、研究材料私有化、成果交易地下化趨向。一是科研題目個體化。中國有龐大的科研隊伍,但鮮有形成規模化研究的科研共同體,基本有多少“農學家”就有多少研究組,可以稱為“大科研、小作坊”模式,大多是1人,多者2~3人,或許是夫妻子女店,很多時候基本上都是單兵或散兵作戰。課題主持人利用“流動”的在讀研究生或臨時工完成育種程序。禁錮在畫地為牢、自我束縛的環境里,造成院所之間、科研人員之間相互封閉、重復研究,期盼“突破性”小概率發生。二是研究材料私有化。科研人員擁有的研究材料,被視為私有財產和商業機密,彼此間很難做到資源共享或友好交流。科研材料的私有化和局限性,造成資源浪費,重復低效。三是成果交易地下化。以品種選育為例,農業管理體制造就育、繁、推脫節,企業經銷種子需要從科研單位購買。今天,一個國審品種售價從幾百萬元到上千萬元,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將親本材料或新育組合與企業私下交易,通常都會有幾十萬至上百萬元的收入。業界人士指出:科研人員希望采取短、平、快方式出成果,把它作為牟取額外創收的措施之一。這已經是不足為奇的事,很多時候科研成果或新培育品種就這樣私下流向了企業。
特別指出,農業科研院所體制改革遇到的問題,要從歷史沿革和政治高度來審視。有些問題既是根本性的,又是歷史沉積而成的,體制改革有積極的動力,也有強勁的阻力,肯定會遇到很多困難,陣痛或劇痛是必然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已成過去,理性改革與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是一個躲不開又必須邁過的“坎”,改革有困難,停止有危險,但絕不能推論說“改革自己”是不可能的,放棄改革將永遠落在世界后面,現代化種業也不可能發展、壯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