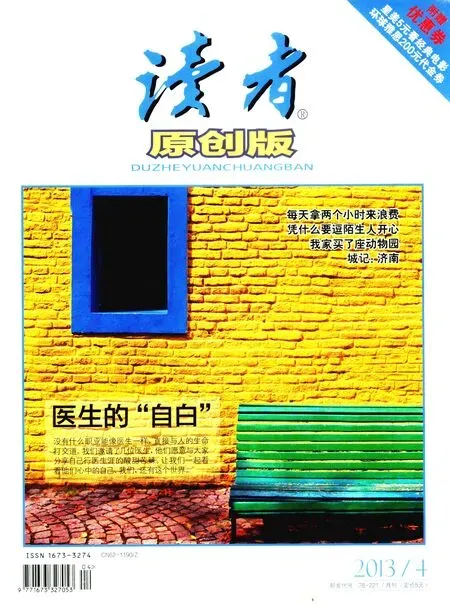皮爾森的夜
文 _ 韓晗
皮爾森的夜
文 _ 韓晗

皮爾森的深夜

入夜前的皮爾森
我們抵達(dá)捷克工業(yè)重鎮(zhèn)皮爾森時(shí)已是下午6點(diǎn)。這座城市與德國(guó)接壤,是斯柯達(dá)汽車的生產(chǎn)地。為了方便,我們?cè)谑袇^(qū)一家名叫Clarion的酒店住宿。
與妻安頓好之后,決定徒步出去看看這里的風(fēng)景。酒店的斜對(duì)面有家樂(lè)購(gòu)(Tesco)超市—這是捷克最多的超市。據(jù)說(shuō)這家超市在捷克生意極好,以至于連世界連鎖業(yè)巨無(wú)霸家樂(lè)福超市都無(wú)法進(jìn)駐捷克,只好與樂(lè)購(gòu)?fù)讌f(xié),采取部分入股的形式,分得一杯羹。
當(dāng)我們走到樂(lè)購(gòu)超市門前時(shí),忽然發(fā)現(xiàn)超市已經(jīng)停止?fàn)I業(yè)了,仔細(xì)一看,晚上7點(diǎn)是下班時(shí)間,里面有幾個(gè)服務(wù)員在拖地。
我們決定向城區(qū)走走看。樂(lè)購(gòu)超市的門前,有一座古老的石板橋,橋下是區(qū)分皮爾森新城和舊城的拉布扎(Radbuza)河。橋邊的石柱都已經(jīng)發(fā)黑,估計(jì)有八九十年的歷史。石板橋的人行道與車道都是碎石塊拼成的老路,與周圍的馬路、人行道天然地連成了一片。當(dāng)我們從石板橋上走過(guò)時(shí),忽然發(fā)現(xiàn)周圍零散的路人加起來(lái)不過(guò)三五個(gè)人。
按照常識(shí)判斷,這是高峰期剛過(guò)的傍晚,應(yīng)該有不少回家的人才對(duì),但越往前走,行人越少。走到一家快餐店門口時(shí),我們發(fā)現(xiàn),偌大的皮爾森街道上只剩下我們倆了。我們所看到的店鋪,沒(méi)有一家開門的。
夜晚的皮爾森雖然安靜,但所有的店鋪都打烊,這也給我們?cè)斐闪瞬槐悖┤缈诳柿耍胭I瓶水都買不到。
妻只好用手機(jī)導(dǎo)航,尋到了一條近路,準(zhǔn)備回酒店。整條路上,除了路燈之外,似乎就只有樓房屋舍里的燈光。
我們強(qiáng)忍著口渴,繼續(xù)往前走。功夫不負(fù)有心人,在遠(yuǎn)處的路邊,我們看到了一間亮著白燈的小屋。常識(shí)告訴我,那是一家社區(qū)超市。
我與妻加快了腳步,走過(guò)去之后,忽然驚訝地發(fā)現(xiàn),超市的老板與服務(wù)員是華人!
“你好!”我大聲用中文跟兩位同胞打招呼。他們面面相覷地看著我。
“你們是中國(guó)人嗎?”
“您需要什么?”女老板勉強(qiáng)擠出生硬的英語(yǔ),而她正在里屋搬運(yùn)貨物的兒子也探出頭來(lái),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他們完全聽不懂中文。
“您是中國(guó)人嗎?”我繼續(xù)用英語(yǔ)問(wèn)。“是的。”女老板這次聽懂了,“但我們并不來(lái)自中國(guó)。”
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遇到同胞,相互之間卻不能說(shuō)中文,這聽起來(lái)有點(diǎn)可笑。記得我們念中學(xué)的時(shí)候,為了訓(xùn)練大家的英語(yǔ)口語(yǔ)能力,老師突發(fā)奇想,讓同學(xué)之間用英語(yǔ)交談,結(jié)果教室里笑聲一片,一個(gè)平時(shí)敢發(fā)言的同學(xué)很大聲地提出不同意見(jiàn):“大家都是中國(guó)人,干嗎聚在一起講英語(yǔ)?”教室里爆發(fā)出哄笑,老師無(wú)奈,只好作罷。
但是我在皮爾森卻對(duì)自己的同胞說(shuō)英語(yǔ),因?yàn)樗麄兇_實(shí)聽不懂中文。這種感覺(jué)是尷尬的,好似你回到了自己的故鄉(xiāng),卻不能說(shuō)方言,而要講普通話。我買了一瓶礦泉水,妻子買了一盒酸奶,結(jié)賬時(shí)他們也不問(wèn)我們是否來(lái)自中國(guó),冷淡的態(tài)度讓我們覺(jué)得很失落。
從這家店出來(lái),外面夜幕更沉,遠(yuǎn)處的屋頂仿佛和蒼穹連接成了一片。
在黑夜里,哪怕是最微弱的光,也會(huì)被迅速、準(zhǔn)確地捕捉到。我發(fā)現(xiàn),不遠(yuǎn)處還有一家店鋪。手頭的礦泉水已經(jīng)被我一飲而盡,需要再買一瓶,我決定到下一家店鋪去看看。
這家店鋪和上一家一樣簡(jiǎn)陋,貨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許多非易耗的日用品都來(lái)自中國(guó),如指甲刀、塑料簍之類。店主又是兩個(gè)華人,像是兄弟倆,同樣聽不懂中文,同樣面對(duì)我們沒(méi)有表現(xiàn)出“他鄉(xiāng)遇故知”的欣喜。我回頭時(shí)發(fā)現(xiàn),門上貼著的李小龍的舊海報(bào)早已斑駁不堪。
在皮爾森,這樣的商店有近十家,最大的一家大約有一百多平方米,老板雇用的店員也是華人,但他們都用最為熟練的捷克語(yǔ)交流。
在回酒店的路上,妻說(shuō):“還是我們?nèi)A人最勤勞,大家都睡覺(jué)了,拼命做事的還是華人。”
我沒(méi)有接話,因?yàn)槲也淮_定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是華人。
去年年底,我在臺(tái)灣成功大學(xué)參加該校80周年校慶活動(dòng),席間遇到一位漂亮的女生。她告訴我,她來(lái)自臺(tái)灣實(shí)踐大學(xué),但她是湖北武漢人,算是我的老鄉(xiāng)。
當(dāng)時(shí)大陸生在臺(tái)灣的并不多,我很驚訝,問(wèn)她是哪一年到的臺(tái)灣。“我就是在嘉義出生的。”她回答。我更為驚訝,嘉義女孩何以成為我的老鄉(xiāng)?
我再一打聽,原來(lái)她的爺爺曾是武漢會(huì)戰(zhàn)時(shí)的國(guó)軍,后來(lái)因?yàn)閮?nèi)戰(zhàn),從大陸到了臺(tái)灣。她的父親從小在眷村長(zhǎng)大,后來(lái)出去經(jīng)商,時(shí)常往返于陸臺(tái)兩地,總給她帶一些武漢的特產(chǎn)與風(fēng)光片,久而久之,她對(duì)于武漢非常熟悉,以至于會(huì)模仿電視里的人說(shuō)幾句不地道的武漢話,但她一直未曾去過(guò)武漢。
在臺(tái)灣,我經(jīng)常遇到與我攀老鄉(xiāng)的人。從桃園巴士站到士林捷運(yùn)站,從臺(tái)北故宮到臺(tái)南國(guó)家文學(xué)館,我遇到過(guò)很多沒(méi)有去過(guò)湖北的湖北人。當(dāng)然,這種情況在大陸也時(shí)有發(fā)生。曾經(jīng)有一次在南京大學(xué)開會(huì)時(shí),我遇到了臺(tái)灣中央大學(xué)的涂藍(lán)云博士,她是湖北鄂州人,可惜她從未去過(guò)鄂州。當(dāng)她知曉我的新居就在鄂州時(shí),很興奮地告訴我:“下次我來(lái)鄂州一定要聯(lián)系你,我好想去鄂州看看,我從小就知道我是鄂州人。”
民族的認(rèn)同源于文化的認(rèn)同,這文化包括語(yǔ)言、環(huán)境、文字與性格。雖然我在皮爾森也遇到了沒(méi)有去過(guò)中國(guó)的華人,但他們對(duì)于中國(guó)卻是這樣的陌生。皮爾森不是臺(tái)北,當(dāng)China這個(gè)單詞從這些捷克華裔們的嘴里生硬地蹦出時(shí),與apple、water這些單詞沒(méi)有什么兩樣。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是因?yàn)閷?duì)顧客客氣才說(shuō)他們是華人?如果他們一輩子遇不到一個(gè)中國(guó)顧客,他們是否會(huì)忘記自己的身份,而天然地認(rèn)為他們是捷克人?
這種感覺(jué)非常奇怪,也一度讓我匪夷所思。以前我在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時(shí),曾看到過(guò)一個(gè)記載。“一戰(zhàn)”爆發(fā)時(shí),中國(guó)政府曾經(jīng)派遣勞工隊(duì)赴歐參戰(zhàn),這時(shí)就有一批中國(guó)人留在了東歐,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國(guó)家。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后,這些中國(guó)人因?yàn)闆](méi)有學(xué)歷,語(yǔ)言又不通,只好在當(dāng)?shù)刈龇浅?嗟墓ぷ鳎┤邕\(yùn)尸、掏下水道等等。第一代人立足之后,中國(guó)又相繼爆發(fā)抗戰(zhàn)、內(nèi)戰(zhàn),而德國(guó)治下的捷克卻相對(duì)太平許多,第二代人自然也不想回國(guó),就開始經(jīng)營(yíng)中餐館、做保姆等等,做比父輩稍微輕松一點(diǎn)的工作。到了第三代人時(shí),捷克已經(jīng)成為紅色波西米亞的世界,對(duì)于大多數(shù)華裔人士而言,他們?cè)缫讶豚l(xiāng)隨俗,有的搞外貿(mào),有的從事超市經(jīng)營(yíng),部分人還進(jìn)入政界與學(xué)界,當(dāng)選為議員或受聘大學(xué)教職,已完全融入了當(dāng)?shù)厣鐣?huì)。
他們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交往、婚姻,東歐的華裔多半還是選擇和華裔結(jié)婚,所以后代還是華裔,只是他們?cè)缫巡皇侵袊?guó)人,自然也聽不懂中國(guó)話。除了中餐館老板外,絕大部分東歐華裔的日常生活也早已西化,有的全家信仰天主教,每周趕到教堂去做禮拜,有的日常三餐均為西餐,早已不習(xí)南北菜系之味。甚至在個(gè)人習(xí)慣上,也被逐漸打上了西方人的烙印—他們不愿意拍照,不喜歡討價(jià)還價(jià)。但是,在骨子里他們依然保留了中國(guó)人最本質(zhì)的特征—勤勞。

黃昏,皮爾森街景
有朋友在國(guó)外的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室留學(xué),回國(guó)之后大為感嘆:西方人工作八小時(shí)之后就下班去喝咖啡了,為了幾十美元加班費(fèi),熬夜加班的永遠(yuǎn)是中國(guó)人!
我相信,入夜之后的皮爾森,一定不會(huì)是無(wú)人之城。有的家庭早已開始了他們的家庭聚會(huì),有的一家老小開著車到劇院去聽歌劇,還有的人或許已經(jīng)鉆到地下室酒吧里去暢飲一杯,當(dāng)然也不乏駕車到周邊去旅游度假者。放棄休假,為了賺一點(diǎn)口糧而堅(jiān)持在晚上營(yíng)業(yè)的人,始終是華人。
“這一晚上,你說(shuō)他們能多掙多少錢?”妻問(wèn)。我不知道,所以我無(wú)法回答。整條街道上只有我與妻兩人,我們?cè)趦杉业赇佡I的東西加起來(lái)總共還不到100克朗,也就是4美元。而在皮爾森街頭晝夜?fàn)I業(yè)的華商店鋪大約有十家,就算每家店鋪都可以遇到我們這樣的顧客,他們每天晚上的毛利潤(rùn)也就只有2美元,算上成本,最多只能掙幾十美分。在一個(gè)高福利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幾十美分有什么用?
我相信在這里開店鋪的每一個(gè)華商都有捷克的護(hù)照,否則他們根本拿不到經(jīng)營(yíng)執(zhí)照,既然是這樣,那他們就可以享受高額的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xiǎn)和連美國(guó)人都羨慕的歐盟福利,但他們?yōu)榱诉@幾十美分,還在徹夜堅(jiān)守。我想,這筆賬與金錢無(wú)關(guān),全在骨子里的民族性當(dāng)中,就算過(guò)了五代人、十代人,或許也無(wú)法抹掉。
多年之后,我若想起皮爾森的夜晚,恐怕腦海里第一個(gè)浮現(xiàn)的,就是昏暗的燈光下同胞那熟悉的面孔。這印記,無(wú)論過(guò)多久都難以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