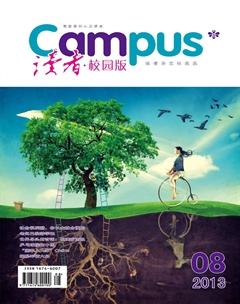乒乓球控在中國
克里斯托夫·比恩

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是北京的一所精英體校。我第一天去那里,常教練把我介紹給他乒乓球班的學生們:“從今天起,我們有了一位來自美國的新同學。”常教練在室內還戴著一副墨鏡,他一邊說一邊從眼鏡上方瞅我。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頓覺緊張起來,好像又回到了上幼兒園的第一天,只不過這回我都有胸毛了。“據他自己說,他打乒乓球已經超過10年了,”常教練繼續介紹,“但我看,倒像是10天。”全班爆發出一陣哄笑。
什剎海體校的地下室有3個乒乓球大廳,我們在其中一個大廳排好隊。這個巨大的體育館內有27個球臺,墻壁上掛著中國國旗,到處是攝像頭(常教練說是出于安全考慮)。在這里,大部分學生是從全中國各地的學校選拔來的。在支付了每節課25美元的高昂學費后(這是外籍學生的收費標準,中國學生每年的學費在1500——5000美元間,包括上午的文化課和一天兩次的乒乓球課,還有食宿),我也成為這里的一員。報名時我就知道自己會是一名大齡學生,但我并未意識到,自己的年齡會是其他學生的3倍。此刻,在我兩側各站著12名8——12歲的孩子,他們身體瘦高,穿著整齊的隊服和短褲,留著幾乎相同的寸頭,而我則是隊伍中顯得最傻的那一個。
對于乒乓球,我曾有不敗的歷史。小時候,我纏著家人和我打球,弟弟們常被我“打”得直哭。大學畢業后,我住進一幢單身公寓,一次生日,女友送我的禮物就是一張乒乓球桌。我站在球桌一側,痛擊一個個挑戰者。不是他們太差勁,實在是我技高一籌,削球、對角球、側旋球都打得得心應手。最終,公寓樓里沒人再敢應戰。
去年夏天,我因工作原因來到北京,乒乓球自然而然成為我展開社交、融入當地的門路。這項運動在中國隨處可見,想到1971年重啟中美關系的“乒乓外交”,我更加信心百倍,如果乒乓球能讓中國人喜歡上尼克松,那他們也必定會喜歡上我。
我在什剎海體校的第一個對手是一個面帶微笑的小男孩,個頭剛到我的胸。在常教練的指令下,我們走到球臺邊開始練習。男孩發球,球越過網,擊中我這一側的球臺;我揮拍回擊,球彈過網,但并未打中他那側的球臺,而是飛得老遠。就這樣,在我連續25次回球失敗后,我一下子不會打球了,仿佛拿在手中的不是球拍,而是一個平底鍋。
常教練叫了暫停,我被安排到另一個球臺,一位年長的張姓教練正在充當發球機。他站在球臺一側,不停地從桶里拿出球,并把它們發過網,每個發球都有著同樣的速度、角度和節奏。一名學生在對面弓著身,以同樣完美的速度、角度和節奏回球。
輪到我練時,張教練糾正起我的拿拍方法來。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用的是“握手式”拿拍,把球拍握在手里。我以為張教練會讓我學習大多數中國人用的“握筆式”拿拍,但他解釋說,不用改變拿法,只是按了按我的大拇指,使球拍牢牢地鎖在我手里,又掰了掰我的手腕,使球拍成為我手臂的延伸,我才知道自己以往的動作有多么不標準。下課時間到了,張教練對站在地板上數以百計的乒乓球中間大汗淋漓的我說:“下次還是繼續練正手。”“那反手呢?”我問。“8到10節課以后再說吧。”他回答道,“這里的學生有的從會走路起就開始練球了,你著什么急。”
幾周過去了,我在乒乓球課上遇到的“羞辱”并未消失,只不過以更隱晦的形式出現。那是我在體校上課第二個月的一天早上,走進體育館后,我看見兩個孩子面墻站著,我問張教練緣由,“他們練習不專心。”他回答。幾分鐘后,那兩個孩子愁眉苦臉地迎來了懲罰的第二項內容——和我練球。練習的過程和以前一樣,我幾乎無法得分,我打的每一個球都飛出界。我告訴自己,只要得1分,1分我就心滿意足了。比分到0∶10后,我的對手發球出界,我最終以1∶11慘敗。事后,另一個學生告訴我,那個小孩是故意失誤的,那1分是為了給我留點面子。
無論如何,我覺得我的球技提高了。弓著腰數小時練習前后揮拍,不管鍛煉的是哪些肌肉,它們都變得更強壯。但我的壞習慣仍存在,我不愛移步,不愛轉身,動手腕不勤,發球不會帶轉兒。
總之,我打了10多年的乒乓球,現在得重頭來學。“我兒子都比你容易教。”常教練說的是他6歲的兒子,“雖然他練得還不夠,但他的動作都是正確的。你很努力,但動作都是錯的。”為了證明他說的話,常教練讓他的兒子站在球臺前,和我正手對練。這個孩子也許還在玩拍手游戲,但我打過去的每個球他都能接住。
中國人稱霸乒壇有各種解釋,從科學的到文化的,再到體制的,但中國最大的優勢也許是參與這項運動的人數。美國女子奧運乒乓球隊前教練蒂爾多·喬治回憶自己訪華時的情景,她聽見一位廣東官員抱怨該省“只有”500萬人打乒乓球。蒂爾多說:“你可以想象我當時有多吃驚。”不像足球或者籃球,乒乓球不需要太大的空間——只需一張球臺、兩個球拍和一張網(或者一排磚頭)。就像沒人比美國小孩更會打棒球,沒人比巴西小孩更會踢足球一樣,沒人比中國的孩子更會打乒乓球。
數周的訓練課過后,我準備好迎戰我第一次真正的比賽——與北京的退休人士過招。那是一個晴朗的休息日,我騎車去了后海的一處公園,我知道在那里我肯定能找人打上幾局。公園里全是身穿運動服的老人,做著各種中國式的運動。當我走近乒乓球臺時,人們都看我。我肯定不是他們看見的第一個外國人,但有可能是第一個帶著自己的球拍和球來打球的外國人。一個戴假皮帽的人要看我的拍子,他把球拍貼近臉,用拍把敲了敲頭,以聲音判斷木頭的質量。“你花多少錢買的?”他問。“超市里花25元買的。”我回答。“質量不行。”他說,然后給我看了他的拍子。球拍一面是他剛換的新膠墊,另一面是裸木,上面有一處深深的凹痕,那是他用了30年的見證。“這拍子只花了3塊5。”他得意地說。言下之意是,我不但能打敗你,而且還更省錢。
一位身著粉色棉背心、身體結實的女士,正在和一位銀發老先生打乒乓球,后者足蹬橙色襪子和閃亮的黑色運動鞋。那位女士堅持讓我接替她的位置,對面的老先生先發球(他的球拍花了500元)。他用一只手將球拋向空中,乒乓球幾乎快飛到我們頭頂的禿樹枝,隨著他重跺一腳,球被彈過網,動作嚴絲合縫,跺腳聲掩蓋了球拍擊球的聲音,以至于我無法判斷他是用球拍硬的一面還是軟的一面擊球。
運動員總喜歡將他們從事的體育運動與國際象棋相比——擊劍就是拿著劍的國際象棋,拳擊就是會有腦震蕩的國際象棋。但乒乓球在我所知的比賽中,是最類似于國際象棋的,因為它帶轉兒。每一個球都需要瞬間計算,球員需要判斷其旋轉程度,以相應的反旋轉回球。“國際象棋中,你可以判斷接下來的三四步棋,”什剎海體校的張教練說,“但對于乒乓球,下一步的可能性是無限的。”那位銀發老先生的轉球從一開始就讓我處于防守,他贏了第一局。我變得咄咄逼人,試圖以力量抗擊旋轉,借助幾股有利于我的強風,我贏了第二局。第三局我又輸了。但在過去幾周里,我一直被一群小屁孩壓著打,這次輸給一個成年人,我仍有勝利的感覺。
如果你從小在美國玩體育,那你肯定知道每個人都會得到獎杯。但在什剎海體校接受了3個月的乒乓球訓練后,我還什么都沒得到,除了備受打擊的自尊和拇指上的水泡。因此,當聽說5月初社區有乒乓球錦標賽時,我立刻報了名。比賽在北海公園進行,它將是證明我實力的機會。
比賽那天,我6點鐘起床,騎車到公園。還有1個小時比賽才開始,場地上已經人頭攢動,每張球臺兩側的選手們都在熱身。我先抽了個號,好盡早知曉我的對手。當我看見他時,我舒了一口氣,除了人種不同以外,他可以做我祖父了。裁判叫號后,我們開始熱身。他的球風簡單,沒有花哨的動作,這對我是個好征兆。比賽終于開始,老人先發球——至少我認為他已經發了,雖然我的球拍完全沒接到球。突然之間,我仿佛又回到第一天在什剎海體校時的情景,每一個球打到我拍子上都飛出去好遠。我連輸了幾分后才搞清楚狀況,他發的是古怪的側旋球,我從未遇到過,也不知道如何回球。我試圖在腦子里盤算著招數——如果他發的球這樣旋轉,我就應該那樣移動我的球拍……等我盤算好,老人又使了另一套轉法,我還是沒能把球回過去。
我想說的是,這個場地是讓我終于能正視自己失敗的地方,否則我過去數月的經歷意義何在?隨著比分的流失,我知道是該扛起失敗重量的時候了。數月的訓練,結果竟沒有變化。比賽很快結束,我連著輸了兩局,4∶11和6∶11。我的對手勝利后過來和我握手。他今年66歲,我問他現在打球和他年輕時有什么不同。“現在我的動作慢多了。”他說。
我們聊天時,一位比賽負責人遞給我一件藍色球衣,上面有舉辦這項賽事的社區乒乓球聯盟的名字。球衣本來是給獲勝者的,但她說我應該穿上,因為人們會找我合影。盡管我可能是這項比賽舉辦3年歷史中表現最差的選手,但我仍獲得特殊待遇,我立刻把它穿上了。
在什剎海體校上課時,一次我請常教練去餐廳吃飯。他告訴我,他曾在日本教了20多年乒乓球,乒乓球甚至幫助他了解了日本社會——從教授、政治人物到工商領袖。我告訴他,我在中國并未有這樣的收獲。盡管我努力打球,但仍感覺被當做小丑、吉祥物和商業機會一樣對待。
在中國,有一種說法是,到這里來的很多外國人都是在本國混得不怎么樣的。換句話說,外國人在中國能更輕易地獲得成功。但對于我來說,恰恰相反:我在美國可是贏家,千里迢迢跑到這里卻輸了一次又一次。任何一位心理醫生都會告訴你,失敗是有益的,它教會你忍耐和優雅。當我回顧這一年的經歷,打乒乓球被只有我身高一半多的人打敗(6歲和60歲的全算上),我確實重新熟悉了忍耐和優雅這兩種品質。這些失敗也讓我明白,有時,放棄不只是可以的,而且是重要的。當我問常教練我是否有機會成為乒乓球比賽冠軍時,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下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