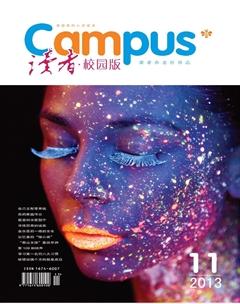《人間的詩意》第八講:心愿之鄉
編者按:2012年,《讀者·校園版》介紹過嚴凌君老師和他的“青春讀書課”。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他是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語文教師,在努力地還原語文教育的初衷。除了課堂上的努力,嚴凌君老師還主編了一套內容豐富的《青春讀書課》叢書,作為語文課堂的補充。從今年開始,《讀者·校園版》增設“講堂”欄目,請嚴凌君老師開講他的“青春讀書課”,希望更多的人能與我們共享“青春讀書課”的魅力,也希望通過這個欄目能找到更多有想法、有個性的老師,讓志同道合者相互交流,為語文教育多保留一些生機。
自己的土地
一個人對故鄉和祖國的愛,和對母親的愛是相似的。阿赫瑪托娃是俄羅斯偉大的女詩人,其詩風明快,內涵豐富。她的一生備受折磨,因為她生活在蘇維埃時期,兒子被作為叛徒抓起來了,她自己也受到政治迫害。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她的詩歌是不允許發表的。她寫下一首詩,馬上背下來,然后把詩稿燒掉。專制時代過去了,她才把它們默寫下來。在俄羅斯的白銀時代,不止她一個人這么做的,有好些作家也是這么做的,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索爾仁尼琴。
……
是的,對我們,這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對我們,這是牙齒間的沙礫,
我們把它踐踏蹂躪,磨成齏粉
這是多余的,哪兒都用不著的灰塵!
但我們都躺進它懷里,和它化為一體,
因此才不拘禮節地稱呼它:“自己的土地。”
——阿赫瑪托娃《祖國土》
阿赫馬托娃的詩表現的是詩人對自己祖國的由衷熱愛之情。
為什么每個人對自己的祖國都會有一種天然的尊敬和親情呢?告訴你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你所有的感情都是出于一種習慣,一種習俗。你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吃著這里的糧食,讓你的胃口適應了這里的中餐;你說的是漢語,寫的是漢字,你覺得這種聲音對你來說是最親切的。然后有具體的人,父母親人,朋友同學,這些人陪伴你一起成長,成為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安全的港灣。所有這些你經歷過的,讓你形成了一個概念——這是我的祖國、我的家、我的靈魂安放之處。
文化里的故國
每個人天然地都和世界有一種聯系。這種聯系通過祖國這個媒介讓我們覺得安全安寧,讓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同類。每個民族因為習俗的不同,培養出的人、人的人格品質和表達感情的方式以及他生存的方式都大不一樣。說到底,最讓人動容的是一種情感的記憶。對任何一件事、一件東西、一片土地都是一樣的,你投入了多少情感,它就會容納你多少記憶。比如余光中,他生活在臺灣,他對大陸沒有太多的印象,只不過童年生活在大陸,成年后在孤懸海外的臺灣島上,他就會對大陸充滿渴望,如同一個游子對母親、對故鄉的情感一樣。他思念的是中國人的原鄉——文化里的中國。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詩里的江南……
蘇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蓮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
春天,遂想起
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
太湖濱一漁港,想起
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
(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
……
——余光中《春天,遂想起》
這首詩有一種美妙的韻律,他通過重復的詞句,表達了一種不斷增強的節奏感。在中國,江南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它總是帶著柔情注視著你,用溫情的懷抱容納著你。這么美麗的地方當然只能發生美麗的故事。江南就好像一個國家的腹地,就好像母親,是我們溫情的源泉。作者以江南來代表母親,不僅是因為他的母親來自江南。
江南的歷史,一想起來就是江南的風光、江南的女子、江南的杏花煙雨。這樣一種記憶是文化的記憶。也就是說,每個人對故鄉的記憶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懷念。或許你們以后不在中國生活,但是你身上的記憶永遠是中國味道的,因為這種文化熏染了你的靈魂,就好像一個南方人喜歡吃辣椒。你永遠都喜歡中國煙雨山水的那種情調,中國風物,中國風土,這才是我們靈魂安放的地方。就好像我們要尋找母親的乳頭一樣,我們會回到自己記憶的源頭,無論在什么情況下。
丟失的故鄉
中國人安土重遷,有一個凄涼的詞:背井離鄉。離鄉,就是離開自己喝水的井,非常形象地表達了人和故土的依存關系。
有很多原因會讓一個人離開故鄉和故國,其中被迫的離開最容易讓人產生連根拔起的感覺。比如,中國歷史上幾次大的戰亂——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末靖康之亂等等,大量北方人口南遷;除了政治因素,還有為生存所迫,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等等。這些動輒數十萬人口的遷徙,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分布狀況,每一次遷徙都有許多悲壯的故事發生,可惜被掩埋在時間的塵埃之下。
一座城市的改名,也可以讓人丟失故鄉。當長安改名為西安,一個王朝消失了;當北平被稱為北京,一個新時代誕生了。這些重大的歷史細節,可惜中國詩人很少記錄。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記下了他的故鄉彼得堡改名為列寧格勒,他向這個心靈認定的故鄉呼喊:
彼得堡,我還不愿意死: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
可是,彼得堡已經人間蒸發,眼前是全然陌生的列寧格勒,隨時會有人破門而入,把詩人推進地獄。最終,詩人無聲地消失在流放西伯利亞的途中。故鄉與人一起丟失了,這首詩卻留了下來。
當今世上,有兩類人對故鄉的情感尤其強烈而深沉:一類是猶太人,他們從《圣經》時代就一直流浪,出埃及,尋找家園,然后經歷種族滅絕,九死一生,終于成立以色列國;還有一類是黑人,非洲的居民,被作為奴隸、商品到處賤賣,分散在世界各地。美國詩人休斯在《黑人談河流》里寫道:
我了解河流:
我了解像世界一樣古老的河流,
比人類的血管中流動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
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人類文明的源頭伴水而生,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文明,就有黑人,卻未必有黑人的家園。他們當然有資格說:“我了解河流。”
心愿之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國,很多時候我們會為她焦慮痛心,中國詩人艾青說:“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一唱三嘆,為苦難的祖國吶喊。
也有一些國家的人似乎是口含金鑰匙出生,認為自己的故鄉是上帝選中的福地天堂。比如,希臘詩人埃利蒂斯的《愛琴海》,他的故鄉是哼著歌謠的,海浪也是溫柔的。意大利詩人夸西莫多的《島》,他的故鄉是花開芬芳的,鄉音溫柔而羞澀,是童年和愛情的聲音。
對你的愛
怎能叫我不憂傷,
我的家鄉?
如此纏綿的愛,以至于愛到憂傷的境地,這樣的故國,這樣的心情,真是讓人嫉妒啊。只有幸福的國度、幸福的人才會愛得這樣憂傷,這樣幸福過度。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相信,故鄉具有治療心病的功效。一個人可以遠離故鄉,只要他的心中有個精神家園,他就是一個有家可歸的人——德國詩人、小說家黑塞在《面對非洲》里寫道:
不讓身邊的事務將我緊緊地溫暖地捆住,
因為,即使在幸福之中,我在這世上
也只能當個過客,永遠不能當個市民。
在這個家園里,有無限的美好,如果要用詩句來表達,可以是愛爾蘭詩人葉芝在《心愿之鄉》中憧憬的模樣:
……她們聽見風兒邊笑邊說邊唱,
唱一個連老者都很美麗的地方,
就是聰明人也談笑風生;
到風兒邊笑邊說邊唱時分,
心的寂寞啊就要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