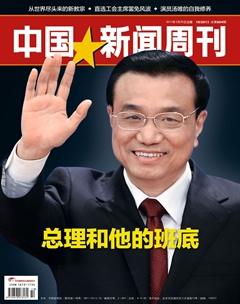齊奇:市場經濟一定是法制經濟
龐清輝
2011年3月11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報告中稱,確保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的體制還不健全,司法體制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
多年來,司法界人士一直在呼吁依法獨立審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即是其中一位。200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決定對全國26位省級法檢兩長實行異地任職交流,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當了6年常務副院長的齊奇被交流到浙江,擔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代院長。2008年1月,齊奇高票當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齊奇頭發灰白,愛上網,喜歡在西湖邊喝茶看書。浙江省一位官員評價說,“你別看平日里他總是笑瞇瞇的,和風細雨,其實綿里藏針,骨子里強硬得很。”齊奇有個老習慣,就是喜歡到基層法庭聽庭審,曾有過一周內兩次不打招呼到基層法庭旁聽庭審的經歷。
浙江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方,發生的案件也和其他省份有所不同。歷時近5年的吳英案,曾經讓浙江省高院處于輿論的中心。由于涉及民間借貸等金融案件頗多,齊奇幾乎成了半個金融專家。
兩會期間,齊奇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依法破產不是壞事,是好事”
中國新聞周刊:浙江的民營經濟很發達,該省的案件呈現了哪些不同的特點?
齊奇:浙江民間借貸十分活躍,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民間借貸的情況十分普遍。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持續上升,而且民間借貸的融資性特征越來越明顯。

按照現行央行規定,企業之間直接借貸,仍然是無效的,既然是無效就不受法律保護。這還是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就是企業之間不能自行借貸,必須得委托銀行進行貸款,叫委托貸款。
這就迫使難以獲得銀行貸款的民企,在相互之間進行的民資調劑借款都轉入地下,處于灰色地帶,往往也不能夠正規地簽訂借貸合同,只靠寫個人借條。個人借條,民法可以處理,但民法處理的個人借條借款在過去主要是生活性的、消費性的,不是融資性、經營性的,法律對這種借貸關系、利率的保護都是不一樣的。現在混在一起,其風險及負面作用更難控制。比如溫州等地,有的年利率甚至曾經高達180%。有的人為了規避“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規定,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這些“陰陽合同”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了困難。
由于高利貸的吸引,一些地方還出現了許多職業放貸人,一些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使流向分散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在高利誘惑下,也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銀行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因為資金鏈斷裂,一些企業主、放貸人出逃躲債,引發連環訴訟和信訪上訪等群體性事件,給法院審理案件和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帶來較大壓力。
如果民企間的借貸始終在地下運行,風險很大。所以應該讓它浮到地面上來,讓它合法化規范化,發揮其融資上的積極作用,遏制其高利貸傾向的消極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有沒有和銀行等部門就此做過溝通?
齊奇:浙江也做過一些突破,央行也給我答復了,說你們法院承認一些民企借貸有效,我們也認可。但實際操作中還是有問題。所以我呼吁,這條老規定要改掉。至今央行的條例還是規定無效的,只不過是默認有效,作為法治國家就應該當廢的廢,該修改的修改。當然企業也不能任意地以借貸為主業,專門炒錢就不行,要受到金融監管。
中國新聞周刊:這兩年出現了很多溫州等地商人跑路的情況。
齊奇: 這也是我最近比較關心的企業破產問題,那么多老板跑路已經演變成跑路潮了。因為浙江民營企業的借貸是互保、聯保。如果一個企業資金鏈斷裂、資不抵債,其互有擔保的民企群體會一圈一圈地相互殃及,甚至可能形成區域性的金融風險,這是我們要防范的。
如果各地法院、銀行都擁到某一個企業去貼封條、去凍結賬號,這個企業即使還有發展潛力,也肯定完蛋。對此,我們就采用指定一個法院集中管轄的辦法,訴狀都登記在冊,審理集中管轄。然后統一來考慮,這個企業還有多少訂單,還有幾條流水線可以用,是不是先緩一緩,讓它再繼續轉一轉,把那些訂單的生產經營先解決好。通過集中管轄,就是不要一哄而起把企業掐死。
我們通過依法破產重整、資產重組、債轉股等方式保持它的資產,盤活它的有效資產。也鼓勵一些優質企業來抄底、兼并,實際上就可以保留好企業的有效生產力。一個股份制的企業,無非就是老板是張三李四,現在就換成另外的王二趙五,但這個企業卻能維持生產渡過難關,獲得新的發展,員工也沒有下崗,這是最好的起死回生。我總結了一下,去年我們審理的90多件破產案子,這一類的占20多起。這樣的起死回生,使銀行和其他債權人的債權反而得到保護了。否則如果只是簡單地清算債權的話,可能償付率只有10%、5%,其他的就都壞賬了。
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是在行業產能過剩、重新洗牌當中屬于應該被淘汰的。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產能落后的企業就應當在競爭中退出市場。不過,淘汰不必用跑路的辦法,你一跑路自身就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護,企業職工也就沒著落了。
還有一種方式叫做依法破產清算,于破產重整而言是另外一個概念。破產清算就是關閉加上清償債務,但關閉是有序的,剩下的企業土地跟廠房,還可以盤活。浙江的土地資源是很緊張的,我們把這些企業稱為“植物人企業”,肯定要死的,但它拖著不辦,會不死不活地占用土地而不生效益。
中國新聞周刊:破產清算在銀行不良資產核銷時也有很多規定,銀行這方面好溝通嗎?
齊奇:我問過一些銀行負責人,你們作為債權人,為什么不愿意向法院提起申請企業破產?他們說是因為破產清算時間比較長,少則一年,多則兩年,而央行規定,必須等企業資產清算完畢后才能夠核銷銀行的不良資產。這樣就很少有銀行主動依法提起企業破產申請。
浙江這方面的情況比較突出,我們已經向省里提議,能不能先行先試,一旦經法院審查企業符合破產的立案條件,一經立案即可讓相關銀行先核銷,這并不影響清算審理之后的債權清償份額。其實銀行剝離不良資產以后,也就輕裝上陣了。
這個雙贏的政策現卡在瓶頸上,如果可行,一個月就能核銷不良資產。所以還需要有關方面來支持,來把這條路走通。破產清算以后企業就要有序地退出市場,實際上是反映了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壞的淘汰,泡沫清除,好的幸存發展起來,市場份額更大。所以破產法的實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既然如此,為什么那么多老板寧可跑路,也不申請破產?
齊奇:很多企業主不知道可以到法院申請破產,我們在這方面宣傳很少。于是他們就逃跑,結果就引發職工上訪,公安去追緝,就會查他們有沒有欠薪拒付?有沒有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存款?是屬于刑法犯罪的。可能多少會有這些嫌疑。
在國外叫做申請破產保護,萬一資不抵債了,千萬別慌不擇路地逃跑,你跟債主講,我們到法院去,我去法院申請破產。
第二個原因在于有的地方黨政領導不喜歡也不懂得企業破產的意義,只是覺得難聽。他們會覺得,企業破產多了就是我政績破產。所以他們不希望破產,工商注銷就完了。而工商注銷不負責財產的處理,財產的處理還是要到法院。這樣也影響了破產制度的發揮。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法院就搞過一大批國有企業的破產審理,當時是政府主導的計劃性破產。但現在要搞市場化的破產了,因為民營企業不能找國資委,只能走市場化、法制化的企業破產道路。依法破產是可以讓好的企業起死回生的,也能使落后企業有序退出,不是壞事,是好事。
“地方和部門干擾司法現象仍有發生”
中國新聞周刊:對民間借貸案件性質的劃分很多時候仍是不明朗的,包括吳英案在內?
齊奇:吳英這個案子跟民間借貸不一樣,當然跟民間借貸的土壤有聯系,區別是吳英案屬于詐騙。
其實,浙商、溫州商人都是很講信用的,很少有人去騙人家的錢。吳英的案子,對于刑法上的意義就是財產性犯罪與暴力性犯罪仍有區別,量刑時可盡量少殺。吳英詐騙的金額遠超以往集資詐騙死刑犯的金額,而她被判死緩。從這方面看也是有意義的。
所以說她是犯罪,與普通民間借貸還不一樣。我們現在就是努力讓民間借貸從地下到地上,使它盡早陽光化,給它合法性,又使其規范化。
中國新聞周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曾說,確保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的體制還不健全,對此你怎么看?
齊奇:社會各界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是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之一。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表明黨中央非常重視法治。回顧歷史,文革之后提出過“以法治國”,雖然大有進步,但是境界還不夠。要建設法治中國、法治國家,那就不管是領導人還是群眾、社會各界,都要受到法律約束,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司法權本質上屬于中央事權,不能過于分散,才能確保中央政令暢通。但在實際運作中,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干擾司法現象仍有發生。有的基層黨政領導把法院看作與其它行政機關一樣的工作部門,讓法院參與招商引資、包村扶貧、計劃生育等工作,有的為保護本地利益動輒要求法院如何裁判、如何執行。我們的法律是中央制定的,如果都被各地切割成只保護本地利益,那整個市場就亂了,整個公平正義的秩序就亂了。
還有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也要增強法律意識。有位人大代表說我已經拉了幾票了,如果這個案子你不判我贏的話,你就要準備在法院報告表決時看到更多反對票。我們就跟他講,是否投反對票是你的權利,但公正司法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決不會做臺下交易。其實這位人大代表對自己的定位還不清楚,人大代表不是代表你個人或你的企業,而是代表群眾。說到底,還是一個法制觀念問題。
法治中國雖任重道遠,我們會矢志不渝,一代一代接力奮斗,我想一定會達到的。尊重獨立審判,尊重司法權威,今后肯定會有更大的改觀,包括兩院的憲法地位的進一步落實。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是法制經濟,沒有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