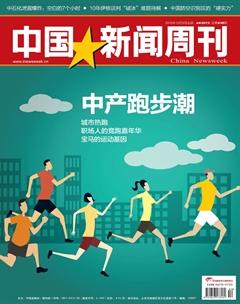名人書信,小眾收藏到大眾投資
馬海燕

周作人絕不可能想到,自己上世紀50年代被兩家報紙退稿的《元旦的槍聲》,60年后在拍賣場上竟被高價收購。這位民國知名作家那時請求報章發表的原因,不外是為自己正名,讓更多人體會自己做“漢奸”的無奈,如今這封信原原本本呈現在后人面前,標上了價簽供人競買。
11月12日,一年一度的嘉德秋拍如期登場。名人信札只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但卻是古籍善本部分最重要的“開場戲”。著名收藏家方繼孝比喻,“這好比戲劇舞臺上正式演出前的‘序曲,魯迅、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新文化運動大家的整齊亮相,意味著后面‘正戲的絕對分量。”
古籍善本5大專場最終成交額近5600萬元。其中,信札寫本表現亮眼,魯迅的《致陶亢德信札》200余字拍出655.5萬元;李大釗《致吳若男(章士釗夫人)書札》以414萬元成交;陳獨秀《致陶亢德書札》成交價230萬元。
20年:從十萬到數百萬
1994年,魯迅的一篇《論言論的自由》就拍出了10萬元,由一位新加坡華人買下后捐給了上海魯迅博物館;而今,一頁魯迅手書《古小說鉤沉》手稿690萬元成交。此次秋拍,魯迅致陶元德一封信估價就在180萬元至220萬元之間。
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拓曉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世紀90年代起拍時,一般是一篇好幾頁,現在已經論頁定價,此次秋拍出現的魯迅信件一頁定價就100萬。”
上世紀90年代前半期,一場古籍善本的成交額大概在400萬元,而現在一場過4000萬元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前幾年市場行情好的時候,最高一場拍到8000萬元。2012年整體形勢不佳,古籍善本板塊卻表現搶眼,總成交達9840萬元人民幣,原因不過是相對于動輒數千萬上億的中國書畫,這些信札還是顯得“便宜”。
讓拓曉堂印象最深刻的是1998年、1999年拍賣過云樓書信時,連續拍了四場,最終收獲千萬。
可那時還遠沒到十年后的瘋狂。
1994年翰海秋拍中有一冊15通的徐悲鴻信札,估價10萬元,平均每通約6000元,但最終流拍。10年之后的2004年1月,同樣在翰海,估價10萬元的3通徐悲鴻信札,以24.2萬元拍出,每通均價突破8萬元。
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孫中山致葉恭綽書札4通達到了111.1萬元高價。
2005年,黃賓虹致陳柱書札18通,曾著錄于《黃賓虹書信集》,拍出了55萬元。
2009年,國學大師陳寅恪的112件手稿,成交價是285.6萬元。弘一大師的77頁手稿,拍出了257.6萬元。
2010年嘉德秋拍,周作人的文稿去年底在嘉德以358.4萬元成交,創下了周作人手跡的拍賣紀錄。
即使在整體市場處于調整期的2012年,嘉德春拍一本朱自清的楷書七言詩札以161萬元落錘,趙之謙信札120.75萬元成交,趙孟信札10通299萬元被買走。
從幾百塊到幾百萬,中國的書札市場歷經不到30年時間。現在再去潘家園、什剎海等舊貨市場已經不可能淘到當年那樣的寶貝了。
“用20、30年時間經過了人家一輩兩輩人走過的路,這樣后代怎么去想?”拓曉堂見證了全過程,仍覺得不可思議。當然,這與中國同時期的經濟整體發展同步,拍賣行也是其中的一個縮影,而那些故紙堆遭到瘋搶不過是“縮影中的縮影”。
從地攤貨到拍品
方繼孝把整個信札收藏分為三個時期:90年代前拍賣公司還沒興起的地攤時代、1993年到2002年拍賣時代、2002年至今的火爆時代。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還沒有拍賣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書札作為書畫的一部分收藏,那時的書信還屬書畫、小品范疇。市場來源主要在古董書店、郵票市場、還有民間自發形成的跳蚤市場,如北京的潘家園、什剎海、雙龍、月壇、亮馬橋等地都會出現。
那時候的潘家園,逢到周六日就有很多賣書札字畫的,方繼孝還記得買一沓子書札(相當于幾本書的厚度)只要500到800元人民幣。在人均工資只有幾十塊錢的時候,這也價格不菲,只有真正喜歡的才舍得花錢,也培育了一批收藏家。
在北京月壇的郵票市場,有的連郵票帶信封和信,可價格還是按照郵票的票面價賣,信封和信屬于附贈。那時候流落舊貨市場的信札一部分來自“文革”中被抄家的物品退賠,一些文人、干部后代認為舊書還有些收藏價值,舊書信沒什么用,就當廢舊紙變賣了;另一部分來自于國有出版社、報刊社、國家機關的文檔處理。“文革”后許多文化單位搬家、擴建,整理文檔時諸如作家來稿、作家與編輯的通信等,常被當作廢舊紙張變賣處理。
1993年內地第一家文物藝術品拍賣公司中國嘉德誕生,信札被納入拍賣品行列,那時書札還歸入書畫板塊。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嘉德第一次書信拍賣征集的廣告一發出,許多人就帶著東西上門了,很多并不來自作者本人或后人。說明這些拍品就已經在民間倒手多次。
1994年,拓曉堂組織起嘉德第一場古籍善本秋拍。他仍記得,古籍善本大約20件左右,占整個拍賣的四分之一,重要拍品有魯迅、林琴南、孫中山、吳昌碩的書信等,整場大概拍出20多萬元。
那場拍賣會上,已是知名收藏家的方繼孝花2000元拍到了林琴南、王國維等人的冊頁,有幾十頁之多。
在拍場上,他主要買晚清時期的珍貴信札,如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翁同,這些人的書法本就精湛,加上書信所談論的往往都與時局相關,價格并不高;而另外一些如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的信札,他還能去市場上淘到。
他就曾在舊貨市場花幾百塊錢買過人民文學編輯部與上述各位作家的通信,也曾淘到過吳玉章、成仿吾等人寫給文字改革委員會談文字改革的信,李四光、裴文中寫給當時的地質部的信,這些信既有書法的美,又有文化信息,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都極高。
有了拍賣公司給作品定價后,一些地攤攤主也逐漸把東西送到拍賣公司,市場總體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
2002年,魯迅博物館為了紀念魯迅赴日留學100周年,搞了一個“民間收藏家精品展”。100通書札吸引了許多人來,國家圖書館找到方繼孝,請他寫寫書札背后的故事。6冊《舊墨記》隨之出爐,這也在后來成為許多仿品的參照。
這一年,書札正式從書畫拍賣中剝離出來,開始作為古籍善本的“序曲”出現在拍場。“如果書札檔次很高,整個古籍專場都值得期待。”方繼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02年秋拍中,“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就以990萬元成交,打破當時古籍善本的拍賣紀錄。信札拍賣市場開始進入成熟期。
2003年,方繼孝花27000元買了鄭振鐸的三封信時,“當時人都說我瘋了。”之后書信拍賣直線飆升,即使像方繼孝這樣的“瘋子”,也只能看而不買了。
2009年春拍中,陳獨秀、梁啟超與徐志摩等致胡適的一批書信,創下744.8萬元的成交高價。這個轟動性大事件標志著信札拍賣一個新的時代來臨。
書信背后的情感與未完的故事
拓曉堂說,現在市場受追捧的名人手跡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手稿;第二類是名人書札信件。前者如此次秋拍出現的周作人的《元旦的槍聲》,后者如這次出現的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健將的信件。
名人信件中,一類是關系不熟,學術往來,有文獻價值;第二類是密友,談論朝堂上不能說的話,有歷史價值,這往往都構成書札的魅力所在。“文稿、書稿的原始稿,說白了就是書札,從中可以窺見作家真實的創作狀態。” 拓曉堂說。
拍賣市場上的書信,人們往往更為看重作品的上款和抬頭,作者因何原因送予什么人,往往被當作一段佳話,書信更承載著直接而坦白的情誼。
然而,當一張泛黃的舊紙動輒帶來幾十萬上百萬的收益時,情誼在后人眼中已經是另外的含義了。
2012年周作人的后人與唐的后人圍繞“周作人的書稿何以成了唐藏書”引發糾葛;同年,梁啟勛后人拍賣“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引發梁啟超后人聲明抗議;今春,錢鐘書給某出版社編輯的書信和文稿出現在拍場,圍繞人情與法律展開了一場持久的較量,最終以委托方的撤拍而告終。
拓曉堂說,這些年這樣的事看得多了。作為拍賣方,只要拍品不涉及違反法律,就只有尊重委托人的意見。其實,懂行的人都知道,這類事情在拍場上更多見的情形就是悄悄拍了就拍了。
也有兒子、孫子拿著祖上的東西來拍賣的。當一個人只剩下出賣祖宗的那點東西,不管曾經多顯赫的門第也就氣數已盡了。
啟功曾在某拍賣公司看到一份自己在“反右”期間的交待材料后憤而離去。原因是拿著這份材料的人當時曾找過啟功,求一幅字而換回這封信。啟功把字寫給了對方,信卻沒有送回。
2005年,在上海嘉德秋拍上,郁達夫致王映霞的8封情書以34萬元高價成交。“我很真心,我簡直可以為你而死”,當年窮困潦倒的郁達夫如知自己如此私密的表白竟以如此價格估量,不知作何感想?
嘉德今秋展出的一幅信札中,有一封袁世凱寫給端方的密信,信中稱“日本人狼子野心”,并囑后者看完“付丙”(即燒掉),結果不僅沒有燒掉,反而流傳至今。
隨著電腦、手機等電子化書寫手段的普及,也許有一天我們連“付丙”的機會也沒有了。方繼孝預計,未來的信札價格還會走高,一是因為沒有手寫信了,二是這個時代也沒有名人了,這些信札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顯得珍貴和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