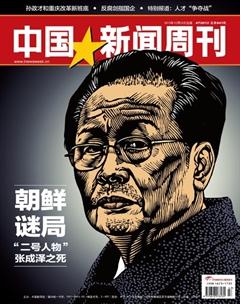全球視野下的災害預防
瑪格麗特·瓦爾斯特倫
過去三十年來,伴隨著全球氣溫的逐步上升,洪澇、風暴潮、颶風以及干旱等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損失也不斷攀升。越來越多的政府官方數據顯示,自本世紀以來,全世界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已經達到2500億美元之多。不僅如此,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最新報告發出警告說:最糟糕的情況還在后面。
當然,全球氣候溫度升高導致的急劇天氣變化,是災害性損失產生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我們的準備措施不充分而造成的損失,也是情況更加惡化的重要因素。
如今,為了滿足不斷擴張的人口需求,大量的投資進入了關鍵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拓展以及城市發展領域,預計在2050年,這些領域的投資額將會達到90億美元。但是,這樣大規模的投資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災難風險。正是由于沒有綜合考慮對這些新興經濟領域的資產保護措施,因而在未來幾十年中,災害造成的損失將會急劇增長。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氣候變化的預測應該能夠促使政治家和商業領導者們重新調整他們的災害風險預期。我們的決策者必須意識到:世界上沒有單純的自然災害,只有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工作場所、房屋、道路、學校、醫院,以及各種公共設施產生的災難性影響。
2004年,印度洋海嘯摧毀了11個國家的海岸地區,造成了15萬人死亡,50萬人受傷,最終導致了100多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自此次海嘯之后,168個國家達成《兵庫行動框架》(HFA) 的一致意見。這一框架制定了一個十年的綜合減災計劃。
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卡特里娜颶風再次凸顯出這一計劃的重要性,并創造了全世界受保險保護的經濟損失的年度新紀錄。而這一紀錄在2011年由發生在日本東北部的地震與海嘯災難再度被刷新。
到目前為止,《兵庫行動框架》的實施產生了較為復雜的結果。盡管提前預警系統等改善措施減少了災難中的死亡率,但是,災難造成的經濟損失仍在持續飆升。究其原因,在于太多的投資者不顧基本的常識,在土地利用和基礎建設當中更傾向于追逐短期利益。
對一些環境與生態條件脆弱地區的持續開發,尤其是對海岸地帶的開發,極大地增加了經濟資產暴露在災害當中的風險。例如,全球每年暴露在熱帶氣旋風險之下的GDP比例,由20世紀70年代的3.6%增長到21世紀前十年的4.3%。
另一方面,洪澇災害所帶來的經濟損失風險也在逐漸增長,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首當其沖。
以美國為例,2010年的普查數據顯示,39%的人口居住在海岸城鎮。處于海濱地帶的房屋數已達到4900萬間,而且,這些地區日均有1355個建筑項目通過審批。這樣的聚居模式極大地加重了去年桑迪颶風造成破壞的程度,桑迪也因而成為美國歷史上造成第二大經濟損失的颶風。
當然,如今并不全然是壞消息。
挪威正在積極建立以提高洪澇與風暴潮防護水平為目標的標準,并且在過去的四年里已經通過立法形式,發布了一套新增的建筑分類體系。其中要求醫院這類關鍵性的基礎設施必須達到能抵抗一千年一遇洪災的水平(即指某一年內發生概率為0.1%的洪水等級)。而居民房屋也要求必須能夠達到抵抗兩百年一遇的洪災的水平。
與此相類似的是,新西蘭在2010年與2011年坎特伯雷地震之后,提出了《基督城城市發展策略》。這一策略的目標,著眼于實現城市效率、宜居程度與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最大化。在這一策略中,最適宜發展地區的選定主要考慮交通、城市規劃以及房屋和水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因素,以應對地震、洪澇以及巖崩等自然災害。
鑒于減少不必要風險的措施可以大大地節省資金,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可避免的損失,挪威、新西蘭等國所采取的這種規范性解決措施有著極大的經濟意義。
在這樣的考量之下,即將于2015年實施的第二次《兵庫行動框架》,將會強調建筑方式的改善以及土地利用的透明化與決策過程的明晰化。同時,也將重視私營部門的作用——這樣做,是考慮到在多數經濟體中,私營部門的投資占據了整體投資額的70%至85%。
以上種種措施所帶來的結果是——為人類提供更加安全的居住條件。與此同時,也將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效益。
(譯/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