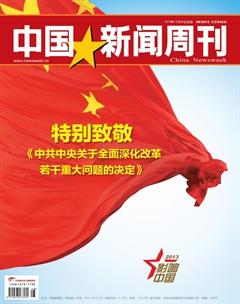以獨立視角直面中國教育
陳薇
獲獎理由
作為中國唯一一個致力于教育改革研究的民間非營利機構,幾乎中國每一個重大的教育改革,都與其持續地多方奔走、呼吁以及調查研究有關。從2003年起,研究院每年出版的《中國教育藍皮書》已是中國教育領域的一個指標性文本,2008年開始的“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開創了第三方評價政府教育績效的先河。10年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始終在實踐自己的承諾:以獨立視角研究教育問題,以社會力量推動教育進步。

“你打算讀高中嗎?”“你今后希望在哪里生活?”
這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在中國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3年農村初中生調查問卷中的兩個問題。
答案讓人深思:1598名農村初中生中,打算上高中的只占69.7%,而愿意生活在現住地的更少,僅5.2%。
“這便是我們農村學校的常態。培養單一的、‘超脫的理想,將村娃子鎖在鄉土之外,無形中教人力求逃離農村,這些接受了‘離農并且低質量教育的農村孩子,步入社會時對自己的命運將有怎樣的解讀?”12月初,研究院將數據發布,引起廣泛關注。
這個已成立11年的民辦非營利組織,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創新研究為主,致力于獨立的專業化研究、廣泛的公眾參與,希望最終推動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我們的愿景是成就最具公信力的民間教育智庫,目前可能只達到20%,”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有些驕傲,也有些不滿足,“但要是按規范的、可持續的、專業的民間教育機構,我們大致完成了一半以上。”他64歲,頭發花白,不過說起研究院時,雙眼仍閃爍著熱切的光芒。
“信息拼圖”
“美麗鄉村教育”公益評選,是研究院在2013年的重要活動:4月啟動,經過自主申報、專家和媒體推薦,共發現80多個典型案例;項目官員隨后奔赴各地現場調研,漸漸篩選出10個優秀案例,在年終的高峰論壇上分享。
現場調研工作常常由院長楊東平帶領。“他喜歡到各地去跑,比我們年輕人更有力量”,一位項目官員評價他。但對于楊東平來說,這樣的工作常給他帶來激情。
比如,在四川東北部貧困縣閬中的調查,便使人驚喜。一般農村學校大多蒼白空洞,閬中的學校完全不同:孩子們學書法;教室墻上掛著種在可樂瓶里花草;每個門都繪上畫,稱為“門板文化”;大多數學校有菜地,既種菜,也是學生勞動基地;不少學校還有豬圈。楊東平看后感嘆,“這種粗茶淡飯的教育不僅合于水土,可以持續,而且真正可口養人啊!”
當然,閬中僅是特例,中國農村小學的整體情況并不樂觀。據研究院的《農村小規模學校建設研究報告》,近半數(48.8%)村小沒有運動場;在非走讀村小中,約三成(29.1%)無食堂;在寄宿制村小,75%的學校每間宿舍住10名以上學生,最多的一間宿舍要住40名學生……
這種“以案例式、田野式的發現,完成一幅信息拼圖”的調查辦法,如今已成為研究院的主要調查和工作方式。僅2013年,研究院就發布了《中國在家上學研究報告》《中國教育公益組織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報告》《北京市“小升初”教育信息公開情況調查報告》等多項調查報道。
執行院長黃勝利說,這種扎實的田野調查,是民間研究機構的優勢,同時也是民間研究的價值所在。
民間智庫比政府的目光更長遠
研究院每年的例行工作有:組織年度教育高峰論壇,出版當年《中國教育藍皮書》,隔年舉辦“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兩個月一次研討會,每月舉辦一次教育沙龍,每半個月出版一期《教育雙周刊》……
很難想象,完成如此體量工作的,是一個僅有11人的專職團隊,其中有轉型公益的記者,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教育相關領域的前公司職員。
楊東平是研究院的精神領袖。他出身“紅二代”,生活簡樸,常和組員們一起吃盒飯,總是騎一輛舊28自行車,穿行于大學校園。研究院每個選題的確定、每份重要報告的發布,以至活動宣傳材料上的用色,他都親自給定意見。
2004年,楊東平以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的身份,受聘出任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這是研究院的前身,2002年由時任蘇州市副市長朱永新在蘇州創建,主要集合民間教育集團,開展教改實驗。
楊東平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也是環保NGO“自然之友”發起人之一,與教授生涯對比,他“深刻地意識到體制內的事、學校內的事,很難改變。但在NGO,可以做很多事”。
楊東平擔任院長后,北京部分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工作單位,2008年下半年正式獨立,組成了包括新東方聯合創始人徐小平、著名畫家陳丹青等人在內的理事會,更名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
最初的辦公室是北京理工大學一間教師宿舍,楊東平的三四位研究生,擔任兼職研究員。但集沙成塔,幾年間,研究院始終堅持以獨立、積極的姿態介入社會生活和輿論場,漸漸成為教育重大話題的“民間聲音代表”。
他們開創了第三方評價政府教育績效的先河,舉辦“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推出了民間版中國教改方案;發布北京小升初狀況調查,呼吁對奧數、高考、擇校熱等教育問題的公眾討論……
“政府只關心三五年的事,而民間智庫應該關注十年的事兒。”楊東平說,而且由于民間智庫的獨立立場和公立追求,有可夠持續推動一項重大政策的轉變,進而推動教育創新和社會變革。
見證自下而上的變革
21世紀教育研究院提出的一些觀點,已被各地政府直接或間接采納。湖北省教育廳受研究院的教育制度創新獎的啟發,也設了一個教育制度創新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制定過程中,研究院多次提出,“要用個性發展概念取代全面發展”,這個建議后來在《規劃綱要》中化為“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相統一”。
由于關注的都是敏感話題,研究院常常受到攻擊。批判奧數教育時,就有憤怒的家長在網上留言:普通人的孩子想升好學校,只有奧數這一條路了,不能把這條路堵死。
楊東平不以為意,他看到的是中國正以國家力量,從童年起便把每個人驅趕到同一條應試教育道路上去,“退化速度之快、惡化之激烈,是中國前所未有”。
他因此特別珍視那些火種般的教育改革:山東杜郎口中學撤掉講臺,搬走講桌,實行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改革;浙江上虞在學校里設立鄉賢學習分會;友成基金會正將人大附中初一的數學課,直接通過視頻同時上到鄉村中學去……
“近些年來,很多教育改革,都是首先在邊遠地區學校發生的,”楊東平說,“教育創新的核心概念,正是自下而上的變革。有人覺得我是個偏激的批判者,不過我也因為看到了很多基層變革,在某種程度上又對中國教育充滿信心。”
2013年,研究院第一次成為變革的主體。他們和福建連城縣教育部門合作,創辦了培田實驗小學,開展鄉村特色教育實踐。2014年,研究院決定將教育信息公開作為切口,推進微小透明。
研究院希望成為變革的發現者、參與者和推動者。然而現實常常鐵板一塊。比如,他們在北京地區研究小升初的體制改革,每年都在奮力高呼,卻幾乎毫無變化。
“我們做的很多事情,難道不是在隔空打墻嗎?”研究院2012年年會時,一位研究員對楊東平說。
這位臨近退休的老人回答:“我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這一次,他沒有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