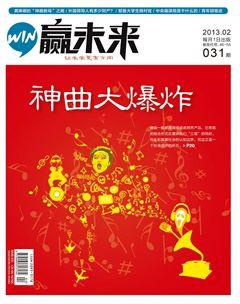90后大學生的新沙龍運動
1月19日,“706青年空間”來了一群特殊的年輕人。這些來自清華、人大、中大、武大、南京特殊教育學院等國內十幾所高校的大學生利用寒假,來參加一個名叫“706空間寒假青年營”的活動。“706青年空間”在人人網的公開資料顯示,為期三天的活動內容主要有“同道讀書會:社會主義的可能與不可能”、“獨立紀錄片及民謠音樂會”、“口述歷史和青年擔當”,他們甚至還請來了紅極一時的北美“崔哥”說脫口秀。
“706青年空間”是1 2位在讀或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在大學云集的北京五道口租下的一間小屋,他們利用這個空間舉辦一系列獨立活動,同時提供背包客住宿、圖書借閱等服務。
2012年11月24日是“706青年空間”的開放日。當日,主辦方邀來14位青年講者分別用15分鐘講述自己的感悟,內容涉及攝影、中醫、印度旅行、飛行部隊等方方面面。同一天在這里進行的活動還包括佛學沙龍、讀書會、獨立電影放映等等。
“706青年空間”基本都是依靠微博、人人、豆瓣等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宣傳,它在人人網上的公共主頁有5907名粉絲。它發布的活動預告常有幾百人閱讀和留言。近幾個月來,“706青年空間”還通過網絡募捐的方式籌集了7萬余元資金。
事實上,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的類似交流平臺不在少數,廈門的“碧山公共空間”、無錫的“春暉論壇”、南京的“先鋒論壇”等都在逐步擴大影響,并且其中不少已經發展出較為穩定的參與者群體。
臺灣交換陸生回大陸辦沙龍
人大社會學系大三學生周雨霏是“勺見沙龍”的創辦者,她一年前以交換生身份赴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她參與了清大許多沙龍活動。臺灣學期快結束時,周雨霏與一起交換的廈大女生商量,兩人都希望把清大的沙龍氛圍帶回自己所在的高校,那名廈大女生返校后就參與到“碧山”的活動和建設中,周雨霏則回到人大創辦了“勺見”。參與創辦南大“先鋒論壇”的束沐同樣有臺灣交換生的經歷,期間他也參加了多場校內外講座和討論。
周雨霏說:“沙龍這個東西在他們那里是很正常的,可是我們這里就沒有,這是很奇怪的。”希望同學之間可以對共同關注的話題進行更多交流和討論,可以說是大多數學生創辦校園交流平臺的初衷。
從校內到校外
“706青年空間”的構建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4月,當時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的鄔方榮在人人網上發了一個帖子:“讓我們花2000元在五道口開個咖啡廳吧。”參與創辦了“706青年空間”的新疆女孩努爾比亞說:“當時還有很多人回應,大家都很激動,覺得第二天就能把這地方開起來似的。”
鄔方榮說:“我們在一起商量的時候就覺得確實需要這樣一個平臺,一是青年組織之間比較孤立,各個組織之間很多事情不了解、不溝通,他們缺少一個相互溝通的平臺;二是覺得在北京做活動,場地確實比較少,而且如果活動的主題或者嘉賓比較敏感,學校不批準,可能這個活動非常好也辦不起來。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做一個青年人的獨立空間。”經營一家咖啡館對于這些青年人來說畢竟事項復雜而且成本高昂,他們最終決定從小做起,共同出資在五道口租下一間小公寓作為活動空間。經過近一年的討論和籌備之后,“706青年空間”終于在2012年3月正式開業。
廈門“碧山公共空間”的創辦初衷與“706青年空間”某程度上是相似的,一群廈大學生在2011年4月合伙租下了校內的一間職工宿舍。有了這個空間以后,他們開始在這里舉辦放映會、讀書會、接待來到廈門的各地學者、NGO和背包客。在接待了幾位在官方看來較為敏感的學者之后,廈大以出租手續不合法為由要求“碧山”從校內據點遷出,這批學生輾轉在廈門碧山路租下現在的空間,并取名“碧山”并繼續開展活動。無錫的“春暉論壇”同樣迫于校方的壓力在2011年將舉辦地點遷往校外。“碧山”和“春暉”在遷出校園后都有了更大的發展。
低組織化規避風險
“勺見沙龍”現有的核心主辦者只有四人,都為同班同學,因此活動的組織從來無需開會,只要在宿舍或在課間稍加討論即可,工作人員也沒有明確的分工。“勺見”的主辦者們無意改變目前松散的組織狀況,他們表示,這樣既有利于保持勺見的親和、多元和開放;還可以規避政治風險,若將來真的觸動了敏感話題,可以避免被定性或追究組織者責任。同樣的低組織化現象也出現在大多數的校園沙龍中,主辦者所給出的原因多與“勺見”類似。
“706青年空間”則在嘗試對自身進行組織化和制度化,他們將主要人員劃分為組委會和管理團隊。其中組委會主要由創始人員組成,負責對重大事項進行決策,而管理團隊負責“706青年空間”的日常運營,但目前組委會與管理團隊仍有不少人員是重合的。
“勺見”現在依靠活動現場的募捐勉強達到收支平衡,同樣依靠募捐維持的“碧山公共空間”則因為要負擔房租和水電費用偶爾需由主辦者墊付虧損,而南大“先鋒論壇”仍在通過尋求外聯小額贊助的方式艱難維持。經費拮據或主辦者自行出資的情況,在學生自辦沙龍中非常普遍。
“706青年空間”正在嘗試建立自己的經營模式。由于落戶在租金高昂的五道口,“706青年空間”每月的運營成本動輒上萬,若無法找到自主盈利的模式,它肯定是難以維持的。“706青年空間”目前計劃通過向其他組織租賃場地、收取活動入場費、有償接待背包客等方式獲取收益。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價值中立
說起青年人的沙龍,許多人想起的仍是80年代。畫家陳丹青說:“我很懷念80年代,為什么?很簡單,90年代以來,這樣一種氣氛沒有了——一個人群持續在各個領域制造興奮感、制造話題、打開觀念,這樣一種自發的體制和體制外互動的大范圍結構,在社會上、在知識圈、在大學差不多不可能再有了。”
許多80年代的沙龍不僅帶有鮮明的政治價值和立場,探討的話題也往往著眼于社會、法律、行政制度的建設。然而在新媒體時代興起的青年自辦交流平臺則大多將自身定位為價值中立的平臺,在討論的話題上也傾向于談更多“問題”,談更少“主義”。
“706青年空間”的活動著重于青年人相互交流各自的經歷、想法,名人講座活動也涵蓋政治學、哲學、國學、宗教等領域。鄔方榮說:“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平臺,不可能強輸觀念給青年人。”
主創者全部為社會學學生的“勺見沙龍”目前探討過的話題包括同性戀、紅燈區、釣魚島等。“勺見”的主辦者之一宋雙說:“我們都比較強調價值無涉,沒有特別強烈的感覺要讓別人認可我們自己的東西。”同樣的價值中立的傾向也出現在南京大學的“先鋒論壇”和廈門大學的“碧山公共空間”等平臺中。
在這些平臺所舉辦的活動中,雖然由于嘉賓的引導或者提問者的發言,也不時出現與政治相關的討論,但往往流于參與者對相關話題的各自表態,討論難以深入而鮮有創造性觀點的提出。
周雨霏和鄔方榮都承認,青年沙龍的中立表現某種程度上也出于規避政治風險的考慮,但他們都并未將這一點列為主要原因。除了“勺見”原定在2012年11月1日舉辦的討論會與許多計劃在“十八大”前夕舉辦的校園活動一樣被校方要求取消以外,“勺見”和“706青年空間”的活動都不曾受到來自官方的干預。然而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諶洪果的遭遇則完全不同,諶洪果原定在2012年11月24日進行的“學術與政治”讀書會被學校勒令停辦,準備在讀書會上發言的學生還遭到校方的約談和警告。
許知遠認為,當代青年沙龍的價值中立是一種值得憂慮的現象:“現在這代人表面反抗,但其實內心是匱乏的,因為沒有一個對世界的基本判斷。看著很多元、很瑣碎,其實又挺沉悶的,因為談任何事物如果沒有深度的話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個人的感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