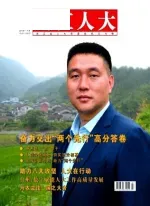治堵決策的迷途與正軌
/阿 計
北京計劃征收交通擁堵費!首都官方近期宣布的這一動議,猶如投石入湖,激起一片民意喧嘩的聲浪。近些年,在人們對多個城市治堵措施的“討伐”中,我們不難發現,治堵,已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管理議題,也成了考察公共政策民主性、公正性的政治窗口。
北京實行汽車搖號限購后,中簽比例不斷走低。

限制的升級
2013年9月2日,北京市環保局發布了清潔空氣行動計劃(2013—2017年)重點任務分解措施,在有關治理擁堵和尾氣污染的一系列政策設想中,最具震動效應的信號是,有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征收交通擁堵費政策,并適時出臺。
此前的8月末,新版《上海市交通發展白皮書》已將征收交通擁堵費首次列為政策儲備。再往前追溯,深圳于2007年在國內率先醞釀過征收交通擁堵費,其后,廣州、杭州、南京等地都曾釋放過類似風聲,但因分歧巨大、抵制甚眾,最終不了了之。比較而言,北京經過數年試探后,此次已列出了相對明確的時間表,很可能成為第一個破冰者。而作為具有風向標意義的首都,北京又對其他城市具有強烈的示范作用,由此引發全國性的關注和爭議,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實,交通擁堵費對中國而言是一個舶來品。1975年,新加坡率先推行了這一治堵政策,其后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先后跟進。不過,這些城市都是在各種治堵措施幾乎用盡而又無法緩解擁堵的情形下,才采取了這一極端手段。如今,交通擁堵費在中國已經箭在弦上,是否意味著治堵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呢?
最近10多年來,我國以超常速度快速步入了汽車時代,截至2012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2.4億輛,北京更是在短短兩年內就從400萬輛猛增至500多萬輛。與此同時,許多城市日益陷入“堵城”的困境,在私家車保有量排名前四位的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高峰期全城皆堵已成常態。此外,因汽車尾氣排放這一主導因素,目前全國約有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氣污染嚴重。有測算表明,因交通擁堵等問題,我國15座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財富。因汽車時代而帶來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已成為城市管理必須解決的頑疾。
在此背景下,各地開始為治堵而頻頻發力,從限行到限號,從限牌到限停……各種以“限制”為特征的行政、經濟調控手段連綿不斷、持續升級,幾成一“限”到底的態勢。對公眾而言,購買、使用汽車的自由日益受到限制,成本變得越來越高。
以北京為例,自2011年實行搖號限購以來,中簽比例不斷走低,到今年9月已跌至1∶87,購車成了“搖號難,難以上青天”的撞大運。隨著北京明確到2017年年底將機動車數量控制在600萬輛,未來車輛指標配額將進一步削減,據測算中簽比將下降為至少1∶132,即132個人去搖號,只有1個人能中簽。
在實行“車牌拍賣”的上海,今年上半年平均中標價已達8萬元,以至出現了“牌比車貴”的奇特現象。在廣州、貴陽、石家莊等城市,各種不同版本的限購措施,也令消費者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而這股“限購政策潮”依然以不可阻擋之勢蔓延,據預測到2015年前后,全國最擁堵的25個城市都將套上限購的枷鎖。
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在推出如此之多的治堵措施后,多數城市并未擺脫擁堵之困,一些限制政策雖收一時之效,但很快便呈衰減效應,以至故態復萌甚至擁堵加劇。仍以北京為例,雖然近年來接連推出尾號限行、搖號限購、停車費漲價、限制外地車進城等手段,但今年上半年擁堵指數卻比去年同期增長6.4%,工作日路網平均擁堵時間已高達100分鐘,比去年整整增加了30分鐘,北京人自嘲的“首堵”,絲毫看不到緩解的跡象。
正因此,征收交通擁堵費會不會重蹈“只收錢不治堵”的覆轍,不能不令人生疑。而在質疑必要性之外,更需反思的是各種以“限制”為特征的治堵政策的正當性,追問其是否真正體現了正義的價值,即制訂程序是否民主,實質內容是否公正。
民主的缺席
諸如限行、征收交通擁堵費之類的治堵政策,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公民的出行不便,或限制了公民財產權的使用,可謂與公民的切身利益、自由權利息息相關,因而其決策理應征詢民意、進行聽證等等,必要時還須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批。然而現實中的不少治堵政策,缺失的恰恰是程序的正義和民主。典型的例證是,北京于奧運會后實行的尾號限行,便是以一紙簡單的行政命令推出,且年復一年地延長有效期,而由此引發的“是否侵犯公民物權”等爭議,亦經久未息。
相形之下,許多國家推行的涉及公民權利的治堵政策,大多經過聽取公眾意見、提請議會批準等程序。其中的一個樣板是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2006年,斯德哥爾摩提出了征收交通擁堵費的設想,一開始遭到市民的強烈反對,為此,當地政府在加速改善公共交通的同時,設置了7個月的收費試行期。試行期間,該市市中心交通流量減少了20%,空氣質量明顯好轉,由此,市民們再也無法忍受回到擁堵的日子,紛紛由擁堵費的抱怨者轉為支持者。盡管社會共識已經基本達成,但當地政府并未借勢獨斷行事,而是依然一絲不茍地執行民主程序。2006年9月,斯德哥爾摩通過市民公決這一最直接的民主方式批準了收取交通擁堵費的提議,次年6月,該市議會正式通過了這一決策。也正因為公共政策同時確立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斯德哥爾摩成為世界上征收交通擁堵費最成功的城市。
從表面看,我國一些城市推出各種限制性的治堵方案時,也啟動了征集民意等民主機制,然而,公眾提出的如潮意見,常常無法影響最終決策,甚至得不到官方的合理解釋和反饋。更多時候,人們看到的是一些專家為官方意志站臺和背書,征集民意蛻變成了政府單方聲音的表達。
就此次征收交通擁堵費的動議,北京市有關部門也已表示,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這一承諾無疑是值得歡迎的,但真正的憂慮和挑戰是,決策民主能否落實兌現而非流于形式。比如,交通擁堵費如何征收?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在公共交通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推出這一極端手段是否時機恰當?將大量車主“趕”到公交系統,是否可能令其更加不堪重負?這些都是公眾極為關心的問題,既需要深入論證和公共討論,也需要政府承擔起應盡的說明和解釋義務。尤其是,征收交通擁堵費直接涉及公民財產、收費等問題,因而召開聽證會、甚至提請人大議決都是其不應繞開的門檻,但這些民主程序能否得到尊重,目前還是未知數。
治堵政策的復雜性還在于,它不僅涉及公共治理與公民權利之間的矛盾糾結,也關乎有車族、無車族、黨政官員、普通市民等各種不同群體的訴求沖突,因而與此相關的政策選擇,并非簡單比較人數多寡、聲音高低,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尋找到最具協調性的治堵方案,這也是程序民主的真正價值所在。
公正的失衡
除了程序民主,治堵政策面臨的另一個拷問是:如何才能不偏離公正的軌道?
回溯歷史,為了扶持汽車工業、拉動內需,政策導向曾長期鼓勵汽車消費,然而當擁堵、污染等諸多城市病爆發后,政策制訂者又面臨必須加以控制的壓力,進退失據之際,犧牲的往往就是公眾權益。但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讓公眾為缺乏預見的政策失誤買單,是否有違政府誠信、顯失公平?
而在具體治堵思路上,限制公民汽車消費自由和權利的招數只能收一時之效,改善基礎路網、發展公共交通等等才是根本出路,但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財力,遠不如前者來得簡易快捷。于是,頻頻登場的便是各種限制政策,總在公眾身上打主意幾乎成為一種本能的沖動,政府的應盡職責卻往往輕描淡寫、躲躲閃閃。人們疑慮,在政府義務尚未履行窮盡的情形下,將治堵責任過多推到車主身上,是否有推諉卸責之嫌?甚至滋長“只知限制和收費,不思改進”的懶政思維慣性?而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平感,也成為民意焦慮甚至官民對立的重要癥結所在。
公眾質疑的另一個焦點是,拍賣車牌照、提高停車費等經濟手段,是否建立了公開透明的資金流向監督機制,保證其投入公共交通,而非中飽管理單位的腰包,或變異為政府“創收”的捷徑。
北京大幅度提高中心城區停車費后,車主動輒就要支付數十元的停車費,但在停車成本急劇增加后,交通擁堵并未根本緩解,停車難與停車貴反而產生了疊加效應。更令車主們反感的是,多收的停車費的數額、流向等等,并無公開透明的知情渠道,仿佛成了一筆糊涂賬,有些還淪落為物業等管理單位的斂財之道。
也正因此,不少人對此次北京擬征收的交通擁堵費,最終能否“專款專用”,用于直接改善公共交通,并無多大信心,反而擔憂其可能蛻變成政府的新財源。相形之下,在已經征收交通擁堵費的國家和地區,無不建立了保障公眾知情、監督的暢通機制,這也是獲得民意支持和社會認同的重要基礎。
尤其是,一些抬高購車、用車成本的治堵措施,往往潛藏著制造社會不公平的風險。
以車牌拍賣這一限購政策為例,富裕階層在政策實施前往往早已購置了汽車,政策實施后的增量消費人群,大多是收入一般的普通階層,他們通常居住在房價較低但公交系統欠發達的郊區,汽車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但如今,他們不僅需要節衣縮食攢夠購車資金,還必須支付高昂的牌照費,這樣的政策效果,很難稱得上符合社會公平。
至于交通擁堵費,更是存在著難以解釋的內在悖論。作為一種價格杠桿,交通擁堵費只能對價格敏感者產生導向作用,迫使其調整出行方式。但不難設想,富人對這點“小錢”根本不在乎,公車用公款買單絲毫不心疼,因而交通擁堵費對兩者的限制作用幾可忽略不計,真正擋住的只是大批工薪階層有車族的車輪,剝奪的只是弱勢群體改善出行質量的權利、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其結果就是,由全體納稅人出資建設的公共道路資源,很可能變成被官員、富人買斷的“專用道路”,進而人為擴大路權不公平和交通權益的貧富不平等,甚至使交通擁堵費淪為一項“欺負窮人的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治堵政策之所以引發強烈的質疑和抵制,并非這些政策真的如此糟糕,而是投射了人們對行政專斷、特權交通等等的不滿情緒。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要解決交通之堵,必先排遣人心之堵,而要實現既暢交通、又疏人心的目標,就必須堅守兩個基本的出發點——民主與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