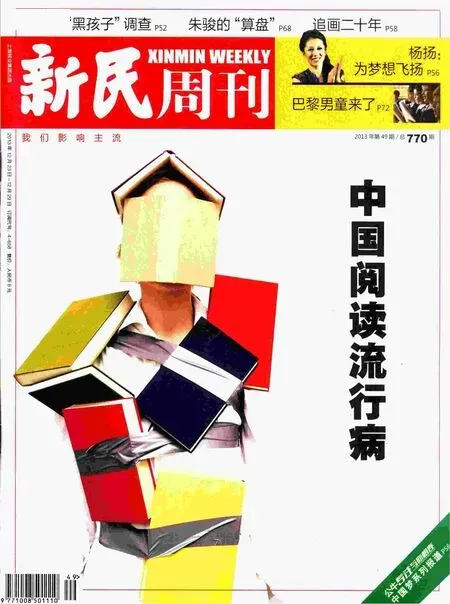鳥與世界
姚謙
在剛剛認識戴子越時,他已是一位典型的資深驢友,而且他偏重于較荒蠻非旅客常去的地方,以最簡單的裝備和自身的體力去完成一段行走。這樣的旅行對個性低調的他來說幾乎是唯一的愛好。在我看來觀鳥的心態與這樣的徒步旅行是有一定的相近頻率的。他不這么認為,因為他從驢友變成觀鳥者是因為一個小故事引起的。
十年前我與他經朋友介紹而認識。當時我決定另安一個家于北京,對于裝修要求,在見過了幾個設計師后,只有戴先生能聽明白我的意思,讓我有種知音難得之感。戴先生不愛說話、比較沉默,我們平常也比較少交流。記得有一年,他忽然邀請我去河北省一塊沼澤地觀鳥,那時我才知道他多了觀鳥的愛好,以為那是旅行外加的節目,可惜那次邀約我沒有成行。上回因為改客廳音響線路我們又見面了,完工后聊天他跟我提起十一假期他會去江浙的海岸線,觀察猛禽的遷徙。
聽他說起近來觀鳥,那個初秋的下午,忽然都平靜了起來。對于長年觀鳥的人來說,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可以遇到哪些鳥群,是一件那么生動的事。當他說著十一假期正好是從俄羅斯往南飛的猛禽們路經那里時,我忽然想起不久前在飛機上看的一部以色列電影:一位中年鳥類學家架起一個觀鳥網站,報道從俄羅斯出發一路向南的鳥群,中途將經過他的家鄉——以色列。許久未見他的小兒子,為了能與父親相遇,把握住機會發動了同學,計劃在鳥群預計經過的路上,準備好適合鳥類短暫休息的環境。果然鳥群來了,孩子也與父親見面了。雖然最終父親還是要跟著鳥群離開,往南到非洲,但是也承諾了回程相聚。我問戴先生這些鳥也往非洲飛嗎?他說:是。
對他來說,旅游與觀鳥最大的差別是:旅游有較多的觀察是帶著獵奇與征服,而觀鳥則帶著較多的理解與尊重之意。甚至在觀鳥的族群中,還分兩派,有人帶著全套的攝影器材,在千辛萬苦跋涉后的等候與尋找中,拍攝記錄。而戴先生屬于另一群人,除了行走攀巖的工具以外,盡量什么都不帶,只因為在與鳥群們相遇時,他可以更專注地享受短短的交會時光,留在心里。記得他曾是一位攝影愛好者,這樣的轉變我想是一次精神上的凈化吧。
我問起了他萌生觀鳥的典故。他告訴我他的辦公室是在一個老院子里,有一回同事從花鳥市場買了一對小鳥掛在院子里欣賞,沒想到才掛不到半天,一不注意其中一只鳥就莫名其妙地死了,而且死狀奇慘沒有了頭,應該是活生生地被籠外兇猛動物硬扭斷叨走的。他與同事非常震驚,于是決定躲樹后觀察,不一會兒,發現了一只比麻雀大不了多少的小鳥盤旋出現,并且用非常快的速度飛向鳥籠,咬住幸活的那一只,并且非常有氣力地企圖將它抓走,這真是令人吃驚的畫面。到底是什么樣的鳥,看似嬌小卻有如此猛烈的性情以及力量呢?他隔天設了一個局:把鳥籠打開,又放了另外一只鳥當誘餌引鳥入室,果然兇猛的小鳥又出現了,這次它掉入了陷阱之中,戴先生與同事捕獲了這只小鳥仔細觀察后,決定回到花鳥市場詢問鳥販。他了解到這鳥叫做虎布拉子,長得一般、個性兇猛,北京到處可見,并不稀奇且食量大沒人愿意飼養,不久他們就決定把這只鳥放走了。不過對于虎布拉子他心中充滿了好奇,上網搜尋才知道虎布拉子就是“伯勞鳥”,甚至在春秋古籍就早已提過伯勞,原來這種鳥早已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其中“勞燕分飛”說的就是看似相似的兩個人,因為本性差異太大,最終還是無法在一起。勞與燕指的就是伯勞與燕子,體型相近生性卻差異頗大。越閱讀越是對鳥類有更多的好奇。過往在旅途中經常能遇到一些他叫不出名字、也完全不了解的鳥群,相遇了也錯過了。從此他決定在他的旅行中,把觀鳥當作另一種認識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方式。不同的鳥、不同的習性和不同的遷移途徑,都跟這世界絕對有密切的關系,可以客觀地對照與認識自己生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