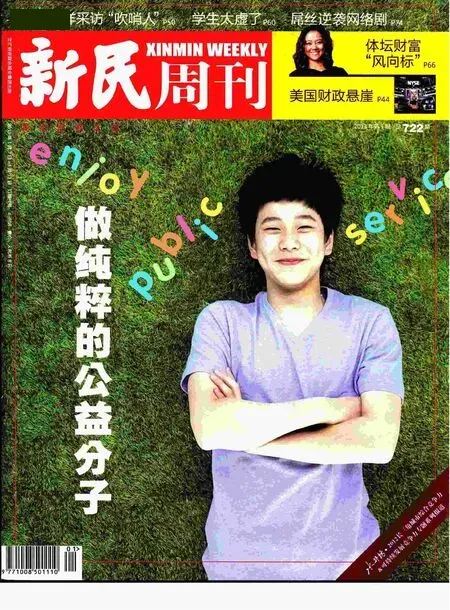越洋采訪“吹哨人”
金姬



人們似乎很容易記住某個令銀行倒閉的魔鬼交易員(例如終結英國巴林銀行的尼克·里森),而總是忘了拯救一家銀行或者挽回客戶損失的金融英雄的名字。
在金融界,及時止損和修正錯誤是保持屹立不倒的金科玉律,而很多上市公司為了賬面漂亮往往選擇掩耳盜鈴,直接的結果是敢于說真話的職員在公司被邊緣化甚至在業界混不下去,最后不得不以匿名方式向有關機構舉報。很諷刺,不是嗎?
好消息是,美國的金融英雄們已經有了制度保障。經過2008年的危機洗禮,美國SEC(證券交易委員會)自2010年8月開始與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以及國內收入署(IRS)共同實施“吹哨人項目” (Whistleblower Program,“吹哨”在美國俚語中意為“告密”),鼓勵更多人舉報自己公司的不當行為,甚至拿出罰金的一部分作為回報。
利益誘惑雖然讓更多人成為“吹哨人”(SEC平均每個工作日接到8起舉報),但沒有人愿意實名舉報。直到2012年12月6日,以色列出生的艾里克·本-阿奇(Eric Ben-Artzi)博士,成為“吹哨人項目”實施17個月以來第一位實名舉報者。他宣稱“老東家”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在2007年到2010年掩蓋了某款金融衍生品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本-阿奇博士在電話里告訴《新民周刊》:“公開身份是一項非常艱難的決定,但我做了正確的事。我有十分確鑿的證據支持我的說法。”
華爾街“異類”
如今的本-阿奇博士已經失業一年多了,靠此前的存款生活。在2011年11月7日那個周一之前,他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這名出生在以色列的70后于1992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獲得數學學士學位,然后在以色列海軍服役了4年。1997年,本-阿奇憑借自己的數學才能在摩根大通固定收益衍生品部門找到一份工作,自那以后一直在紐約生活。一年后,他開始在紐約大學主攻金融數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
2006年,他結婚了。為了讓家人生活得更好,他又回到華爾街,成為高盛的一名定量分析師。雖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逃過一劫,但本-阿奇博士考慮找一家“非美國”公司“長期工作”,而且還要用自己的數學知識避免下一場危機——測試復雜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和抗壓能力。于是,他2010年6月進入德意志銀行出任法律、風險和資本部門的副總裁,辦公室仍在華爾街。
德意志銀行歷史上曾是德國工業最為重要的“錢莊”,如今已深入涉足全球投行業務。本-阿奇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詢問同事如何計算德意志銀行金融衍生品的差額期權,但是沒有人的答案令他滿意。2011年初,他發現德意志銀行在2007年到2010年期間用普通高級證券的方式來估值杠桿超高級(LSS)投資組合的差額期權價值(LSS買方所支付的擔保金與LSS賣方同意支付的按市值計價預期損失之間的差額),這可能意味著德意志銀行的賬面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掩蓋了48億和29億美元的損失。要知道,德意志銀行是市場上最大的LSS持有者,這些投資組合產品的名義價值高達1200億-1300億美元。也許,在2008年金融危機最為嚴峻的時期,德意志銀行距離破產邊緣并不像人們此前認為得那么遠。
發現這個驚天秘密后,本-阿奇帶著懷孕的妻子回耶路撒冷休假。他當時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告訴父母和妻子自己所處的困境:如果上報德意志銀行欺詐,他很可能丟了金飯碗,妻兒的生活今后難以保障。
家人支持他站在正義的一邊。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告密者。一開始我曾根據銀行政策和程序在內部進行過大范圍的報告。但是這個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和糾正,我不得不告知相關的執法部門。”2011年3月,本-阿奇撥通了SEC的舉報熱線,并告知了德意志銀行。
這種書呆子式的意氣用事,在本-阿奇博士的代理律師喬丹·托馬斯(Jordan A.Thomas)看來也是個特例。他在電話里對《新民周刊》表示:“很少有人會告訴自己的公司‘我舉報你了。而且,大多數舉報者都選擇匿名方式,以防打擊報復,或是怕自己上了業界黑名單而無法在這一行立足。但本-阿奇博士態度很堅決,他堅持認為德意志銀行應該明白發生了什么。他一開始通過公司內部渠道說明此事,而銀行方面卻故意忽視他的報告,也不愿修正自己的錯誤。我認為本-阿奇博士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責任感。”
舉報的代價
本-阿奇博士沒有想到的是,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在德意志銀行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辦公室里充滿敵意,自己被大家孤立,他無法獲取工作必需的材料。2011年6月底,他開始休假。在他離開的那段日子,德意志銀行重組了他的部門,他不得不考慮在德意志銀行內部尋找其他職位。當發現自己很難在德意志銀行立足以后,剛剛成為爸爸的本-阿奇博士擔心自己無法養家糊口。他從彭博社的新聞中看到了希望。
2011年7月,為美國聯邦政府工作16年的喬丹·托馬斯離開SEC執行部助理總監的職位、加入紐約Labaton Sucharow律所,主管“吹哨人項目”的舉報人代理業務,引發媒體爭相報道。他的辦公室距離德意志銀行的辦公室只有300米。托馬斯告訴《新民周刊》:“當本-阿奇博士首次找我咨詢的時候,我被德意志銀行的這一違規行為的規模和范圍震驚了。這正是SEC‘吹哨人項目要解決的重大未上報證券違規類型。但我們律所接案子很謹慎,一般都會做一些前期調查。我們發現他說的可信度很高,因此就正式代理了這個案子。之后我們又做了更多調查,結果都和他之前所說的一致。”
2011年10月,休假后的本-阿奇博士回到了辦公室。11月7日,他突然被公司人力資源部叫去參加視頻會議,德意志銀行法蘭克福總部告訴他,原來的工作職位被重新安排到柏林了,這意味著他被解雇了。而這距離本-阿奇博士向SEC正式舉報德意志銀行僅僅過了3天。
本-阿奇博士向《新民周刊》透露,德意志銀行的這種行為,促使他決心公開自己的舉報身份。“我花了好幾個月在實名還是匿名舉報之間徘徊,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我而言,守住一個秘密太難了。除了失業,我付出的代價就是有一段時間不和朋友聯系,自我孤立,不能過正常的社交生活。我的鄰居也是搞金融的,我不得不盡量避免和他們接觸,最終我選擇了搬家。”
一年多來,本-阿奇博士發現自己的“英雄舉動”并沒有給他帶來鮮花和掌聲。“華爾街是一個小圈子,各大金融機構之間的HR都有聯系。大多數雇主不喜歡我這樣向SEC舉報的雇員,但我希望會有雇主認同我的做法。”
至于SEC何時結束對德意志銀行的調查,這還很難說。托馬斯表示,SEC通常要花上2-4年去結案,大約61%的案件會在2年內結束。“本-阿奇博士的案子更復雜,持續更久一些也在所難免。他最早是2011年3月舉報的,現在SEC也調查了22個月了,最樂觀估計是2013年會有初步結果。但我認為很可能還要更久。”
爭議“吹哨人項目”
本-阿奇博士強調自己握有德意志銀行違規的證據,但他現在不方便向媒體透露。“我已經全部交給SEC了,所以他們才會啟動全面調查。我不是德意志銀行第一個發現這個問題的人。”
事實上,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還有另兩人匿名舉報德意志銀行。根據《明鏡》的報道,2010年春天,也就是在本-阿奇博士加入德意志銀行前,一個名叫馬修·辛普森(Matthew Simpson)的雇員告訴上司LSS估值有問題。德意志銀行聘請了一家名叫Fried Frank的律所進行了內部調查,并沒有發現辛普森所說的問題,并把此事通報了SEC。后來又有一名德意志員工向SEC匿名舉報了此事。“這在SEC歷史上很不尋常,3個人來自同一家公司,分別舉報自己的東家。”這讓律師托馬斯堅定本-阿奇博士說的是實話。
但也有不少人質疑本-阿奇博士的舉報動機。因為“吹哨人項目”的獎金十分誘人——如果個人向SEC提供的情報導致100萬美元以上罰款,舉報者能獲得罰金中的10%-30%作為獎勵。根據SEC“吹哨人項目”2012財年(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報告,截至2012年9月末,“吹哨人項目”的獎池已累計達到4.53億美元。SEC在2012財年共收到3003次舉報。
“吹哨人”在美國早已有之,但以前的“吹哨行為”不會獲得巨額獎金,動機完全出于“社會責任感和道義”,舉報范圍也不僅僅局限于金融犯罪,還涉及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公共健康等諸多方面。2010年7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設立了“吹哨人項目”,為正當的檢舉者提供強大的就業保護、金錢獎勵以及匿名舉報的便利。
本-阿奇博士再三對《新民周刊》強調:“我選擇舉報并不是看重SEC可能提供的獎金,否則也不會公開身份了。”
當然,舉報者拿到獎金并非易事。除了“帶來100萬美元以上的罰款”的這一眾所周知的必備條件外,SEC還規定,“吹哨人”只能是自愿向SEC提供原始情報的個人,公司或組織不在獎勵范圍之內;其次,舉報信息也必須是“原始”的,既可以是個人所知的事實,也可以是基于公開資料的獨家分析,但這些舉報信息都必須能為 SEC展開調查提供一條新的線索才行。難怪直到2012年8月才出現了第一位獲獎的“吹哨人”——公開信息顯示,此人提供的文件和情報協助了SEC對某個欺詐案的調查,并最終導致法院對被告作出罰處超過100萬美元的裁決,他能獲得其中的30%。
本-阿奇的律師托馬斯當初在SEC工作時參與了“吹哨人項目”的制定工作。他在2011年末帶領律所團隊開展的調研結果顯示,超過3/4的美國人和94%的外國人愿意向SEC告發美國上市公司的不法行為,不過他們只有在匿名、不用擔心報復的情況下才會告密,而且很多人都看重那筆獎金。“這是SEC歷史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愿意站出來舉報。自從2010年8月啟動‘吹哨人項目以來,我代理過很多舉報者,他們大多數是大型金融機構的高管,也有外國人。外國人舉報的大多是賄賂和金融欺詐,這是兩類最常見的案子。”托馬斯告訴《新民周刊》,但在美國公司工作的員工只有34%知道“吹哨人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向SEC舉報的老外“吹哨人”最多來自印度、英國和中國。對于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而言,這也許能夠部分解釋2012年12月SEC對中國包括“四大”在內的五家會計師事務所發起行政訴訟,原因是它們未能提交與其審計的中國公司相關的工作文件,協助其調查——在可能的巨額獎金誘惑下,中國“吹哨人”頻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金融市場瞬息萬變,風險無處不在,單靠監管部門的力量很難全面防御復雜龐大的金融風險,發動市場的力量來消化一部分風險似乎是一個明智之舉。中國市場是否也能引進類似的“吹哨人項目”?
對此,中國證監會相關人士表示,目前證監會的行政性罰款是收支兩條線,收入統一進中央財政,證監會沒有動用的權力。不過,如果可以將證券市場的罰款充實到投資者保護基金里,再從中撥出一部分用作對舉報者的獎勵也未嘗不可。
實際上,目前證監會大部分違規線索來自交易所的日常監控,其次才是舉報和新聞報道。證監會相關人士表示,即使這樣工作量已經非常大了,所以當務之急是擴充人手,而類似“吹哨”的機制,暫時還不在推動的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