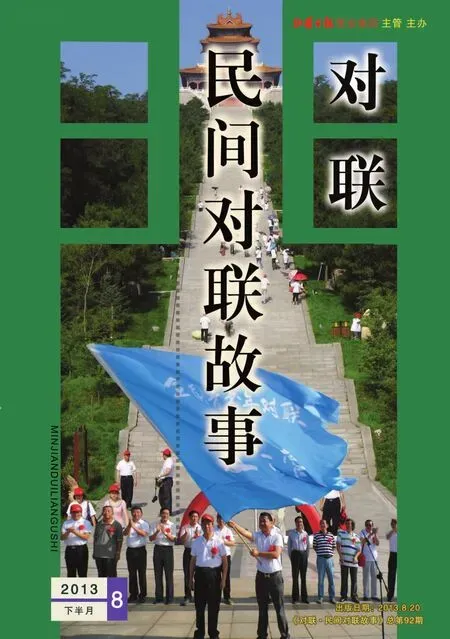中國楹聯學概論(連載七)
□谷向陽 著

春聯始于五代,昔人似乎多無異議。新時期以來,聯界專家倡起楹聯產生更早之說,隨著史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其產生的年代一次次地提前。
第二節 楹聯的雛形
對聯文字何時走上了桃符板?清代楹聯“聯話”開山之作的作者梁章鉅(1755-1849),在《楹聯叢話》首卷即開宗明義地指出:
嘗聞紀文達(即紀昀)師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慶”“長春”一聯最古。按《蜀梼杌》云: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于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后蜀平,朝廷以呂余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節名也。此在當時為語讖,實后來楹帖之權輿。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孟昶(919—965),為蜀開國國君孟知祥第三子,在位三十年,每年除夕都要更換桃符,開始只題“元亨利貞”四字。他為太子時曾自題策勛府桃符“天重余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則記為“天隆余慶,圣祚長春”,賜子孟喆“置于寢門之左右”。
梁章鉅認為孟昶的五言聯“最古”,是我國第一副春聯,對后世產生很大的影響。
新年納余慶;
嘉節號長春。
這副春聯首尾二字連起來是“新春”,上下聯首二字分別是“新年”、“嘉節”,有很強烈的節日氣氛。但這并非因聯語驚人而流傳至今被視為“楹聯之始”,而是此聯特殊,特殊到成為亡國之兆的“讖語”:孟昶題聯不久,陳橋兵變,趙匡胤龍袍加身,江山易主,后蜀國君成了大宋的俘虜。宋太祖派去接管成都的一位姓呂的官員,恰好名字叫“余慶”,而孟昶降宋之日,又正值宋太祖誕辰的“長春”嘉節。這種天衣無縫的巧合加之迷信的附和,便成為聯史佳話,而作為題聯者的孟昶,只能用“不幸而言中”來說明他在文化史上的尷尬了。這副有史記載的第一副春聯,只是作為帝王的軼事而被記錄下來,并非是對楹聯來龍去脈的探討。
一、最早的口語聯
春聯始于五代,昔人似乎多無異議。新時期以來,聯界專家倡起楹聯產生更早之說,隨著史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其產生的年代一次次地提前。
《后漢書·孔融傳》記載:
(融)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日:“座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既而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后漢書》為南朝宋史學家范曄(398—455)所撰,同時期的南朝宋文學家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中也載: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商務印書館1921年版《中國人名大辭典》所載孔融詞條中亦記有“嘗自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這副經常吟誦的聯句,當是有意為對,非無意識的偶合,有楹聯的特征,成為我國第一副口語聯。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對聯產生于東漢。如此說,產生于公元200年左右的這副楹聯要比孟昶聯(公元964年)早750多年。
漢代末年,已具備楹聯產生的基本條件。孔融生活的建安時期,正是中國五言詩的旺盛時代。當時的五言詩,既能方便地容納雙音詞,也可以容納單音詞,以至三言詞,它的二、三結構,即三字尾,在一句詩的拍節上,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變化而不單調。孔融能詩,與王粲等文學家齊名。他的聯句正體現了這時期五言詩的特點,并與楹聯的特征基本相一致。當然,孔融的聯句并未引起當時文學家們的注意和效仿,也就是說楹聯在那時未能引入文壇,卻被史籍記錄下來。
二、最早的人名聯
漢末魏晉,排比對偶的手法在辭賦中得到了自覺廣泛的運用,并且有了明顯的駢化跡象。待至晉初,完全用駢偶寫的賦也已經出現。陸機的《文賦》是文學理論長篇,是用詩一樣的文字寫成的,很講究對偶和音韻。在《文賦》中,陸機明確地提倡音韻的協調,“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越來越引起作家們的注意和重視,這為音律的完善和格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晉太康之初,當時天下統一,呈太平氣象,詩壇十分活躍,詩人們把五言詩鍛煉得更加得心應手。晉代文人中,崇尚清淡、崇尚辯論已成風氣,應對常常成為清談內容之一。陸云(262—303)與其兄陸機同是西晉文學家,出身江南世族家庭,為吳郡吳縣華亭 (今上海市松江)人。吳亡后陸機、陸云同至洛陽,名動一時,時稱“二陸”。這期間,就有陸云(字士龍)與太子舍人荀隱(字鳴鶴,潁川人)在文友張華家以應對為清談的記載。《晉書·列傳第二十四·陸云》載:
“云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云因抗手曰:‘云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
《世說新語·排調》也記錄了此事: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張華)坐。張令共語,以其并有天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云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文學家劉義慶撰寫的古小說集,書中所記多為漢末尤其魏晉間文人名士遺聞軼事、清談實錄。
云間陸士龍;
日下荀鳴鶴。
是在“勿作常語”的要求下產生的一副藝術性較高的應答妙對。華亭古名“云間”、“日下”指京都。荀隱潁川人,與洛陽相近,故云“日下”。“日下”對“云間”是地名相對,“荀鳴鶴”對“陸士龍”是人名相對。上下聯不僅對偶工整,在聲律上也表現出異聲相襯,低昂相對之妙。每句之內都是平仄相間,兩句之間又恰好平仄相對,這正是一副合格的楹聯。這種規律當時只有少數文人了解,還沒有作為一種文體走向社會。此聯不僅合律,而且諧音雙關,內含著“云天之間鹿是(陸士)龍,化日之下尋(荀)鳴鶴”的寓意。應當把此聯看做我國最早的人名對。
常江先生對于楹聯探源用力甚勤,多有開拓。他以陸云、荀鳴鶴的對句論證了對聯產生于晉。他又在晉人裴啟所撰的《裴啟語林》中發現了晉人的四副對聯。
青羊將二羔;
兩豬共一槽。
(劉寶與一嫗應對)
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爾;
俊士填溝壑,余波及來人。
(潘岳與石崇應對)
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蕭芳艾榮。(毛伯成)
張屋下陳尸;
袁道上行殯。
以上四聯又為晉代的楹聯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以上四副聯對仗雖欠工,平仄也欠協調,遜色于前聯,但從特點上看它們的確是楹聯,以今天標準衡量,當以“寬對”視之。
三、最早的門聯
駢體文最基本最主要特點就是駢偶。駢偶就是句式結構平行、對稱,詞語相互對偶,又稱對仗。對仗原是古代帝王出行時,走在最前面的兩兩平行、相對排列的儀仗隊。這種對偶或對仗,是適應我國語言單音詞較多、字易構成配對的現象而產生的修辭手法。這種手法起源于對事物的聯想,可以使事類相從,正如日本青木正兒所云:“當胸里還殘留著上句的印象的時候,后讀的下句各自的印象又重疊上去而調和。”而且可以取得語句上整齊和對稱之美。所謂句式結構平行、對稱,即主語對主語、謂語對謂語、賓語對賓語等;所謂詞語相互對偶,是指詞性也要對稱,如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虛詞對虛詞等。當時的文人并沒有這方面的術語,但實際上又是這樣做的。關于語言對偶中涉及的詞義方面的所謂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等,在劉勰的《文心雕龍·麗辭》中,都做了理論上的解說和例述。
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出現的嚴格遵守“四聲”、“八病”之說、講求聲韻格律的“永明體”,不僅促進了比較自由的“古體詩”向著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發展,為唐代格律詩和楹聯的成熟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礎,而且促進了其他文體,如辭賦、駢文等更加聲律化、駢麗化,甚至對后來的詞、曲等都有很大的影響。“永明體”的主要創造者沈約,在詩律學上不僅創“四聲八病”之說,而且對詩歌聲律結構更有創見。沈約對詩律的要求和安排,是以五言詩的一聯兩句為單位的,即在一句之內平仄相間;兩句之內,平仄相對。把輕重音即平仄聲在一句中交叉搭配,在兩句中相對應出現,這樣“永明體”格律主要出現下面兩種律聯形式: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和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現以詩兩句對仗為例。如:
微風搖紫葉, (平平平仄仄)
輕露拂朱房。 (平仄仄平平)
輕字應仄而用了平聲(用平或—示。下同)。
沈約《詠芙蓉》:
落日高城上, (仄仄平平仄)
余光入繐帷。 (平平仄仄平)
以上的對句做到了“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五言一句之內,平仄相間,上下兩句之中,平仄相對。
這時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應是劉孝綽兄妹所作的門聯。劉孝綽,人稱“神童”,為當世名流沈約、王融、任昉等所賞識,官至秘書監,頗為蕭統所重。因其恃才傲物,與世乖忤,五次被免職,罷官歸隱。清學者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記.學編七十四》載:
考宋(應為梁)劉孝綽罷官不出,自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其三妹令嫻續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復生。”此雖是詩,而語皆駢麗,又題于門,自為聯語之權輿矣。
這兩副聯都是出自五言詩中,單獨題于門,起到了楹聯的獨特作用,應看做我國最早的門聯。
閉門罷慶吊;
高臥謝公卿。
落花掃仍合;
叢蘭摘復生。
這兩聯較漢、晉出現的聯語顯然成熟多了,在對仗工整而又靈活的前提下,注重了意境的營造,給讀者留下了體味意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