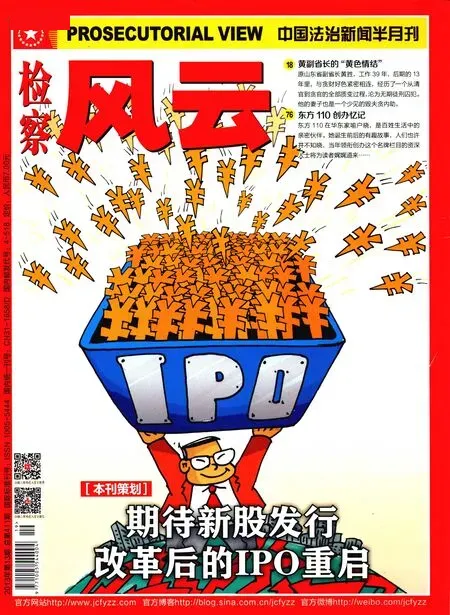西方兒童福利的百年架構
文/張鴻巍
西方兒童福利的百年架構
Child Welfare in Transition: Through Western Eyes
文/張鴻巍

“我們都曾經是兒童,我們都希望孩子們幸福,這一直是并將繼續是人類最普遍珍視的愿望。”在聯合國網站上,這句話被置于兒童議題的顯著位置。
6月總是多姿多彩的,不僅是節氣的關系,還有月首的特殊意義——國際兒童節,這個屬于所有兒童的日子點亮了6月,也讓我們重拾兒童福利的議題。
在審議復雜多樣的全球挑戰時,國際社會決不能放松對兒童問題的關注。未來社會的品質和繁榮取決于當今兒童權利的實現程度。
——聯合國《關于兒童問題的大會特別會議的后續行動》
1959年,聯合國在《兒童權利宣言》中顯露了“兒童福利”定義的雛形,“凡以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與正常生活為目的的各種努力事業,均稱之為兒童福利”。1990年,美國兒童福利聯盟則更為強調地指出,“兒童福利是社會福利的一環,是以全體兒童及青少年為對象,提供在家庭中或其他社會機構所無法滿足需求的一種福利服務”。
翹首之中仿佛等待了千百年之久,才依稀窺見兒童福利的端倪。
西方兒童福利觀念演變
西方兒童福利思想伴隨國家親權、父母監護以及兒童權利三者間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而得以衍化,從“最少介入”到“國家干預”,以至逐步回歸“家長責任”,這一切的嬗變無不昭示著兒童福利政策演進過程的博弈與掙扎。
17至18世紀,英國一系列的社會變遷與司法改革吹響了對兒童人權認知的號角,為后世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對與英國法律一脈相承的美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時期《濟貧法》的出臺及學徒訓練制度的實行,不但促使法官在處理兒童案件時一改往日拖沓的作風,而且對照管不良兒童與失依少年的處理上更具現實操作性,為其指定法定監護人,以便進行實質上的教化與保育。這被認為是解決兒童問題的靈丹妙藥,不但此后盛行于英倫三島長達二百年之久,亦為北美殖民地所應用。
北美殖民地勞動力的匱乏,加之《濟貧法》影響,許多窮困潦倒或桀驁不馴的兒童被新世界眾多美景所惑而毅然決然地踏上前途未知的航程,漂洋過海被“合法”運送到北美大陸成為學徒。而在新英格蘭地區,許多年僅幾歲的兒童因其父母無力撫養,亦只得將其送出學藝。至于那些遭遇虐待或照管不良的兒童,兒童福利機構則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棲息與庇護場所。
這些為數不多的兒童福利組織卻在推動兒童福利方面不遺余力,作出了突出貢獻。1853年,兒童救助協會成立,旨在應對紐約區域的孤兒或棄兒問題。與以往將這些兒童予以收容或放任自流不同,兒童被置于撫育院或育嬰堂中。
受“國家親權”影響,兒童遭遇虐待或照管不良時,政府有權干預。但在美國,直至上個世紀聯邦政府才始有這種權力。此前,兒童福利、兒童保護和對弱勢兒童的援助是由私人或慈善的非政府組織和各州政府所主導。到1874年,出現首個因兒童虐待而被刑事檢控的案件。
1875年4月,“紐約兒童保護協會”成立,被譽為世界上首家專職兒童保護的機構。在其130多年的歷史中,該協會始終致力于對孤兒、棄兒的各項福利工作,且功效卓著。僅在其成立后的15年間,協會便安置了超過15萬個被遺棄的孤兒。
剛剛過去的20世紀,曾被歡呼雀躍為“兒童的時代”。一系列兒童權利宣言、公約及議定書紛紛得以通過,專門針對兒童保護的政策如雨后春筍漸次涌現,未成年人保護社會運動伴隨民主思潮亦風起云涌。
1909年,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召開了“受撫養兒童白宮會議”。以此為契機,兒童局于1912年應運而生。該局對涉及兒童福利的議題,從兒童健康及童工到未成年人犯罪與孤兒等諸多議題均不遺余力。到1926年,美國有18個州建立起不同形式的郡兒童福利委員會,其職責在于協調公、私立兒童機構工作。不過,直到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在新政推動下美國才真正出現有組織的社會福利系統。
1925年,少年法院的先驅們在風起云涌的少年法院運動鼓舞下,開始著手《標準少年法院法》的制訂工作。這部示范法歷經多次修訂,其中1959年版本影響最為深遠。在這一版本中,該示范法立法目的被明確為“每位受(少年)法院管轄的兒童都應得到照管、引導及控制,這些有利于其福利及國家最佳利益;當兒童離開父母身邊時,(少年)法院應確保盡可能向其提供所能提供的照管”。1930年,《社會安全法》確定通過提供資金向被照管不良兒童提供干預。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受益于放射性診斷技術的提升,醫學界逐漸介入兒童福利,一些醫療術語及診療方案陸續進入兒童福利的領域。
基于對隱私的高度關注,美國對涉及家庭個人私密的干涉通常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入侵。受此影響,美國并沒有形成正式的家庭政策。取而代之的便是聯邦、州及地方層面對處理不同家庭關系的法律層出不窮。
在這些法律之中,兒童福利特別是有關兒童虐待與照管不良的法律尤為引人注目。20世紀60年代,因人權運動,兒童權利逐步深入人心,使得美國國會在1974年通過《兒童虐待防治與處分法》,該法要求各州應防止、辨認及解決兒童虐待及照管不良。同年,全美兒童虐待中心亦成立了。
隨后出臺的《收養援助暨兒童福利法》、《兒童福利法》,與1984年《家庭支持法》共同確立了美國兒童保護的實施做法及取向,其中《收養援助暨兒童福利法》最顯著的改進在于引介了“家庭探視模式”。在該模式下,即將為人父母者、新生兒父母或家有年幼子女父母,都可以獲取形式多樣的以家庭為重點的社會福利服務,以處理諸如子女教養、兒童健康及安居環境等棘手問題。
1988年,《兒童虐待防治與處分法》通過修正案,要求聯邦衛生部建立全國性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系統。據此,聯邦政府“全美兒童虐待與照管不良數據系統”應運而生,每年對各州及華盛頓特區自愿呈交的兒童虐待與照管不良案件進行數據分析。自1990年起,基于該數據庫的報告每年均向公眾廣而告之。1993年國會又通過《家庭與醫療準假法》,后又分別于1997年與2000年先后頒布《收養與安全家庭法》。

兒童是我們的未來,未來社會的品質取決于當今兒童權利的實現程度
食品保障計劃
雖然兒童福利早已今非昔比,諸多國際公約及國內法均明文確定對兒童的特殊保護,但仍然趕不上社會的日新月異。無需諱言,兒童福利依舊面臨許許多多的尷尬境地。兒童所面臨的問題不單單只是這些,還包括貧困、虐待、照管不良、輟學、離家出走、早孕及缺乏醫療保障等等,不勝枚舉。僅以美國為例,現今全美計有3,7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上,其中1,300萬人為兒童。時至今日,每13名美國兒童中就將近有一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上。
對許多兒童來說,生活已有太多無奈。民以食為天,尤其是在食品安全丑聞層出不窮的今天,對兒童首要而直接的關愛尤以提供充足、安全與營養的食品為重。以食品保障為例,《兒童權利宣言》原則四約定,“兒童應有獲得適當之營養、居住、娛樂及醫藥之權利”。該宣言在原則六繼而又強調,“對于人口眾多家庭兒童之贍養,宜由國家及其他方面撥款輔助之”。對兒童健康成長而言,食品以“質”與“量”上的客觀要求當仁不讓成為基本的生活所需。其中,前者涉及食品安全與營養,后者則關系食品足量供給。
時至今日,即便對于美國兒童,獲取足量的營養也非易事。截至2009年,大約1,720萬美國兒童(約占美國兒童的兩成三)被劃分為食品無保障人群。過度肥胖亦是造成部分兒童營養不均衡的罪魁禍首,最新的數據顯示只有三成五的青少年達到了體育活動要求,亦只有兩成一食用了日均五份水果及蔬菜的推薦標準。
美國從上個世紀中后葉開始,通過各種途徑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食品券在內的一系列兒童食品保障。食品券又稱貧民糧票,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食品補助項目。
根據《1977年食品券法》,“為了促進公共福利,(國會意在)通過向低收入家庭增加不同層次營養來確保國民健康及福祉”。欲加入食品券計劃,申請家庭必須滿足毛收入、凈收入及財產測試等三個經濟標準,其中稅前毛收入必須等于或低于貧困線130%。僅2000年,該計劃向近1,720萬人提供價值150億美元的食品救助,折合每人每月73美元。通過該計劃,受益人可在授權商鋪購買食品,雖然食品券計劃并非單為兒童設計,但從1998年到2004年,四成七受益人為兒童。
除了“食品券”外,美國食品營養項目基本上集中在貧困兒童特別是在校生身上,這些包括《1946年學校午餐法》及《1966年兒童營養法》。此外,還有1954年“特殊牛奶計劃”、1968年“暑期服務計劃”及1968年“兒童及成人照管食品計劃”等等。“全美學校午餐計劃”之出臺使得全美所有學童每個學日都可獲得營養午餐供應。在2,840萬學童中,有1,650萬學童可獲得免費或減價午餐。1966年,美國國會建立“學校早餐計劃”,向出行不便而需搭乘長途車或母親因工作無暇準備早餐之學童提供早餐。到了1975年,該計劃擴展至所有在校學童。在2004-2005學年,全美共有超過8萬所學校參與該計劃,惠及920萬學童,其中八成二學童獲得免費或減價早餐。
1968年,國會建立“暑期服務計劃”,通過與各類教育及文體機構合作,向暑期在家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營養食品。截至2004年暑期,該計劃惠及1,600萬兒童。1968年,國會亦建立“兒童及成人照管食品計劃”,向托兒所等機構提供營養食品及點心。僅2006財政年度,該計劃向290萬托兒所兒童提供食品。
知以藏往,歐美等國從延續種族和提升國家未來核心競爭力角度出發,持續不斷向兒童特別是弱勢家庭兒童提供安全食品的配給,數十年如一日不遺余力,并不斷完善和延伸。缺乏食品保障的兒童福利,如浮寄孤懸。一杯奶、一塊面包看似不經意,然而小處見大,春風拂面。
食品安全作為兒童福利的最低限度配備,處處彰顯著國家對兒童作為生物個體健康成長的關愛體貼與對兒童作為社會個體長遠發展的深思熟慮,本固枝榮。
與少年司法互為表里
考察西方少年司法實例,兒童福利既可以理解為社會理念,亦可以理解為社會機制與社會政策。2005年,“全美少年與家事法院法官理事會”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指南》中特別強調,“兒童福利體系對少年司法有著重要影響”。
取人之長,兒童福利以一系列制度性設計與少年司法互為表里,缺少任何一方都會獨木難支。作為制度層面的兒童福利,涵蓋面甚廣,幾乎覆蓋了少年司法的方方面面,為少年司法提供了四通八達的出口。
相機觀變,清末沈家本變法以降,歷次法律移植中不乏習得歐美真經的成功范例,但“橘生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的水土不服亦不在少數。中國少年司法與西方少年司法很大的不同點在于后者有相對完善的政府配套資源與社會福利為依托,一些原本在西方兒童福利與少年司法構建及改革中不是問題的問題,其引介過程往往因南轅北轍而面臨難以推廣的現實困境。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將福利等同于救濟、慈善或民政,而有意無意忽視了福利,特別是兒童福利在構建和諧社會、促進兒童成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實際作用。
少年司法不單單只是作為防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而出現的,更為重要的是,它亦是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山水相逢中,少年司法與兒童福利逐步形成了共存共榮的體系框架。如香港律政司《檢控政策及常規:檢控人員守則》第12.2條明確規定,“法院必須顧及出庭應訊的少年的福利。這項法例規定,行之已久。因此,在決定是否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提出檢控時,就必須充分考慮該少年的福利。”
事實上,少年司法創設目的是為了兒童福利,也可以說它是為實現兒童利益最大化而步入歷史舞臺的。因而對兒童的保護不但在少年司法創設伊始作用非比尋常,在后來百年發展中亦長盛不衰。即便是在面對“國家親權”及對未成年人正當程序保障質疑的今天,這項基本原則從來也沒有被推翻過。
“市民社會”的充分培育對于有效發揮社會功能,特別是社區對兒童福利保障、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及少年司法構建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基于我國市民社會仍處于萌芽階段的實際情況,政府在兒童福利保障及少年司法中的引導作用不應缺位,只能進一步加強,并適時引導社會及社區相關工作,專門的政府協調性機構對于構建系統的兒童福利體系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以美國為例,專司少年司法與兒童福利的政府機構較多,其不但在司法部專設少年司法與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署,亦在衛生部下設兒童、青年及家庭署及兒童局,負責少年司法與兒童福利的協調、管理與服務。其中,早在1912年,美國國會通過專門法案在當時的商務與勞工部專設兒童局,負責協助各州指導和實施兒童福利政策。
近年來,兒童、青年及家庭署著力在家庭保全、早期干預、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及改進法院對兒童需求的回應等領域拓展職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針對我國當下兒童福利專門政府機構缺失的尷尬局面,或可推動和促進共青團職能轉化,以組建兒童福利局(青少年事務局)為新起點,增添并擴充其社會管理的政府職能。以共青團組織為依托,建立各級兒童福利局(青少年事務局),靈活使用共青團組織這一群團性質及兒童福利局(青少年事務局)這一政府序列局性質,創造性開展工作,把兒童福利落到實處。由兒童福利局(青少年事務局)協調教育、醫療、衛生、民政與司法部門就青少年各議題的合作,推動兒童福利創新。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