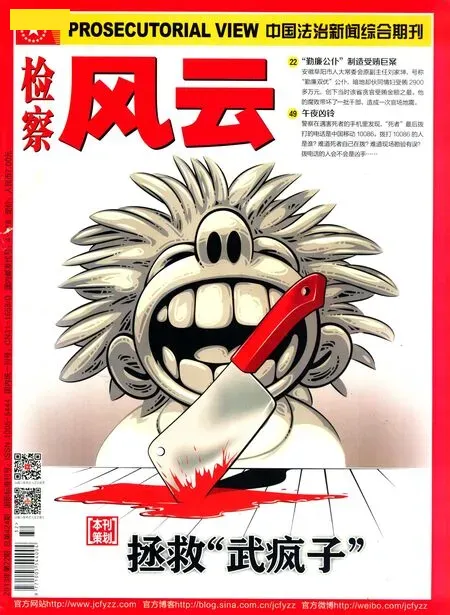劉偉:中國經濟“雙輪”賽跑
劉偉:中國經濟“雙輪”賽跑


本期客座總編輯:
劉偉,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偉教授長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當年被譽為“京城四少”(鐘朋榮、魏杰、樊綱、劉偉)。如果說20多年前的劉偉教授對于自己的名利還有些許的惶恐,那么今天已經碩果累累的他依然謙遜。作為一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很高聲譽的經濟學家,劉偉教授對中國經濟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
中國經濟的“長短策”
《檢察風云》:前些年,針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措施。政府救市使大量資金注入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岌岌可危。
劉偉:短期來看,當時主要是反失業和反衰退。短期內可能有困難,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脅就是失業和衰退問題。中小企業作為中國就業的生力軍,它們要出現了問題,就業保障失衡在所難免。
《檢察風云》:據了解,中小企業承擔了就業的四分之三,國有企業近幾年非但不能提高就業率,反而在減少。在此期間,大量資金投入市場造成通脹,就業保障是否因此也開始失衡?
劉偉:中國經濟實質上是“兩個車輪”在賽跑,同一個舉措形成“兩個車輪”。經過一輪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下來,一方面拉動了需求擴張、經濟增長;另外一方面,它也會推動各種成本的提高、帶動通貨膨脹。換句話說,在需求擴張的同時,它既有拉動增長的功效,也有推動通脹的作用。
中國當時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可以考慮的策略是在一段時間里面,特別是在形成通貨膨脹之前,經過經濟增長的拉動,讓失業問題能夠短期緩解,使反衰退、抗危機取得一定的成果;等過了一兩年,當通脹成為首要問題的時候,可以騰出手來集中治理通脹。所以,我們看到,之后為了緩解失業率,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未來的通脹壓力。
關于中期,主要任務是反滯脹,因為有可能經濟停滯,發展速度沒有上來、失業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貨膨脹。
《檢察風云》:具體而言,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中期可能出現滯漲,背后有著怎樣的動態邏輯呢?
劉偉:短期政策實施之后,顯示不了通脹,更多地顯示拉動增長,但到中期就會表現為需求拉動物價。通常經過一兩年的經濟周期,帶動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動物價。如果一輪宏觀調控舉措下來,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拉動,失業率在短期內不能有效地緩解和降低,那么在過了這個時滯期之后,通脹就會表現出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復雜和困難的局面。
《檢察風云》:要處理好通脹與滯脹的關系,在結構性政策上,應該怎樣處理近期和中期的銜接問題?
劉偉:以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案例來看,剛才說了,當時的策略是:近期主要反衰退、中期主要反滯脹。意思是任務要先明確,近期就反衰退,為此即使加重通脹也值得——凱恩斯主義的菲利普斯曲線正是如此;中期就反滯脹,那只是一個和近期銜接的事情。銜接不外乎兩條: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盡快地顯示出擴張效應,假使對經濟增長和反失業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那就麻煩了;二是如果取得預期效果,失業率很低,經濟增長上去了,過兩年有通貨膨脹就不再恐懼,屆時寧愿犧牲失業率換取通貨膨脹的降低也可以。
《檢察風云》:試圖把兩個矛盾打散么?還是在政策抉擇上,在不同的時段,二者相權取其重?
劉偉:要看二者能不能置換得動。凱恩斯主義當時即是如此,在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有個選擇和替換:如果一個時段內,威脅最大的、首要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業率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就要先解決通脹,為此所有的目標都要服從這個目標,寧愿降低需求、減少通脹,寧愿讓市場疲軟、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要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點。
假如在另外一個時段,中國宏觀經濟的目標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失業率,是經濟停滯蕭條,那么所有的問題都要為解決失業讓步。到了這種情況,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價是物價要上升,即意味這個時候政策重點的選擇是要降低失業率,而不惜提高通貨膨脹率。
為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犧牲次要矛盾,這就是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但也有人認為,為什么到上世紀70年代出現問題了呢?特別是當時中東戰爭、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在全球范圍內提高,此時就出現了滯脹。這種局面實際上意味著,凱恩斯那一套已經失靈了。
從總供給角度調結構
《檢察風云》:從總供給角度看,應該怎樣調整宏觀政策結構,降低就業率,來提高經濟效率呢?
劉偉:宏觀地看,物價總水平和失業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滯脹。物價總水平、宏觀問題講的不是股市或樓市等某一個產品。
因為滯脹的局面很復雜,宏觀政策選擇起來也很困難,所以必須就要考慮:第一,這一輪拉動增長的效應能否盡快顯現出來,增加就業,如果顯現得越快,就恢復得越好(即使出現通脹),我們政策掉頭時候的“本錢”就越大,就可以把宏觀政策搞得很緊來治理通脹了,“彈藥”充分;第二,如果通過一輪政策下去帶來的增長不大,失業率不低,通脹一來就不敢大手筆地治理通脹,因為失業的壓力太大了。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和拉動增長的效應,對未來經濟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
《檢察風云》:控制滯脹必須提高經濟效率,那么未來滯脹的關鍵因素有哪些?怎樣才能有效控制滯脹?
劉偉:的確,此時要特別考慮這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因為未來出現滯脹的關鍵是成本提高,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品的價格、生產數據投入品(煤電運油、上游投入品)的價格。特別是在這兒,一方面資本品、稀缺品的價格在提高,另一方面,關鍵是人們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滯脹的要害是成本推動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產出沒有壓住它,所以要特別突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技術含量、投入產出比越好,未來滯脹的可能性就越小。
《檢察風云》:調結構與提效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劉偉:結構變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樣,使其在國民經濟中成長的競爭力不同,然后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就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包括地區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所以,結構變化是效率改善的結果。
這兩者是中長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總需求那樣,措施一下去就見效。
《檢察風云》:結構的調整,是為了提高效率。此間,必要的銜接點有哪些?
劉偉:從總供給角度調整結構,提高效率,就需要技術和制度的改變。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務銜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總量擴張和結構調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統統銜接好。這才是在能夠有效地保增長、擴就業的同時,避免未來中期出現滯脹的根本辦法。
當時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意識到,近期威脅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滯脹。治理衰退就是刺激總量需求,但是治理滯脹就不是總量的問題了,而是供給問題,就要有結構的變化、有效率,這樣才能把成本降下來。
市場化方向不容逆轉
《檢察風云》:通過這些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考驗,中國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還有哪些不足?一旦危機到來時,我們使用金融工具時可能出現哪些問題?怎樣改進?
劉偉: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肯定有問題,各個國家的貨幣問題都在通過這次危機自我檢討。有人認為貨幣政策根本就沒有用,甚至認為危機是貨幣政策惹的禍,然后讓財政政策來買單。
但在中國,說句老實話,不是貨幣政策不夠松,而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有問題。整個社會制度,使得整個貨幣的擴張傳遞不出去,實現不了,這個是很要緊的問題,比如心臟需要供血,但是血管這兒被堵塞。這恐怕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檢察風云》:此外,對中國與世界的一體化問題您怎么看?
劉偉: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怎么和發達國家一體化?我們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體化?我們有自己的社會制度的經濟、社會、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體化?
中國要是真正進入西方的一體化,弄不好自己要蒙受更大的災難,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一般我們不要撇開自己和國際的現實,去盲目簡單講一體化,像歷史上東歐的一體化實踐都證明是失敗的。
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對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趨勢,是遏制不住的歷史潮流。中國以后的經濟發展一定是全球當中的一部分,中國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一定是全球化的一個內容。這是對中國體制影響非常關鍵的問題。
采寫:朱敏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