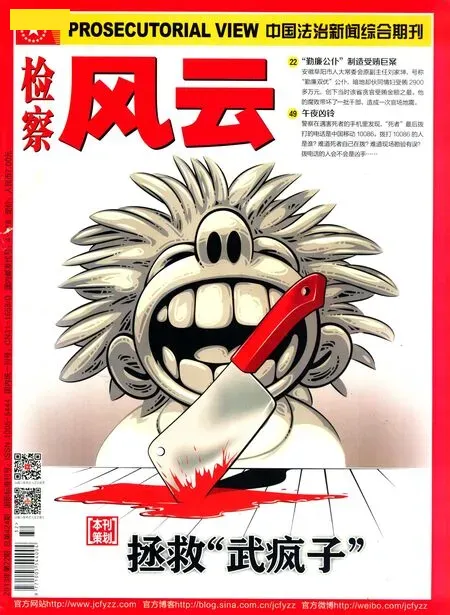美國政府關門的法律迷思及啟示
文/張克
美國政府關門的法律迷思及啟示
Revelation in law of US government shutdown
文/張克

近一個月來,全球最大的政經新聞莫過于美國聯邦政府宣布關門。半個月后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財政法案結束政府停擺,并提高債務上限。
中國媒體與知識界對美債事件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討論的文章層出不窮。本次政府關門是1974年以來的第18次,為何美國政府如此頻繁地在預算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其根源很難僅僅由經濟視角解釋全面,作為一個法治化程度極高的國家,政府一關一開背后的法律體制與困境更令人深思。
否決制才是政府關門的根源
美國政府關門事件的本質是預算危機和債務危機,表象是奧巴馬醫改法案巨額支出和債務上限問題兩黨存在分歧,究其根源在于美國否決制的法律體制,即同時擁有巨大組織能量和權力的眾多“玩家”在主導國家的立法,這已經成為美國體制的重大弊病。
以奧巴馬總統視為政治遺產的醫療改革方案為例,這一旨在為3000萬當前醫療保險體系之外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福利的法律遭遇共和黨保守勢力的抵制。
即使國會于2010年通過了醫改法案,并不意味著全美都能保證政令暢通,奧巴馬總統在推進這一法案的過程中遭遇了司法和政治的雙重否決。在共和黨控制和煽動下,超過26個也就是近一半的州向法院提起醫改法案的違憲訴訟。在一個崇尚個人自由的國家,是否買醫療保險是個人決定,法律不得強制他們買或不買保險。醫改法案的反對者認為這一強制令侵犯了個人自由,違反了美國憲法。共和黨人提出,奧巴馬的醫改方案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同時違背了美國憲法中對聯邦和州政府權力劃分的規定,聯邦不能規定州的義務。
將政治分歧訴諸司法是美國傳統。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任之前是一位公益訴訟和維護少數族裔民權的專業律師,同時他也在聲名顯赫的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擔任高級講師,講授的正是美國憲法與民權。對于醫改法案在最高法院的憲法訴訟,作為曾經的憲法訴訟律師和一位憲法學家的奧巴馬對此似乎并不擔心,果不其然,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以5比4的微弱優勢判決醫改法案符合憲法。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改變觀點,站在了自由派陣營的一邊,最終令奧巴馬醫改法案避免違憲命運。羅伯茨建議將“強制醫保”條款視為“稅收”,而稅收則是聯邦政府的權力,由此使“強制醫保”條款不違憲。
在重大法律和公共政策領域缺乏共識是以多元主義為基礎的美國政治的一大特點,過分強調立法決策主體之間的相互制衡,導致不同權力機構之間相互否決的現象十分突出。最高法院支持奧巴馬總統讓共和黨不得不在另一個重要的否決事項——預算法案上大做文章,這也是半個月以來美國政府停擺與重開的直接原因。
預算是連接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鍵紐帶,也是美國三權分立下的各機構相互否決的慣用工具。1974年到1996年美國政府因預算分歧被迫關閉了17次,這次是第18次,但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幾經流轉的美國預算審批權
美國預算審批權力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建國至1921年是由國會主導,根據美國憲法第九條規定,所有的征稅議案都由眾議院提出。這一時期,由國會主導的預算審批在剛開始還能有效應對實際需求,但隨著工業化進程和社會矛盾的涌現,政府治理權力不斷擴張,預算權旁落導致總統代表的行政機關無法快速高效地做出財政安排。
1921年,美國通過了《預算會計法案》,建立了預算署和總審計署。總統代表整個行政部門提交預算,產生了專門工作機構——預算局來行使職責。總統主導預算法案直到1974年為止,這一年通過了《國會預算法案》和《截留控制法案》,使國會可以獨立起草預算提案并建立了專業的分析機構,從而加強了立法機關在聯邦預算程序中的作用。
在當時現有的收入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的基礎上,國會參眾兩院又分別增加了預算委員會。這一改革的結果是使得預算提案不再是總統的專利,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也不再是預算在技術上的壟斷者。國會不僅可以表決預算,也可以提出預算議案。
第三階段則是1974年至今,其特點就是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制約,我們所說的美國政府關門事件在這一時期反復出現。每當民主、共和兩黨在法律與公共政策等某些重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時,在國會中占據優勢地位的政黨就會通過不批準總統預算辦公室提出的預算法案,以此要挾總統就范。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否決型體制存在諸多弊病,不利于法案政策高效快速推行。然而,如何看待這種否決型體制以及美國政府關門事件對中國有何警示意義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當前中國在再分配領域如醫改方案、養老改革等政策過程中展現出一種既有別于傳統閉門決策又異于西方國家否決體制的共識型決策模式。這種共識型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在決策過程中重視社會各方利益表達的整合與協調,集結不同意見,努力尋求共識。在美國政府因政治分歧關門開門折騰之際,中國的共識型決策模式應當吸取美國教訓,更為有效地整合各方利益,保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民生政策得到高效、民主的決策和執行。
對中國財政法制建設的啟示
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社會普遍認為金融和財稅體制改革將是本輪新政最具突破性的內容。落實到我國財政法制建設,預算法修改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一項工作。預算法究竟應當怎么改?目前來看,其方向就是要將預算由政府管理社會的工具轉變為規范政府收支行為的法律。
在中國,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審查預算是立法權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權力。然而,人大對預算案的否決權、修正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權力被虛置。以剛剛被“雙規”的南京市市長季建業為例,其任上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建地鐵、砍梧桐,引發了很多爭議。重大項目決策要通過人大審查,如果南京市人大能夠做實預算審查和監督的權力,類似不得民心的項目也許就不會被強制推行。嚴格控制項目預算也就可以相應減少尋租腐敗的空間。
目前,省級人大的預算審批權和廣東省、福建省、深圳市、廈門市人大在預算監督方面取得了許多令人鼓舞的進展。審慎科學、代表民意的重大決策要求加強人大預算審查、預算修正權,這才是美國政府關門事件對中國最有現實意義的警示。
美國是西方世界中唯一一個對聯邦政府的債務進行嚴格立法限制的國家,然而國債立法卻沒能有效地控制債務規模,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幾乎每年都需要提高國債上限。國債上限確定的是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量,但實際涉及的是“借新債還舊債”的可支配額度,并不涉及年度預算所決定的政府赤字或支出。
為什么美國國債可以以新還舊不斷地玩下去?是因為美國向全世界征收了鑄幣稅,以其金融強勢地位讓美國國債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資產。而美國國債最重要的持有人就是中國,以此觀之,中美在全球債務危機的現實情況下已經不可挽回地成為某種程度上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識別與化解正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財政法制建設的核心任務。從法理層面來看,以地方融資平臺為代表的債務風險的產生是央地法律關系不明確、政府與市場的法律界限不清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法律關系混亂所造成的,因此,理順現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市場、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風險所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由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缺乏相應的明確性規范,使得央地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確。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行政區域內控制力與影響力的延伸,一方面肩負著代替中央政府履行為本地區居民提供基本公務服務的重要職責;另一方面,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員,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獨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訴求。這種雙重角色使得地方政府經常越俎代庖,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設法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而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相應法律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政府和市場的法律界限不清,地方政府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不斷變化角色,追逐自己的利益。
從明晰法律關系的角度分析對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的控制,應遵從以下幾點原則: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明確市場和政府的法律界限;規范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法律關系。
只有明確央地政府的職權劃分,形成權利義務對等的合理局面,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舉債沖動;只有明確政府和市場的法律界限,才能避免政府以行政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競爭,與民爭利;只有規范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法律關系,形成合理的投融資機制,才能從源頭上治理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