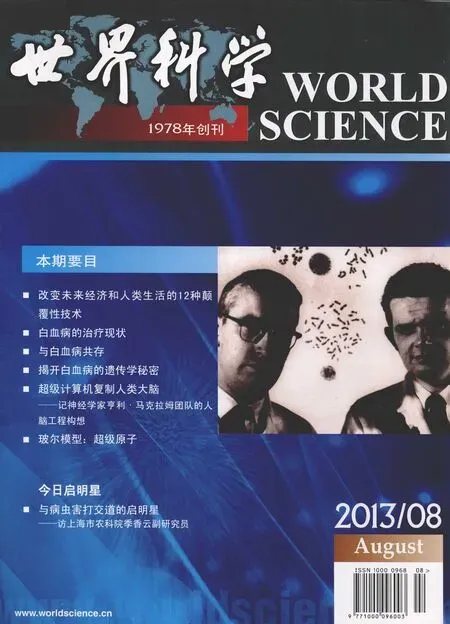用數據說話
——記章振林教授團隊對遺傳性骨病的病例收集與數據分析
本刊記者/李 輝
用數據說話
——記章振林教授團隊對遺傳性骨病的病例收集與數據分析
本刊記者/李 輝
本期項目:骨質疏松和單基因骨病遺傳機制及臨床應用;
所獲獎項:2012年度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第一完成人: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章振林教授。

章振林,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骨質疏松和骨病專科主任,骨代謝病和遺傳研究室主任,醫學博士,主任醫師,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華醫學會骨質疏松和骨礦鹽疾病分會副主任委員、上海醫學會骨質疏松專科分會主任委員。2008年入選上海市科委優秀學科帶頭人;2013年入選上海市領軍人才。
2007年的一天,章振林教授接到一名51歲的女性患者。她訴說30多歲后容貌變化很大,手指明顯變粗,顴骨也越來越突出。出于對遺傳性骨病的敏感,章振林詢問其家人是否有類似的癥狀,該女士說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有。這位女士是嫁在上海的江蘇人,于是章振林請求和她回一趟江蘇,探訪她的父親和哥哥并請他們一起來上海診治。
根據癥狀,章振林一開始認為這一家三人可能是佝僂病患者,但在反復分析患者X線特征并結合生化檢查結果后,章振林判斷他們罹患的可能是特殊類型的畸形性骨炎——一種相當罕見的骨病。根據這一判斷,章振林大膽對先證者予以雙膦酸鹽靜脈滴注,僅僅一個月之后,患者的骨痛就顯著減輕,其特征性表現之一的高水平血堿性磷酸酶,也開始呈現顯著下降。
在已報告的文獻中,全球只在日本有一個同類型病例——由RANK基因突變導致的早發性畸形性骨炎——的家系,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根據日本的這一報道,章振林對三名患者進行了RANK基因突變檢測,并找到了這一致病基因。章振林診治的這一病例,因而也成為了全球公開報道的早發性畸形性骨炎的第二例。
查明病因后,進行醫治就可以有的放矢了。該疾病因于破骨細胞功能顯著增高,因此使用雙膦酸鹽類藥物治療,即可以抑制骨吸收,緩解骨痛,延緩病情。經過章振林的治療,這位女士和她哥哥的病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她父親也沒有特別受到這種疾病的折磨,一直活到近80歲。
國人自身的骨病致病基因突變譜
這位女士一家三口所罹患的畸形性骨炎,在醫學上被歸于罕見病,顧名思義,是指發病率極低的疾病。章振林關心的主要是涉及骨骼的罕見病。由于骨病大多是先天性的,患者在青少年時期往往就表現為骨骼無法正常生長,成年后畸形殘疾的比例很高。
對于罕見性骨病來說,遺傳因素——致病基因的突變——通常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具體來說,罕見性骨病屬于單基因遺傳性疾病,只要任何一個與疾病相關的致病基因發生突變,這種疾病將必然發生——發病率是100%。目前已知的單基因遺傳性骨病有456種。通過對先證者檢測與某種單基因遺傳性疾病相關的所有已知致病基因,就能夠發現有可能導致先證者發病的致病基因突變。基因檢測對于疾病確診、有效治療以及產前診斷和干預,都是關鍵。
對于單基因遺傳性骨病的診斷治療,西方發達國家開展較早。他們對一些遺傳性骨病已經建立了較完善的基因篩選流程。但在中國,僅僅一些大型醫院或者科研單位開展有相關的工作,規范化的診治才剛剛開始。
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群屬于蒙古人種,與白種人或黑種人的遺傳背景有很大差別。因此基因檢測,必須基于中國人自己的致病基因突變譜。但由于起步較晚,現在國人骨病的致病基因突變譜還沒有建立起來。
事實上,在中國眾多人口的基數下,雖然某一種罕見病分散各地較為少見,但整合起來也有相當大的數量。將這些罕見病的病例聚集在一起,統計、分析、研究,建立漢族人群的致病基因突變譜是完全可能的。
這正是章振林所做的工作。建立大樣本量的單基因骨病數據庫,以及開展后續基因篩查研究的重要發現,正是章振林團隊此次獲得上海市科技進步獎的關鍵成果之一。
歷時10年的門診、探訪、分析和記錄
章振林對罕見骨病病例收集整理的動力,來源于他對疑難雜癥的興趣。章振林畢業于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協和的人喜歡看疑難病。這是研究型醫院的職責,也是我們一貫的思想。”他如此說,“遇到疑難病、少見病,我喜歡做記錄。我已經記錄了十幾本。”這種對疑難雜癥收集研究的功力,章振林歸功于其博士研究生導師孟迅吾教授的言傳身教。
2000年于協和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后,章振林來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做了兩年博士后。期間,他完成了FasL轉基因小鼠胰島移植方面的研究工作。這兩年的研究涉及一些遺傳學方面的科研思路和訓練,為章振林日后開展骨病遺傳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做博士后是為了鍛煉我自己的科研能力”,他說。

每遇到一例疑難骨病病例,章振林就會紀錄下來,這樣的筆記本他已經紀錄了十幾本
然而,既受到協和的臨床培訓又在中科院經歷了科研的錘煉,在剛剛進入第六人民醫院時,章振林卻遇到了瓶頸。十年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對醫院臨床申請的項目批準很少。在當時,大多數醫院在臨床上有明顯優勢,但在科研上則水平有限。“十年前我剛來六院的時候,六院的科研氛圍也還不夠濃。”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章振林繼續說道:“當時我很迷茫。沒有條件用小動物做實驗,也找不到研究方向。”
但在半年之后,章振林意識到,臨床資源也是獨特的科研資源。對于某一罕見病患者,確診病情之前必須明白其發病原因;對于某一罕見病病因,必須有患者出現才能獲取數據和分析數據。罕見病病例研究正是醫院得天獨厚的優勢。“我找到了這個思路,利用臨床資源來做科學研究,反過來科研成果指導臨床實踐。”
章振林診治和研究罕見病的患者來源,一些是前來上門門診的,還有一些是網上發布求助信息的。對于后者,章振林發現后會自己或派團隊成員到病人所在地,與病人約談,有時候還用自己的科研經費將病人請到上海。如今他們實地探訪和采樣的足跡已經遍及新疆、內蒙、安徽等全國20多個省市。
隨著病例的增多,數據的量也越來越大。章振林團隊在全國范圍收集成骨不全、原發性骨硬化癥和佝僂病等近30種主要骨代謝病的臨床資料(影像學、病理學等)和血液、組織等標本,截至目前已經構建了較為完善的近600個家系庫,達到2 000多例。這些骨病中,最多的是成骨不全(由于組成骨骼重要的1型膠原基因突變導致骨骼反復骨折以及發生耳聾等癥狀),其次是佝僂病,患者生長遲緩、骨骼畸形等。
由于政策原因,基因檢測項目在我國臨床還是不能收費的,因此章振林對所有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基因突變篩查,都是用自己所申請的課題經費來承擔的。到現在為止課題組在此方面花費的經費已超過200萬元。
在從2002年開始的十余年時間里,章振林就這樣通過門診、探訪、分析、記錄,一步步建成了如今國內最大的單基因遺傳性骨病數據庫。
基因突變譜系建成后的臨床與科研
從對這些數據的分析中,章振林獲得了臨床與科研的雙重收獲。
基因突變譜系建立之后,對本土罕見骨病進行有效地確診、干預和預防就有了基礎。截至目前,章振林團隊根據基因診斷,已經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確診了200余例涉及30多種類的遺傳性骨病,并對部分家系開展了產前診斷、干預和預防工作。所謂干預,是指針對發現的致病基因突變,確診疾病,對一些有治療藥物的病例進行及早處理。所謂預防,是對有家族遺傳風險的產婦進行產檢,從8-12周孕婦處提取羊水,獲得DNA,進行基因突變檢測。如果發現致病基因突變,在孕婦同意的情況下,通過流產等手段切斷該遺傳病的遺傳鏈,從而降低發病率。章振林的診治方法,已經在多家醫療單位得到推廣和應用。
在診治病情的過程中,章振林也發現了一些新的致病基因。一種名為原發性厚皮骨膜病的骨病,患者通常表現為顏面、前額、頭部皮膚肥厚,呈皺褶狀,額橫紋增深,伴有杵狀指(趾)。2008年,英國學者證實前列腺素E2(PGE2)水平增高是這一骨病的發病原因,并發現了降解PGE2的酶HPGD基因突變導致該病,在此之后醫學界認定該基因突變是唯一病因。而章振林團隊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發現,該基因突變不能完全解釋一些臨床表現嚴重的病例,他們應用全外顯子測序技術,發現了導致本病的另一元兇——SLCO2A1(其功能是調節細胞內外轉運PGE2的蛋白)。
這一研究成果在國際人類遺傳學研究領域的頂級學術期刊《美國人類遺傳學雜志》發表,旋即引起了全球關注。這一創新性發現正是依賴于收集的家系——因為只有具備一定的樣本量才可以開展致病基因突變篩查。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該基因的發現使臨床上可以使用降低PGE2的藥物進行對癥下藥。治療三個月,患者面部皮膚等癥狀即可得到顯著好轉。
章振林團隊根據他們建立的大樣本量國人成骨不全致病基因突變譜,也統計分析出了一些以前不曾發現的罕見骨病發病規律。例如,他們發現95%成骨不全患者為1型膠原α1或1型膠原α2基因突變,其中1型膠原α1基因突變最常見,占所有患者的75%。再比如,他們發現國人最常見的遺傳性骨硬化癥是常顯2型,其致病基因為CLCN7。
●相關鏈接●
在章振林的患者中,有一對夫婦是一種隱性遺傳病——脊柱骨骺發育不良——的隱性突變攜帶者。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長大后,呈現出腳彎的疾病癥狀。在對這一孩子醫治的過程中,章振林告訴這對夫婦,在生二胎之前,務必做羊水穿刺測定孩子遺傳該病的幾率,以避免新的悲劇產生。很遺憾,由于這對夫婦當時沒有做這樣的測試,第二胎罹患了同樣的疾病。
單基因骨病雖然已有310種致病基因明確,但是僅12種可以治療。章振林介紹說,目前能夠進行藥物緩解癥狀的骨病僅僅是極少部分,有三分之一患者可以通過骨科手術進行矯形,但其他部分基本處于無藥可治的狀態,唯一能夠減少悲劇的方法是開展高危人群篩查,開展產前診斷等干預,阻斷疾病的遺傳鏈。近年來,章振林團隊一直與這類病患人群保持聯系,目的就是希望能防患于未然。
寫在最后
限于篇幅,本文只寫了章振林此次獲獎項目“骨質疏松和單基因骨病遺傳機制及臨床應用”中關于“單基因骨病”的部分。事實上,章振林團隊在骨質疏松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樣值得公眾所知。他們在十年的時間里,收集了近6 000例漢族人群骨密度等數據和DNA樣本庫!通過這些數據,他們發現了容易患骨質疏松的人群特點。通過這些數據,他們發現漢族人群骨質疏松遺傳背景與白種人群有顯著不同,一些候選基因多態性對白種人和漢族人群具有不同的風險性。
我們之所以主要介紹章振林教授關于遺傳性骨病的科研成果,是因為我們希望更多的“罕見”病患者通過本文能夠獲得信息和信心。實際上,無論是針對遺傳骨病還是骨質疏松,章振林以數據的積累和分析為中心的項目本身,毫無疑問是現階段科技創新的經典案例。“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基于數據的大量產生,而數據的產生則需要扎實而持久的積累——這正是“章振林”們所做出的貢獻。他們熱衷于收集數據,將數據電子化,將數據規模化,為本領域大數據的來臨奠定著堅實的基礎。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數據的持續積累,章振林團隊將繼續在骨病的臨床、科研以及轉化醫學等方面做出更多更優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