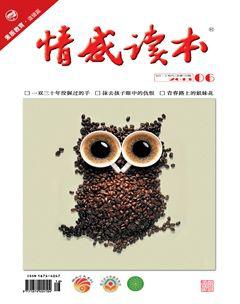誰在分分秒秒為你擔心
周瑩
一
七月的一天,上高一的兒子忽然告訴我,他要去參加暑假期間校外組織的夏令營活動。他的語氣鏗鏘有力,沒有半點回旋余地。倚在房間的門檻上,看著第一次自己收拾東西的兒子,我的心,頓時像懸在半空中的石頭,無法落地。
“不去不行嗎?”我小聲地問。兒子頭都不回:“不行。”“那你晚上洗澡后要把襪子換掉,早上記得刷牙,累得氣喘吁吁時,不要急著喝水,會嗆著……”
“知道了,都說多少遍了。”我的話沒說完,兒子已不耐煩地打斷了我。
我閉上了嘴,那塊石頭卻堵在了心口。
看著兒子和他的伙伴們乘坐的火車像射出去的箭,在凌晨向著南方呼嘯而去,我悵然若失。回到家,我感到整個心都被掏空了。兒子雖然17歲了,但是,他在我眼中還是個孩子,從未離開過我,他不會照顧自己,也不懂照顧他人。出門半個月,沒有我在身邊的日子,他是否會驚慌失措?是否會茫然無助?
兒子出門時的無所謂盤踞在我的心中,無助的我陷入一種無望的惶惑中不能自拔。
午夜,躺在床上,分分秒秒,焦急不安,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中,電話響了。我一看,才凌晨5點多。接了,是母親的電話。
“昨晚夢見你哭了,半夜醒來睡不著,好不容易挺到早上,趕緊給你打個電話,你沒有生病吧?”母親的聲音透著焦慮和擔憂。
我困得要命,敷衍母親說:“我哪里生病呀,還在睡覺呢。我又不是3歲小孩子,你不要老惦著我,好不好?”“哦。沒病就放心了。那你趕緊接著睡吧。”母親似乎為打擾了我的睡眠感到不安,像做了錯事的孩子,匆匆掛斷電話。
聽著話筒里傳出的忙音,我卻再無睡意。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擔心和牽掛,這一幕其實是多么相似啊!
二
在我漂泊城市的這些年里,母親總是隔三差五地給我打電話。母親不識字,不會寫信,唯一可以交流的方式就是通電話。
那時,母親家里還沒有安裝電話。想我了,母親就提一籃子雞蛋,跑到7里開外的鎮上,找一家公用電話,把寫有我電話號碼的小本遞給電話亭的人幫忙撥通。通話完畢,母親就用賣雞蛋的錢付賬。
母親給我打電話的時間永遠都是一大早。很多時間,我都在睡夢中,而母親卻在露水打濕褲腳的清晨走了7里多的山路,尋找到那根連通女兒聲音的電波線,傳遞牽掛。在得知女兒一切都好之后,她才一路小跑回家,去伺候那一群雞鴨和牛羊。
記得有一次,我放下電話后,還想和母親說幾句話,立刻把電話回撥過去。“早就回去了,丟下電話就開始跑。”電話亭的人告訴我。電話那端的我,心頓時像刀割一般,生疼。
想起往事,內疚一點點襲上心頭。曾經,在和母親分離的日子里,感覺城市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我一心一意地生活在這份精彩中,忽略了千里之外母親的牽掛和擔憂。
特別是在我結婚后,母親的電話來得格外勤。我常常在電話里對母親說不要牽掛我。可是,隔不了幾天,母親的電話還是照樣來了,還是那些老掉牙的問候:外面的豬肉沒有油水,我給你郵寄一些臘肉過去,補補身子;我順便給你郵寄一些核桃,補補腦子……我知道母親是好心,但我固執地認為大城市里什么都能買到,費那個勁兒不值,所以每當母親說要給我寄東西時,都不耐煩地打斷了她:我什么都不缺,你留著錢自己花吧。
直到有一天,我去郵局取稿費,遇到了一件事,才讓我似乎理解了一顆母親的心。
一位白發老太太手里提著一個大包裹要求郵寄,郵局工作人員不給她辦理。老太太一個勁地央求:“我女兒最喜歡吃我腌的咸鴨蛋,喝我做的糯米酒,為什么不能郵呢?”我也幫著老太太說好話,工作人員解釋說,糯米酒是液體不能郵,咸鴨蛋可以郵。最后,老太太在勸說下把成鴨蛋郵寄了,一壺糯米酒,只好自己提走了。臨走的時候,老太太不住地嘮叨著:“這么好的糯米酒,你就是喝不成,你不喝一點,我心里咋放下啊。”
望著老太太孤獨離去的背影,我的心里酸楚不已。她讓我一下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才意識到母親好久沒有打來電話了。
掏出手機,我趕緊給母親撥電話,卻發現母親的手機欠費停機了。我跑到移動服務大廳,為母親的手機充了話費。3年前,母親為了給我打電話,賣了一頭肥豬,買回一部手機。
手機鈴聲響了很久,母親才接起來。電話這端的我有點不快:“媽,手機怎么還欠費了?”“家里農活忙,就忘了去充錢了。”母親說,聲音里卻透著掩飾不住的疲憊。“家里不是出什么事了吧?要不月末我請幾天假回去看你。”“沒事,家里能有啥事?你工作那么忙,好好工作吧,我和你爸都好著呢。”母親說。
直到那年春節回家,我才知道母親干活時不小心將小腿摔骨折了,在家里躺了近3個月。她怕我擔心,一直不讓親友告訴我。
后來,我也常常主動給母親打電話,每次接到我的電話,母親都很高興,說丫頭長大了,知道惦著媽了。只是這樣的時光很短暫,自從生下了兒子后,我的生活重心全部落在兒子身上,每日在忙忙亂亂中,對母親的牽掛又漸漸地被我忽略了。
三
兒子出門兩天了。
這兩天我飯吃不下,覺睡不好,喝水都沒味。想到這些,就忍不住想給兒子打電話問一下。轉念一想,又忍住了。
第2天,兒子終于來了一條信息:“放心,一切都很好。”
我感到欣慰,還好,這小子還知道媽媽在惦記著他。
第5天,兒子發來信息:“玩得很開心。不要牽掛我。”
讀完信息,心里又酸又咸。
第10天,兒子發來信息:“玩得太累,忘記想起你了。”
我的眼淚,奔涌而至。
第14天,兒子發來一條信息:“明天晚上到家。”我趕緊回復:“幾點?我到車站接你。”“不用。”就這兩個字,再無下文。
我心里擱著一個疙瘩,一夜難受到天亮。
第二天晚上,兒子自己回來了。出門15天,沒有打回來一個電話,一共只發了4條信息。從兒子手中接過行李,就在轉身的剎那,我的眼淚悄然滑落,有喜悅、有激動,更多的是辛酸和失落。
夜半,趁兒子酣睡之際,我偷偷地來到兒子的床前,看著兒子那張漸漸脫離稚氣的臉,不由感嘆道:兒子長大了,他不再是那個整日跟著我屁股后面轉的小娃娃了。
四
一周后,我向單位請了年假,帶著兒子到千里之外的鄉村看望母親。
母親種了十幾畝地。我和兒子一起幫母親剝花生、喂豬、洗衣服、摘黃瓜。傍晚時分,我們陪母親到山坡上放牛羊。一群牛羊在山坡上愉快地啃著草芽。蒼山如海,夕陽如畫。母親臉上的笑容猶如山花般燦爛。
晚餐時,吃著母親包的韭菜餃子,父親說:“其實你媽這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常回來看看她。早些年家里困難時,每年春節前,你媽都要想盡力法給你郵寄一些臘肉什么的,要不然,那個年,她是絕對過不安穩的。其實,我給她說過多次,郵費那么貴不劃算,大城市啥沒有呀,可是她就是不聽……”
母親翻著白眼阻止父親道:“說什么說……過去的事情,不許再提!”我扭過頭去,假裝擦鼻涕,趕緊把飽滿的淚水和著餃子一起咽下去了。
晚上,我們圍坐在廳堂里閑談。母親發現我腳上穿的襪子破了,就伸手把我的襪子脫下來,硬要給我縫。母親穿針時,好幾次線頭穿不進去。我接過針線,三下兩下就穿好了。我把針線遞給母親,母親手腳麻利地很快把襪子縫好,然后低下頭,用牙齒把襪子上的線頭咬斷。
“姥姥,媽媽的襪子不臭啊?!”看到這一幕,兒子驚訝地問。
“不臭!哪有媽媽嫌自己孩子的?你媽小時候,姥姥天天親她的小胖腳丫呢!”母親笑呵呵地說。
我的心里一顫,又有淚流盈睫。這又是何其相似的一幕——兒子出生后,我不也是喜愛得天天親他的小腳丫、小屁股、小臉蛋嗎?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兒子不再粘著我,不肯再讓我親他了呢?
那天晚上,我再一次和母親同睡一床,卻已是時隔25年了。
黑暗中,母親三番五次地伸出手來,把我露在外面的手臂塞進被窩,并為我掖好被角。我閉著眼睛假裝睡去,心里卻早已柔軟成一灘水,點點滴滴將枕頭染濕一片……
五
一個晨霧彌漫的早上,我們終于要走了。
村口的槐樹下,母親望著我欲言又止。我說:“媽,還有什么話嗎?只管說吧。”
母親猶豫了一會兒,才吞吞吐吐地說:“你不在我身邊,天冷了,要添加衣裳;天熱出門時,要戴帽子;你要是好久不給我打電話,我擔心你是不是生病了……有事沒事的,打個電話回來……”,母親一邊擦眼淚,一邊嘮嘮叨叨地說著,我看見兒子的眼眶也紅了。此情此景,想必兒子一定也很熟悉吧?
“媽,我知道了。”我點點頭,把母親送給我們裝著臘肉、土豆干、雞蛋的紙箱放在了車上,盡管很沉,但這一次我沒有再拒絕這份沉甸甸的母愛。
車開始啟動的時候,母親的聲音飛入車廂,鉆進我的耳膜:“你啥時再回來?”
“媽,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我大聲說。
揮手告別的那一刻,回頭凝望,透過迷迷蒙蒙的晨霧,母親站在身后的山梁上,一絲白發被晨風吹起,她的身影越來越小……
我的淚終于落了下來。這時,一雙溫暖的大手輕輕摟住我的肩,這是兒子長大后第一次主動和我親近。我和兒子相視一笑,眼中都是淚光閃閃……
趙自力摘自《2011年中國精短美文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