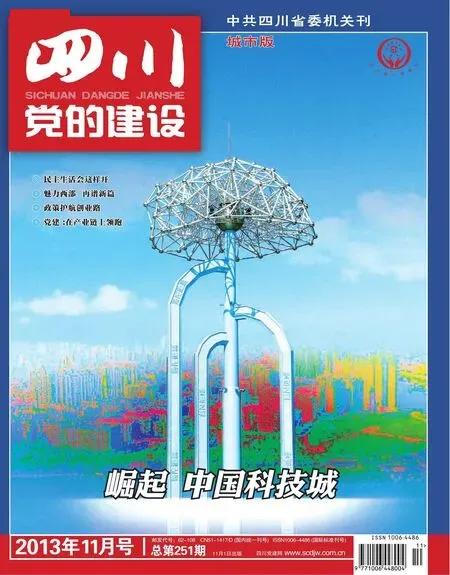毛澤東與三幅成都名聯
●文/劉全
毛澤東與三幅成都名聯
●文/劉全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抵達成都,參加即將在成都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歷史上的成都會議。
3月6日下午,在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興致極高地來到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武侯祠,參觀武侯祠古建筑群。毛澤東先到碑亭詳察了石碑,隨后觀看二門和劉備殿的對聯。在來之前,毛澤東早有耳聞諸葛亮殿前的治蜀名聯,要到諸葛亮殿時,他對隨行人員說:“武侯祠內楹聯隨處可見,以諸葛亮殿前清末趙藩所題最負盛名。”隨后,毛澤東與隨行人員一同認真讀了諸葛亮殿前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毛澤東還反復吟誦,品味這幅對聯的妙處和深意。
這幅對聯寫的是諸葛亮的生平思想,是清末趙藩創作并書寫的。上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概括諸葛亮的軍事成就,總結其軍事思想主要特點是“攻心”為上。即諸葛亮注重從精神和心理上瓦解對方的作戰意圖,在戰略上戰勝對方,使對方心服。趙藩對諸葛亮軍事思想特點的把握很準確,15個字便囊括了要領,還點出軍事的要義不在于好戰,而在于和平,這個思想更加可貴。下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概括了諸葛亮治理蜀國的政治經驗,重點強調要“審勢”,根據具體形勢作出決策,制定相應政策。下聯從反面指出不詳查客觀實際,不根據形勢施政,則“寬”和“嚴”兩種政策容易錯位,導致失誤。對聯全文30字,卻高度濃縮了諸葛亮的軍事和政治智慧,成為難得的對聯佳作。
這幅對聯的魅力除了對聯自身的內容外,對聯的背景也起了交相輝映的作用。對聯的作者趙藩(1851-1927年)是云南劍川縣人,白族,先后擔任過四川籌餉局提調、署鹽茶道、永寧道等職,并兩任四川按察使,對巴蜀文化非常了解。1902年冬天,時任四川鹽茶使的趙藩游覽武侯祠,因想到新任四川總督岑春煊推行用武力鎮壓民眾的情況,心生憂慮,本欲直接勸誡,但趙藩早年得到過岑春煊家族的資助,不便直接指出岑春煊的錯誤做法,于是書寫此聯懸掛于諸葛亮殿前,以便岑春煊第二年開春在武侯祠祭禮時能看到,并及時醒悟。沒想到,岑春煊看到對聯后,反而心生懊惱,趙藩也被撤了職。岑春煊死守鎮壓的辦法,終于引起了人民的不滿,且觸怒了清廷貴戚,結果受誣而被削職為民,岑春煊這才悟出趙藩這幅對聯的精髓所在。

成都武侯祠“名垂宇宙”匾額及“攻心對聯” 。
1972年3月,中央任命劉興元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臨行前,毛澤東在中南海與劉興元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中,毛澤東囑咐劉興元要到武侯祠讀一讀諸葛亮殿前的那幅對聯,意在提醒劉興元在上任后的工作中要注意多學習借鑒歷史上好的政治軍事思想。毛澤東這次談話距1958年的成都會議已經足足14年,可見毛澤東對這幅對聯的印象之深。
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
1958年3月6日下午,毛澤東還提出要去一趟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門外的浣花溪畔,是我國唐代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公元759年冬天,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入蜀,在成都建茅屋而居。杜甫在此居住近4年,創作了大量詩歌,流傳至今的就有247余首,其中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更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首千古絕唱。杜甫草堂是有關杜甫平生創作館藏最豐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圣地”。
到了杜甫草堂,毛澤東看得很仔細,他跨過石橋,又穿過一座高朗明亮的通堂式敞廳。在敞廳里,毛澤東還饒有興趣地觀看了歷代不同版本的杜甫詩集。進入草堂大廨后,毛澤東在一處平盤上坐了一會,吸了一支煙,四下環顧廳堂里的陳列,忽然有一幅對聯吸引了毛澤東的注意力,他起身走到對聯前,細細品讀起來,“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毛澤東隨即對身邊的陪同人員說道:“是集杜句。好聯!”
這幅對聯由清代顧復初(1800-1893年)題寫。顧復初是江蘇長洲(今屬蘇州)人,清代貢生,于咸豐末年應四川督學使何紹基之邀來到四川,后歷任四川總督吳棠、丁寶楨、劉秉璋、成都將軍完顏崇實幕僚。顧復初善于文章、詩詞、楹聯和書畫等,才情稟賦極高。顧復初崇仰杜甫,在寓居成都期間拜謁了杜甫草堂,并撰書此聯。上聯中的“異代不同時”引用杜甫詩《詠懷古跡》中的“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句,所以毛澤東說這是“是集杜句”。整幅對聯氣勢豪放,深沉勃郁,作者顧復初在34個字中概述了杜甫的遭遇和功績,也道出了自己的遭遇和情懷。上下聯包含了作者在自負中自嘲,在自嘲中又完成了對杜甫滄桑經歷和詩書成就的評述,因而脫離了簡單頌揚功德的窠臼,也脫離了因自負而生抱怨的酸腐老套,使得對聯整個格調高逸而含蓄典雅,是一幅佳聯,這也是毛澤東贊嘆這幅對聯是“好聯”的原因。
這幅對聯引起了毛澤東對對聯的濃厚興趣,第二天,毛澤東即專門派人來此借閱了楹聯書10余種,在成都會議閑暇之余就翻看這些楹聯。
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成都還有一幅對聯被毛澤東引用過,這幅對聯就是成都市新都寶光寺的名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寶光寺坐落于成都市新都區內,是我國南方“四大佛教叢林”之一,始建于東漢,歷經戰火,幾度重修,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寶光寺內被毛澤東引用過的對聯由清代名士何元普題寫。何元普是成都市金堂縣人,生于1829年,咸豐初年考取秀才為廩生,后授戶部員外郎為六部司副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何元普以戶部郎中投軍,抗擊英法聯軍的入侵。1871年,何元普因與其他人政見不一辭職回到金堂縣,從事著述,經常與新都龍藏寺雪堂和尚談禪論詩,使自己的禪學修養日益精深。1888年,何元普為新都寶光寺大雄寶殿撰書的“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一聯廣為流傳,成為天下名聯。
何元普天資極高,加上一生從書生到文官,從文官到抗擊外敵的將領,從將領到地方大員,從地方大員辭職從事文學,后又接觸禪學,因而對于世事看的更為通透,對于不同職業和職位的處事方法及心態轉換更為通達。基于這些因素,何元普才在老年寫下此聯,這幅對聯將禪機智慧和樸素辯證法很好地結合了起來,使得原本晦澀難懂的禪學智慧演變為容易理解的哲學思想語句。上聯指出,超脫世俗的人知道所謂的法則是變化無常的,沒有固定不變的法則,然后知道沒有法則其實也是一種法則,有反對教條主義的意思;下聯意思是天下的事情看似了結,其實尚未了結,在時機還沒成熟前,何妨暫時把沒有了結看做了結了,有反對形而上學的意味。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明顯感覺這場運動已經失去控制,在無法提出一個安定團結的綱領和政治基礎的情況下,運動的走向極不明朗。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引用寶光寺的這幅對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來描述他對“文化大革命”后期無能為力卻又不失他一貫恢弘大氣的心態。
事實上,這幅對聯所闡發的思想和心態還體現在毛澤東對于黨和國家事業交班問題的思考上。從1976年5月起,毛澤東的病情不斷加重,身體十分衰弱,毛澤東在住地召見華國鋒等,對自己進行“蓋棺定論”,并談了交班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這個談話透出毛澤東內心悲涼的情緒。 (作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責編:張微微)
- 四川黨的建設的其它文章
- 《四川黨的建設》理事會員單位
- 地 標
——西充縣大力推進北部新城建設 - 民主生活會這樣開
- ——四川中藥產業發展一瞥">"無川藥不成方"
——四川中藥產業發展一瞥 - 以科技創新打造“西部哇谷”
——與嘉賓對話中國科技城的未來 - 科技興則民族興 科技強則國家強
——寫給2013中國科技城科技博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