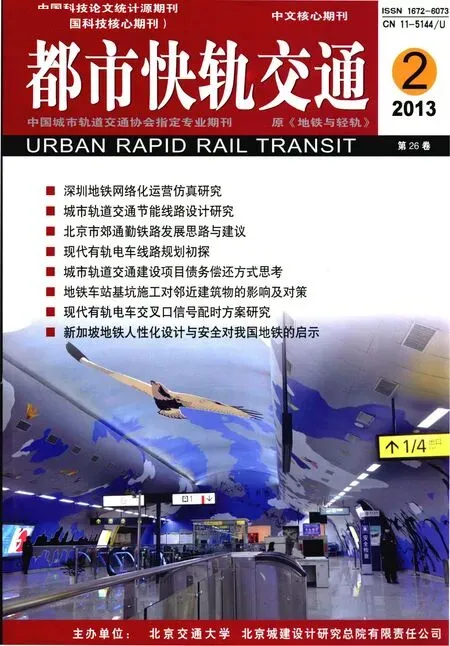地鐵客流預警技術基礎探討
李得偉 孫宇星 黃建玲
(1.北京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院 北京 100044;2.北京市交通委員會 北京 100161)
1 地鐵客流預警技術概況
我國城市軌道交通已經進入網絡化運營時代,截至2011年底,內地共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5個城市的運營線網規模超過3條線,其總里程達到1310 km,占已全部開通運營地鐵里程的76.43%[1]。已經成網的軌道交通共同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大規模的客流量,以北京地鐵為例,2012年9月6日的地鐵全網客流達到736.89人次,高峰時段有13個斷面的列車滿載率超過1.0,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動態監測地鐵內的客流,確保安全運行,成為地鐵運營的核心問題;二是出行路徑多元化,在網絡化條件下,乘客在起終點之間的路徑選擇出現多元化趨勢,如何通過科學的運輸組織手段,引導乘客出行,最終達到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盡可能均衡及效益最優,是地鐵運營部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
在這一背景下,2012年,北京市交通委組織開展了“軌道交通安全防范物聯網示范工程”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通過在北京地鐵布設物聯網感知設備,研究開發先進的客流動態監控、預警和誘導系統,為地鐵運營、應急等提供重要決策支持。本文結合該工程項目,針對其中的客流預警問題進行探索研究。該問題的研究成果,將對北京市地鐵物聯網工程提供依據,對國內其他城市的地鐵運營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指導作用。
目前,我國在地鐵客流預警這一領域的研究還不成熟,有關的量化標準尚未完全建立,既有客流預警的研究主要有上海世博會、西安地鐵、北京西客站[2-4]等特定場景大客流預警的經驗分析和手段探討,但絕大多數仍然是依靠人工經驗,方法還不系統。潘羅敏[5]等對地鐵客流預測方法進行了研究,并在預測基礎上進行預警,丁蕾[6]對南京地鐵換乘站的客流預警進行了一定理論研究。這些研究為人們深入了解地鐵客流預警提供了重要基礎,然而對結合實際的監測工程,以整個地鐵系統為研究對象、系統地開展地鐵預警研究的資料目前還很缺乏。筆者旨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預警的框架、提出地鐵預警指標體系,為北京市地鐵物聯網工程的應用提供技術支持。
2 地鐵客流預警的層次與框架
2.1 地鐵客流預警的涵義
有關地鐵客流預警尚無成熟的定義,結合國內外相關資料和實際工程經驗的總結,將地鐵客流預警的定義為: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監測或預測客流的關鍵指標,通過分析指標,并與設計或歷史經驗數據對比,預知異于常態的信息并通過圖形、聲音等多媒體信息方式呈現和報警,以期達到對決策管理人員進行提示和警告的技術。通過技術手段對區域進行直接監測并進行預警的技術是直接預警;通過數學計算、計算機模擬等方式計算、預測、推演等的預警則為間接預警。
地鐵客流預警按照預警的對象包含網絡預警、線路預警、車站預警和車站管理對象(設備設施)預警等4個層次,線路預警進一步可以分解為若干斷面預警組合。所有預警均可以歸結為列車預警和車站管理對象預警兩種基本類型,因為它們可以通過直接監測獲取對象上的客流數據,屬于直接預警,其他均為間接預警。以軌道交通安全防范物聯網示范工程為例,北京地鐵客流預警示例如圖1所示。

圖1 北京地鐵客流預警示例
地鐵客流預警按照預警目的,可以分為交通預警和安全預警;按照預警數據來源,可以分為實時預警和預測預警;按照預警報警值的參照標準,可以分為以設計標準為依據和以歷史同期值為依據的預警。采用不同類型的客流預警,其預警的目的、特點及適應條件都不同,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類型的地鐵客流預警對比分析
地鐵客流預警的技術流程如圖2所示。為了實現客流預警,首先需要在地鐵列車、車站等位置安裝視頻、激光等檢測設備,進行客流信息的采集,通過對有效信息的采集、編碼、傳輸、加工和抽取,綜合運用信息分析技術,獲取地鐵客流的檢測值如流量、密度、速度等;其次,根據預警目的構建客流預警指標體系,并利用客流的檢測值或預測值進行計算,劃分合適的預警標準,對客流狀態進行評估。將評估結果輸入決策支持系統,為運營部門提供客流疏導、行車組織、應急救援等方面的措施,同時利用乘客信息系統PIS向乘客發布誘導信息,進而影響客流分布;最后,通過客流信息采集對方案實施后的效果進行分析和評估。整個過程是一個閉環的過程。

圖2 地鐵客流預警技術流程
2.2 地鐵客流預警的級別
地鐵客流預警的級別劃分應以不同級別導致的客傷風險(用客傷事件發生概率表示)以及報警后應當采取的措施為依據,與已有的相關技術標準相統一,并滿足各級別之間易區分易記憶的要求。按照上海世博會、西安地鐵等客流預警的一般經驗,地鐵客流預警可以采取3級(紅、橙、黃)或4級(紅、橙、黃、綠)標準。
客流預警的定級標準因監控預警對象的不同而應有所區分。客流規模、客流擁擠的覆蓋范圍(一般用局部、大面積等表示)、客流滯留比例、客流流動速度等4個標準可以作為地鐵客流預警級別的劃分參考依據。對單個設備(如站臺)的預警可以用一個或若干個指示進行定級;對整體的預警(如車站)則需要不同設備和不同指標之間的配合,例如對于地鐵車站,盡管站臺擁擠程度一般,但站廳和進站通道的滯留超過一定標準時,該車站仍具有較高的擁擠風險,報警級別應適當提高。對于換乘車站,還需考慮上游車站的站臺客流狀態,當上游車站達到了一定級別的預警,換乘車站也應根據情況產生報警。
借鑒國內外客流預警相關的經驗,將地鐵客流預警級別劃分為4級,其中第4級為一般性預警,剩余3級為操作性預警,具體級別的判定標準則根據預警對象不同劃分。
2.2.1 車站客流預警的級別
車站客流預警級別主要根據進站口、站廳、站臺3級客流的總體狀態進行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地鐵車站客流預警建議級別
2.2.2 列車客流預警的級別
列車客流預警主要根據列車的滿載率作為依據進行級別劃分,考慮到實際運營情況,將列車預警劃分為4個級別,如表3所示。

表3 列車客流預警級別劃分
2.3 地鐵客流預警的監測位置
隨著監測技術的日益成熟,視頻、激光、紅外等監測技術已經被用于地鐵客流監測,既有的工程技術人員主要關注監測手段的先進性。實際上,監測地點的選擇同樣重要。根據以上客流預警的層次,確定監測位置。
1)對站內客流監測,監測地點主要包括出入口、站廳重點區域、站臺等候區、上行樓扶梯、自動售檢票機以及換乘通道始末端等位置。
2)對斷面客流監測,監測地點可以選擇列車上和車門處。
由于地下空間的結構問題,并不是以上所有的地點都適合安裝監測設備,此時應當注意運用科學的方法彌補盲點的客流狀態。
3 地鐵客流預警指標
地鐵客流預警指標的設計應考慮以下因素。
1)指標的設計應與預警的目的相結合,針對安全的預警和針對擁擠的預警指標應有所區別。
2)需要考慮指標計算所涉及的原始數據能夠通過設備方便采集和獲取,例如:利用AFC設備采集實時客流進行實時預警的做法雖然理論上可行,但由于數據海量、傳輸效果不穩定等原因,在技術上尚不可行。
3)需要結合既有的相關標準考慮指標閾值確定的可行性。如果既有的標準規范存在某類指標的極值建議標準,這類指標應當優先考慮。
3.1 指標體系
3.1.1 物聯網直接監測指標
對于客流,面向擁擠的監測指標主要是客流流量、速度、密度。單點地鐵客流物聯網設備可以直接檢測的值主要是瞬間客流密度,通過一定的技術處理可以獲得進入和離開檢測區域的客流流量。兩個激光監測設備同時連續布置于地鐵的通道等位置,可以監測到客流的流速值。此外,通過視頻設備的輔助,運用數字圖像處理技術,可以獲取客流中每個個體的行人軌跡,對踩踏事故視頻的研究發現,在極度擁擠條件下,踩踏事故發生前,擁擠人群中每個個體的頭部運動出現橫向運動,這是重要的踩踏征兆,通過獲取乘客軌跡,分析軌跡運動,可以作為面向安全的監測指標。
3.1.2 地鐵客流預警指標體系
根據地鐵客流預警的應用范圍、適應條件及指標的特征,將地鐵客流預警指標劃分為承載能力指標、設備能力指標、安全性指標和波動性指標4類。具體如表4所示。
1)承載能力指標屬于地鐵車站整體擁擠水平或安全水平的指標,它反映了地鐵車站的乘客聚集量,由于站臺上下車處監測困難,實際很難獲得準確的車站乘客聚集量,因此該指標適用于預測性預警。
2)設備能力指標反映了單個設備上的客流狀態,過高的密度、過低的速度均反映了客流的異常狀態,流量指標反映了單個設備的能力利用情況,對設備設施流量的監測,不僅要考慮入口斷面流量,還要考慮出口斷面流量,二者的差值可以反映設備的實際客流占用狀況。由于瞬間高密度和持續高密度對地鐵設備的影響有很大區別,因此,筆者亦將高密度持續時間作為監測指標,同時,該指標也能夠支持決策人員對瞬間高密度報警是否需要處置進行進一步確認。通行效率反映潛在的乘客擁擠,其定義是乘客實際速度與期望速度的比值,其取值范圍為[0,1],該值越接近1表明通行效率越高。

表4 地鐵客流預警指標及適應條件
3)安全性指標主要反映擁擠造成踩踏事故的可能性。在擁擠的人群中出現速度的突變,極易引起踩踏事故,這主要由速度變化率來描述。高密度輻射范圍則從擁擠的規模上反映了人群的安全性,大規模的高密度人群比小規模的高密度人群更易引起事故的發生。為了更加準確地監測踩踏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筆者借鑒德國社會學家Helbing提出的人群壓力[7]的概念,并將其引入到踩踏預警指標體系中,其基本定義如下:

式中,ρ(t)表示 t時刻監測區域的人群密度,vart()表示監測時段監測區域人流速度的方差,計算公式為vart()=[V(,t) - V()]2。
既有研究發現,當該值超過0.2人/s2時,人群中出現“湍流”現象;當達到0.4人/s2時,踩踏事故隨時有可能發生。
4)波動性指標反映了客流規模隨時間的變化情況,持續監測地鐵出入口等區域的密度變化率,可以比較準確及時地判斷突發大客流的產生,從而觸發突發大客流預警,這對啟動大客流預案,保證地鐵的安全運營具有重要意義。
3.2 地鐵客流預警閾值的建議
地鐵客流預警目前在國內外尚無公認的閾值定義。研究最為廣泛的是客流密度值,一般認為在通道內當密度接近或大于5人/m2時極易發生踩踏事故[8],因此,該值可以作為安全預警的重要依據。對擁擠預警,當通道內密度達到2人/m2時,人立即產生擁擠的感覺[9],筆者調研發現2人/m2作為擁擠預警的閾值是合理的。然而,由于車站內的地鐵客流屬于行人流預警的一個分支,因此,行人流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參考,由于不同國家、同一國家不同的發展時期所制定的劃分標準與指標不盡相同。如美國A級標準的行人空間同日本A級標準行人空間相差達3.7倍之多;美國1971年與1985年制定的標準也相差很大。因此,我國地鐵客流預警無法直接照搬國外的相關數據,在對地鐵車站不同設備上的客流進行大量基礎研究后,劃分了人行通道、樓扶梯、排隊區、檢票區、安檢區、站臺等設施的服務水平,確定了其實際的通過能力(小于設計通過能力[10]),可以為地鐵客流預警標準的制定提供參考,具體可見文獻[11]。實際上不同車站由于服務的人群不同,車站對下游車站的影響程度不同,預警的閾值不宜完全一致,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調研確定。
對于地鐵列車的客流預警,我國目前采用的地鐵車輛一般按照額定立席人數6人/m2計算,(超員)人數按8人/m2計[12],該值可以作為客流預警的參考依據。考慮到地鐵線路的行車間隔,可以比較容易地將其轉化為斷面能力預警指標。
4 結語
本文在北京市軌道交通物聯網工程的應用背景下,針對地鐵客流預警問題,從預警的層次、監測位置、預警指標體系及閾值建議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基礎性的探討。通過實踐得出如下結論:客流預警與服務水平不同,預警要從視頻、AFC、售票、激光等設備以及歷史數據庫等平臺多個方面收集大量信息;地鐵系統的預警宜組合分析預警,即充分考慮監測指標的組合和監測地點組合,否則容易發生虛報警;客流預警分級宜根據影響范圍、預警指標值等綜合確定;客流預警的閾值宜按照預警的目標慎重選擇,不同車站由于客流構成不同,對下游的影響不同,預警閾值不宜相同;預警宜按照實際采集值進行預警。地鐵客流預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不同專業的知識,應從預警的標準、執行和解除等方面開展專門研究。
[1]中國城市軌道交通研究年度報告課題組.中國城市軌道交通研究年度報告[R].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2]李彬.2010年上海世博園區大客流狀態下園外交通系統預警及應對方案[J].城市公共事業,2010,24(2):1-4.
[3]呂華.西安地鐵遇大客流將啟動預警機制保障安全[EB/OL].[2010-09-28].http://news.xiancn.com/content/2011-09/28/content_2493497.htm.
[4]劉曉琴,姚曉暉,龐雷.馬爾科夫鏈模型在鐵路春運客流預測中的應用[J].安全,2010(2):5-10.
[5]潘羅敏.地鐵短時客流量預測預警研究[D].北京:首都經貿大學,2011.
[6]丁蕾.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客流預警及應對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2.
[7]Helbing D,Johansson A.The dynamics of crowd disasters:an empirical study[J].Physical Review E,2007(75):1-7.
[8]Hughes R L.A continuum theory for the flow of pedestrian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Part B,2002(36):507-535.
[9]朱嶸.基于世博會人流組織的規劃用地構成與策略[J].規劃師,2006(7):43.
[10]GB 50157—2003地鐵設計規范[S].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3.
[11]李得偉,韓寶明.行人交通[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403-405.
[12]GB/T 7928—2003 車輛設計通用標準[S].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