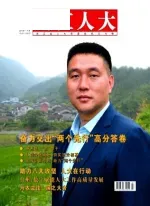法治的“秘密”
劉瑜
法治的“秘密”
劉瑜
所謂“法治”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來自于權力機構的價值自覺與實踐。民眾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機構本身的“素質”。
“為什么法院說什么,美國人都會照辦?”這個貌似天真的問題,問出了很多民眾的心聲。確實,美國憲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個法官,憑什么要聽從他們?
事實上,美國人對法院的遵從并非因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下,人們往往把總統看做隨民意而搖擺的民粹分子;而國會議員的形象,則是為了黨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只有法官,在人們的集體想象中往往代表著公正、超脫、冷靜。事實上美國的各種民調也顯示,最高法院的民眾支持率一般明顯高于總統和國會。因為,“美國的大法官不是選舉產生的,所以他們是抵抗多數暴政的堡壘”。
但美國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歷史和社會般地英明神勇嗎?事實似乎比這復雜得多。美國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過許多重大錯誤。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中,大法官判定黑奴德雷德·斯科特沒有公民權,被很多人視為美國內戰的導火索;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決種族隔離并不違憲,導致種族隔離政策延續了半個多世紀;1944年“是松訴美國案”中,法院判決羅斯福總統戰時“以集中營安置日裔美國人”的做法合憲,給美國憲政史留下一個巨大污點……凡此種種,足以將大法官們拉下“圣壇”。歷史上美國人也無數次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法院判決的不信任,大到美國內戰,小到層出不窮的對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戰,而正是這種不信任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憲政和法治的不斷完善。
人們可能會說,美國人聽從法院的決定,是因為他們有守法的習慣和文化,簡稱“人家素質高”。但是“素質”從何而來呢?現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解釋道:人民遵從法律,是因為他們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從何而來呢?民眾對權力機構的信任,如同戀人之間的信任,來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維系?
民眾對法院的信任,來自于法院捍衛憲法及其基本價值觀的實踐。讓我們來看下面這個案例。1952年,“楊斯頓鋼鐵公司訴索耶案”中,法院裁決美國總統杜魯門為了應對韓戰而將私人鋼鐵企業收歸國有的做法違憲,從而維護了私有產權。小布什時代的關塔那摩案,則彰顯了最高法院如何“處處”和總統“作對”,以維護關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權利……最高法院將捍衛憲法所保護的個人權利、自由和平等視為己任,由此獲得了民眾的信任。換言之,人們聽從法院,是因為它在源源不斷地提供合乎人們價值體系的“公共善”。
由此可見,“法治”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來自于權力機構的價值自覺與實踐。民眾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機構本身的“素質”。
獲得民眾的信任并非一勞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決中背叛了美國憲法的最基本價值觀,沒有對這些價值觀進行與時俱進的適應性詮釋,或者在憲法所追求的不同價值觀之間沒有實現微妙的平衡,民眾的信任和服從很可能隨風而去。這大約是美國法官們工作的艱難之處:他們永遠在如履薄冰,永遠在風口浪尖。但這大約是他們的工作充滿魅力之處:他們需要不斷運用智慧化險為夷。他們像童話中的精靈,用一根神奇的指揮棒,讓民眾信任法院,敬畏法律。
美國人民遵從法律,是因為他們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從何而來呢?民眾對權力機構的信任,又如何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