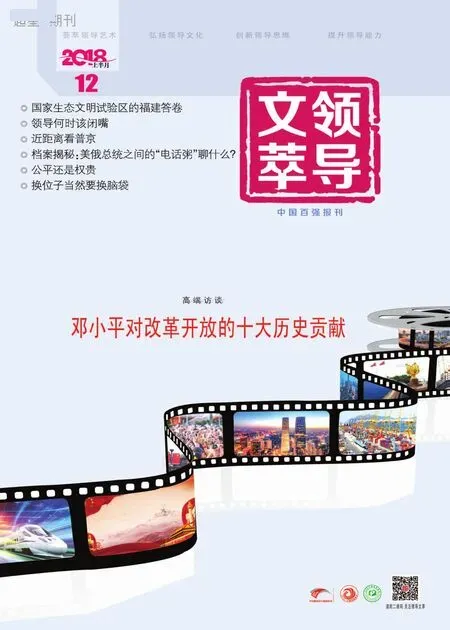傅高義眼里的鄧小平
□朱又可
“鄧小平的貢獻在于他成功控制了開放的進程。”2012年1月18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在完成了900頁的《鄧小平》后,花了10年時間寫作的《鄧小平》(《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該獎授予最佳英語外國事務非虛構著作。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1961年開始在哈佛學習中文和中古歷史,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1972年他作為費正清的繼任人,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選入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成為美國最有名望的“中國通”之前,傅高義首先是個“廣東通”。傅高義寫過兩本關于廣東的書:《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和《先行一步》。
傅高義自費采訪以保證獨立性,從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義在廣東實地調查70多個縣,1988年夏季,他又調查三周,1988年底脫稿。《先行一步》是外國學者研究、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書。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多克·巴涅特評論:“這本書描繪了鄧小平時代所邁出的冒險的一步”。
沒有用保密的情報
2000年,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傅高義認為當時是研究鄧小平的最佳時間。因為很多基本的年譜材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很多回憶錄已經出版,此外,他還有后來的歷史學家無法利用的機會:他能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交談。
雖然有關于中國的兩本書墊底,但寫鄧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鄧小平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記憶力。“文革”期間批判鄧小平的人想搜集他犯錯的文字記錄,結果一無所獲。鄧小平的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這是研究鄧的學者都會遇到的一個挑戰。
傅高義唯一遺憾的是他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交談。他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業界的中國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當時他離鄧小平只有幾步之遙。
傅高義知道有人認為鄧小平 “獨斷專行”,“但故事的另一面,他讓一個貧窮受苦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國家,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帶領中國與世界接軌。所以想要公平地看鄧的貢獻,就需要公正地看待他的強硬。我很難想出在20世紀還有其他領導人像鄧小平一樣為如此多的人做出了如此多的貢獻。”
傅高義認為最有助于理解鄧小平復出前他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榕(毛毛)寫的兩本書:《我的父親鄧小平》和《鄧小平:“文革”歲月》。“她在書中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傅高義說,子女對父親通常都會“說好話”,他得在不同講述人對同一事件的記述中加以比較。
研究鄧小平的英文版著作為傅高義提供了很好的起點。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斯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鄧小平和現代中國的形成》一書,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歷。
理查德·鮑姆的《安葬毛澤東》(Burying Mao)利用了1994年之前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傅高義則極少使用香港的報道,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
面對浩如煙海的資料,傅高義慶幸有兩位得力助手,一位是任意——任仲夷的孫子,另一位是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們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專門收集大量材料。
傅高義閱讀了大量的回憶錄,包括鄧力群、胡績偉、楊繼繩、宗鳳鳴等人出版的著作。他也觀看過記錄鄧小平的講話、會見各種人物、出訪各地以及和家人休閑的紀錄片。助手甚至還按他的要求翻譯了俄語文獻。
“很多中國領導人與客人坐在并排擺放的沙發上會談時都是目光直視,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來注視與他交談的人。”傅高義善于發現各種細節。
傅高義采訪過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和鄧琳、陳云的子女陳元和陳偉立、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長達兩百多人的采訪名單還包括江澤民、李銳、錢其琛、任仲夷等中國高層領導;也包括與鄧小平有關的世界政壇領袖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吳作棟,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霍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前副總統沃爾特·蒙戴爾、前國務卿基辛格等等。
雖然傅高義在1993年到1995年擔任過與東亞有關的美國國家情報官員,但他保證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沒有利用保密資料。
鄧小平像個總司令
“鄧小平的作息很有規律。他8點在家吃早餐,9點去辦公室。他的妻子卓琳和秘書王瑞林為他準備好閱讀材料,包括大約15份報紙、從外國媒體翻譯的參考資料、一大堆來自各部委和各省黨委書記的報告、新華社搜集的內部報道以及送交他批準的文件草稿。為了解最新動向,鄧小平主要依靠書記處整理的情況匯總。文件在上午10點前送到他辦公室,他當天就會批復。他不在辦公室留下紙屑,這里總是干凈整潔。”《鄧小平》讀來如同小說,當然所根據的材料相當可靠。
“強勢、堅定、有條理。”2012年1月18日,傅高義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用了三個詞來形容鄧小平。
傅高義把鄧小平與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以及毛澤東相提并論。與他們相比,鄧小平“將完成近200年來中國所要實現的使命,即找到一條中國的富強之路”。
“在1979年1月的華盛頓國宴上,雪莉·麥克雷恩對他說,有一個‘文革’期間被下放的知識分子,很感謝自己在下放農村種西紅柿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后向她講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在傅高義看來,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時代:“鄧小平像個總司令,他細心地監督著自己的作戰計劃得到正確部署和落實。”傅高義注意到,和毛不同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上從不擺放鄧小平的塑像”,“人們的家里也幾乎見不到他的畫像,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也很少。鄧小平從未成為黨的主席,學生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理論’,引用他的一些著名格言,但是他們并不花時間背他的語錄”。
“鄧小平最后一次公開露面是1994年春節。此后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再也沒有力氣參加會議了。他于1997年2月19日午夜后去世,享年92歲,死因是帕金森氏綜合征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簡單樸素。毛澤東的遺體經過處理后被擺放在專門建立的毛主席紀念堂供人瞻仰,但沒有人為鄧小平建紀念堂。2月25日,大約一萬名黨員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江澤民強忍著淚水念完悼詞。追悼會在電視上做了直播,有關鄧小平生平的報道在此后數天一直是媒體的主題。按照鄧小平的遺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被捐出供醫學研究,遺體被火化,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共黨旗。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傅高義說:“就像一個成立了公司并掌管這個公司的人,鄧小平開創了一場革命,他考慮到了建立一個機制所需的所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