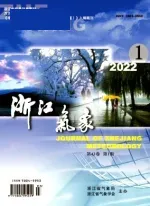氣候變化背景下醫療氣象研究綜述
梁曉妮 駱月珍 雷俊
(浙江省氣象服務中心,浙江杭州310017)
0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全球氣候正在發生變化,而大部分變暖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經濟的飛速發展,極大依賴于化石燃料的燃燒,而這將導致溫室氣體的大量釋放。在過去的100年中,中國也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正經歷著顯著的氣候變化。
以氣候變暖為主要特征和趨勢的全球氣候變化正在加劇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氣候事件本身可直接危害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生態環境變化可能產生更為廣泛的適合媒介生物及病原體孳生的環境,引起疾病分布范圍的擴大和流行強度的增強,加劇傳染病的傳播。氣候變化也可能引起大范圍的極端天氣事件,包括臺風、洪水、暴風雪、風暴、干旱和山體滑坡。已有數據表明,世界范圍內的許多地區,日死亡的增加與極端氣候變化有關。WHO(世界衛生組織)估測在最近的30年中有超過15萬的死亡病例以及500萬疾病而導致的傷殘人士都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近年來,國內外對氣候變化對人類疾病的影響的研究進行概括綜述,一方面指出氣候變化下極端氣候事件對疾病的發生和死亡將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在意識到了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負面作用之后,介紹了國際上進行的對人類未來熱引起的疾病死亡率的預測計劃,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以及其對人類疾病的影響的認識,為今后醫療氣象的研究提供參考。
1 極端氣候事件對疾病的影響研究
對氣候均值的偏離都幾乎必然影響到熱浪和暴雨等極端氣候現象的頻率,在氣候變暖背景下,熱浪、風暴、洪水、干旱、極寒天氣等極端氣候事件會通過各種方式對人類健康造成影響,另外臭氧層破壞、空氣污染加劇等間接因素也共同威脅著人類的健康。
1.1 高溫熱浪與疾病
大量文獻表明溫度的增加會增加與天氣相關疾病的發病率以及死亡率。Knowlton等研究發現,極端氣溫主要是引起心腦血管和呼吸疾病導致的死亡,尤其是對于老年人[1]。McMichael等人的研究表明,對于那些最熱的月份,氣溫超過30℃的地區,氣溫每升高1℃,就會增加3%的死亡率。Basu R等的研究指出,在北美,一天內大約每4.7℃的增溫,就對應著2.6%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增加,對于心臟方面的疾病也有同樣的危險[2]。
Rogot E等認為高溫能引起生理上深刻的變化,如血液粘性和心輸出量的增加,這些將導致脫水、低血壓,甚至是內皮細胞的壞死[3]。Ockene等的臨床試驗表明,在高溫下,血液粘性和血清膽固醇水平升高[4]。Tsai等認為高溫會加速冠狀動脈疾病和腦血管的梗塞[5]。Flynn A的研究表明,在高溫期間,導致死亡最可能的原因是血栓栓塞疾病和嚴重的心律不齊以及熱引起的休克等[6]。
總之,未來氣候變化只會加劇高溫熱浪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一點已經獲得了普遍的認識,然而在氣候變得更加極端之前,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高溫對疾病的影響途徑和機制,以便人們更好的應對。
1.2 極端低溫與疾病
寒冷、低溫等氣候異常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也越來越引起研究人員的重視。Spencer FA等的研究發現,在冬天,急性心肌衰弱侵害的發生比在夏天增加了53%[7]。Morabito M指出,當日平均氣溫低于26.2℃,急性冠狀病綜合征增加30%~70%。如果日平均氣溫降低,那么每天的心血管疾病病人都會增加(降低10℃,將會在65歲以上人群中增加19%的心血管發病率)[8]。Danet等的研究表明,氣溫降低10℃,將引起冠狀疾病發生率增加13%,伴隨癥狀以及冠狀病死亡增加11%,同時增加26%的復發率[9]。
大量試驗試圖找出冷應激如何引起人體生理變化,從而認識和預防寒冷、低溫對人類健康產生的影響。Argiles A等的研究表明,血液的平均收縮壓和舒張壓在冬天最高在夏天最低[10]。Keatinge WR發現冷應激會引起血壓增加、交感神經活動頻繁以及血小板的聚集[11]。冷能引起血壓的增加,這歸因于心輸出量的增加,Cui J為證明這一結論所做的試驗表明,冷應激首先是導致肌肉交感神經系統活動的增加,而接下來是人體提升外部抵抗力活動的增加[12]。The Eurowinter Group 針對歐洲人的試驗則表明,冷能引起心跳加速,全身血管阻力的增加,血漿腎上腺素、血管收縮神經縮氨酸水平以及血壓的增加[13]。Nabel EG等發現,在冷加壓試驗中,冠狀動脈粥樣硬化被證明與冷有關的交感神經變化相關,潛在的改變了心肌需氧量和供氧量之間的平衡[14]。激光多普勒血流儀[15]、體積描記器[16]和手指皮膚溫度等都證實了冷能引起皮膚組織的血管收縮[17]。
世界范圍內,快速積累的溫室氣體,不僅使平均溫度增加,也增加了溫度的變化。這一變化迫使人們要更好的認清極端氣溫對健康的影響,包括熱浪和寒冷。
1.3 大氣污染與疾病
現有對大氣污染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的認識,有人認為其對溫度-死亡率之間的關系有影響,有人卻認為是干擾因素。Medina-Ramon等和Ren等的研究認為大氣污染是溫度和死亡率之間關系的干擾項[18-19],而Basu等和Zanobetti等的研究則認為沒有證據證明其干擾作用,大氣污染和溫度對死亡率的影響基本相互獨立[20-21]。
Jiminez-Conde等的一項針對婦女的研究顯示增加粒子濃度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直徑小于2.5μm的粒子每增加10μg/m3,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比率將增加1.24[22]。在低空氣污染的赫爾辛基地區,也發生同樣的影響,這說明極端精細的粒子(直徑小于0.1μm)會增加中風死亡的風險[23]。Lin C等考察了中風住院病例與幾種污染物之間的關系,發現直徑小于10μm的懸浮粒子和二氧化硫各自獨立的負面影響。而其它污染物對腦血管和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影響,僅有二氧化碳的影響達到了統計學上的意義[24]。
而Qian Z等發現,在因炎熱的夏季而被稱為“火爐”的武漢,高溫會增強PM10對心肺疾病的影響,盡管在高溫期PM10濃度比在正常的或低溫期更低[25]。而一些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則會受到溫度的影響,如臭氧的濃度在熱天是增加的。Zhang Y等的流行病學研究還證明臭氧危害也與溫度增加有關[26]。總而言之,大氣污染對人類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但是其中的影響機制還不明確,通過現有的數據還很難得出結論。
由于氣候變化,城市的大氣污染很可能增加,因此未來城市人口將更多的暴露在高溫和大氣污染中[27]。大氣污染(如臭氧)的增加和極端高溫事件經常同時發生,未來因熱引起的死亡的原因不僅表現為溫度的作用,也很可能是因為間接的原因,如溫度升高引起的臭氧的增加,或者是高溫和大氣污染的協同作用[28]。因此有必要去認識高溫和大氣污染對死亡的任何可能的共同作用,而不僅僅是溫度的作用[29]。
2 氣候變化與疾病死亡率預測研究
2.1 預測疾病死亡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IPCC 報告指出炎熱的天氣在未來可能導致更多的與熱有關的死亡率。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的城市,由于城市熱島效應的影響,粗劣的城市設計和規劃,以及空氣污染和熱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人口更易受到全球變暖的影響。
各種研究試驗方法被用于證明溫度對死亡率的影響,包括描述、病例對照、病例交叉,時間序列法,空間和天氣圖方法。一般而言,時間序列和病例交叉方法對于研究溫度-死亡率之間單一的或多重的關系方面較為有效。
許多研究證明了高溫和死亡率之間的關系,然而需要更多的對于未來氣候變化對死亡率的影響的研究。在未來氣候不確的背景下,情景預測作為主要的方法用于政府決策和計劃。IPCC在排放情景特別報告中提出一系列的未來氣候情景(SRES)[30]。這些情景沒有賦予概率值,因而都被認為是未來可能的情景,其區別基于人口、技術、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30]。這些情景不僅用于更好的預測未來,而且能更好的理解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從而幫助決策者在一系列可能的未來情境下得出更好的結論。
大量的方法被應用于預測未來氣候變化下的與熱有關的死亡率。盡管每一種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卻提供了在氣候變化情景下預測熱引起的死亡率的可能。預測熱引起的死亡率要求分析歷史的溫度-死亡率關系函數,同時需要考慮未來氣候、人口和氣候適應性的變化。一些研究人員已經在不同的氣候變化情境下預測了熱引起的死亡率,在不同的排放情景下預測死亡率有很大的不同,表明溫室氣體減緩政策對保護人類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盡管預測方法仍處于初期且存在局限,基于證據的未來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評估顯得尤為緊迫。
盡管未來氣候變化的程度仍有不確定性,然而,氣候模擬實驗認為未來的熱浪將更經常的發生,且強度更強、持續得更久。考慮到我們對未來人口對熱的敏感性的認識仍不明確,因此利用各種方法得到氣候變化對健康的最合理的影響就顯得很重要。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提供更強的與熱有關的死亡的理論框架,包括對社會經濟發展、土地使用情況、空氣污染和改善戰略的更好的認識。
2.2 預測氣候變化下的疾病死亡率需要考慮的問題
2.2.1 溫度指標的選擇
預測未來死亡率基于歷史的溫度和死亡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其被應用于氣候變化模式和排放情景,去評估未來熱引起的死亡率。因此,選擇哪一個溫度量作為預測死亡率的最好的指標是很重要的。
日最高氣溫和平均氣溫常被用來衡量熱的程度。也有使用復合指數的,這樣能夠考察外界的溫度、濕度和其它氣象要素的綜合作用。例如,天氣學方法就是基于氣團的研究方法,用于量化天氣和露點溫度、風速、云量、氣壓以及其它要素之間的關系。表觀溫度和溫濕指數就反應了溫度和濕度的共同作用。Kalkstein和Greene利用空間天氣學方法評估美國的氣候-死亡率之間的關系[31]。Hayhoe等認為在加利福尼亞,最高溫度的臨界值與熱引起的死亡率升高有關[32]。Barnett等人試圖證明溫度的哪一個衡量方法對預測死亡率是最優的。他們比較了7個溫度值:最高、平均和最低溫;最高、平均和最低表觀溫度以及溫濕指數,資料來源是美國107個城市的1987—2000年的日資料。結果表明沒有哪一個指標更優。這些值之間的高相關性表明它們對死亡率的預報能力基本相同。因此,可根據實際需要選擇合適的溫度衡量方法,如使用平均溫度,這在氣候模式中比較普遍[33]。
選擇研究溫度-死亡率的時間段也是很重要的。對于同一個城市而言,溫度-死亡率之間的關系在1960年代和2000年代的表現就不一樣。原因可能是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統計信息的變化和人類氣候適應性的不同。由于日死亡數據在許多城市里沒有早于1990年的,因此1996—2005年,以2000年為中心的這一時間段,被認為可用于作為基本的研究時間。
2.2.2 未來氣候情景的選擇
未來氣候狀況的模擬也是預測未來疾病死亡率的重要問題之一。IPCC定義的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的情景主要分為4組:第1組(A1)代表快速的經濟增長,全球人口達到頂峰,以及高效的新技術的應用,其中又分為3個分組,分別是很強的燃料排放組(A1FI)、無燃料排放組(A1T)和平衡組(A1B);第2組(A2)代表高速的人口增長,低速的經濟和技術發展;第3組(B1)代表的人口狀況與第一組一致,而高速發展的是服務和信息經濟;第4組(B2)代表了人口和經濟增長的中間型,并保持區域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不同的大氣環流模式,上述情景可以模擬未來的氣候。由于不同的大氣環流模式有不同的優勢和缺點,IPCC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環流模式是最好的。因此選擇合適的氣候模式也是很重要的[34]。
氣候變化情景將決定預測熱引起的死亡率的大小。因此,在影響評估時應考慮不同的排放情景,提供一系列的未來氣候和健康之間的可能的影響關系。這些不確定的關系也在英國的氣候實驗中得到證實,實驗使用了高、中和低的排放情景,這也與IPCC所述的第1組的第1分組(A1FI)、第1組的第3分組(A1B)和第3組(B1)情景相對應。
2.2.3 人類氣候適應性的變化
氣候適應性是人體適應他們所處的環境的生理調節過程。在更暖和的地區,溫度的臨界值趨向于更高,這反應了氣候適應性的作用。Balloux等認為,生活在較寒冷地區的人,線粒體多樣性水平較低,同時發現,生活在不同溫度下的人們的基因也存在差異[35]。這些研究表明氣候決定的自然選擇結果導致形成了目前人類線粒體基因組序列的分布。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通過增加使用空調、減少運動、改善房屋設計和城市規劃,都能夠逐漸適應極端高溫天氣。隨著時間推移,人類可能適應日益升高的氣溫,這也是影響死亡率研究的問題之一。
因此,氣候變化導致基因多態性的變化以及因此導致的人類對氣候的適應性的改變,從而對人類疾病發生率和死亡率產生影響,它們之間如何發生聯系以及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定論,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有研究者綜合考慮氣候適應性的變化進行溫度-死亡關系的研究。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在相似的城市中使用暴露-反應曲線進行試驗,利用所選擇的相似的城市現在的氣候狀況,能夠最接近的反映和模擬出目標城市未來的氣候狀況。例如,Knowlon等模擬紐約的氣候適應性,則是利用由華盛頓、亞特蘭大和佐治亞州1973—1994年的平均夏季氣溫推導的溫度-死亡率反應公式來反映紐約2050年代的溫度和疾病狀況[36]。另一個方法是在目標城市中選擇相似的夏季來模擬氣候適應性,Hayhoe等研究未來氣候適應性依據歷史上記錄的最熱的夏季中的溫度-死亡率關系來進行[37]。
3 結語
總之,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氣候變化威脅著人類的健康。未來的研究應該提供適應氣候變化的方法,改善氣候-健康關系特征。基于國內外大量的對氣候變化下醫療氣象研究的結論,我們發現氣候均值的偏離必然導致極端氣候事件的增加,在氣候變化和更大的氣溫的極端變化下,這種影響只會加強而不是減弱。研究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研究極端氣候事件對人類疾病的影響途徑和機制,同時,大量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對亞人群(如老人和小孩)的影響更大,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城市熱島效應和空氣污染的加劇,使得城市人口成為氣候變化下的易感人群和脆弱人群,針對不同人群特征(如年齡、性別、是否有疾病史等)展開研究可以更精確的確定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另外,大氣污染與氣候變化,尤其是高溫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它們對疾病的影響究竟是相互獨立還是協同的作用是未來研究的課題之一,而大氣環流模式的發展和未來氣候情景的確定為醫療氣象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在氣候變化與人體健康科研和業務方面,目前我國尚存在很大的不足,如基本數據獲得困難,衛生信息系統不健全,防治措施滯后等等。此外,我國現有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是氣象條件對疾病影響方面的,極少是嚴格意義上的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研究。今后在開展氣候變化與人類健康的研究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確認溫度對疾病影響的臨界點。熱對健康的影響可利用溫度的臨界值和曲線的斜率表示。溫度-死亡率常常表現為非線性的U、V或J型,即當氣溫低于或高于某一臨界溫度時,隨著溫度的降低或升高,某一類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逐漸升高[38-39]。確定某一疾病的溫度臨界值,即熱的危害開始出現的溫度,對疾病預防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
2)研究不同人群適應氣候變化的比較研究。開展針對亞人群(如老年人和兒童)以及易感人群和脆弱人群的研究,為特定人群制訂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提供依據。
3)建立健全健康疾病登記或數據收集系統。在許多發達國家,疾病發病和死亡的登記系統較為健全,為疾病的發生、變化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保障。收集和加強監控可能影響健康的數據,如極端氣溫導致的死亡率、極端天氣事件影響的媒介傳播疾病、空氣質量、花粉和霉菌數量、經食物和水傳染的疾病和精神疾病等是未來開展疾病研究的基礎。
4)開發建立氣候變化與人體健康早期預警系統和應急預案等相應的適應技術。如果人們想要有效的減少因氣候變化導致的死亡,那么這些研究對于能夠在更極端的氣候變化到來之前制定計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很重要的。
5)加強大氣污染與氣候變化之間關系的研究。環境和大氣污染問題日益突出,而其與氣候變化,尤其是高溫熱浪之間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共同的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在加速城市化和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大氣污染和城市熱島效應將使城市人口受到更大的威脅,因此,有必要加強大氣污染與氣候變化以及它們對疾病的影響研究。
[1] Knowlton K,Rotkin-Ellman M,King G,et al.The 2006 california heat wave:impacts on hospitalization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J].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9,117:61-7.
[2] Basu R,Ostro BD.A multicounty analysis identifying the populations vulnerable to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high ambient temperature in California[J].Am J Epidemiol,2008,168:632-7.
[3] Rogot E,Sorlie PD,Backlund E.Air-conditioning and mortality in hot weather[J].Am J Epidemiol,1992,136:106-16.
[4] Ockene IS,Chiriboga DE,Stanek 3rd EJ,et al.Seasonal variation i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treatment implications and possible mechanisms[J].Arch Intern Med,2004,164:863-70.
[5] Tsai SS,Goggins WB,Chiu HF,Yang CY.Evidence for an association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daily stroke admissions in Kaohsiung,Taiwan[J].Stroke,2003,34:2612 -6.
[6] Flynn A,McGreevy C,Mulkerrin EC.Why do older patients die in a heat wave?[J].QJM,2005,98:227 -9.
[7] Spencer FA,Goldberg RJ,Becker RC,Gore JM.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second National Registry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J].JAm Coll Cardiol,1998,31:1226 -33.
[8] Morabito M,Modesti PA,Cecchi L,et al.Relationships between weather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a biometeorological approach[J].Int J Cardiol,2005,105:288 - 93.
[9] Danet S,Richard F,Montaye M,et al.Unhealthy effects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n the occurrence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oronary deaths:a 10-year survey:th Lill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ONICA project(Monitoring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J].Circulation,1999,100:1 -7.
[10] Argiles A,Mourad G,Mion C.Seasonal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treated with hemodialysis[J].N Engl J Med,1998,339:1364 - 70.
[11] Keatinge WR,Coleshaw SR,Cotter F,Mattock M,Murphy M,Chelliah R.Increases in platelet and red cell count,blood viscosity and arterial pressure during mild surface cooling:factors in mortality from coronary and cerebral thrombosis in winter[J].Br Med J,1984,289:1405 -8.
[12] Cui J,Wilson TE,Crandall CG,Baroreflex modulation of muscle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during cold pressor test in humans[J].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2002,282:H1717-23.
[13] The Eurowinter Group .Cold exposure and winter mortality from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respiratory disease,and all causes in warm and cold regions of Europe[J].Lancet,1997,349:1341 -6
[14] Nabel EG,Ganz P,Gordon JB,Alexander RW,Selwyn AP.Dilation of normal and constric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oronary arteries caused by the cold pressor test[J].Circulation,1988,77:43 -52.
[15] ThomasJR,Shurtleff D,Schrot J,Ahlers ST.Cold-induced perturbation of cutaneous blood flow in the rat tail:a model of nonfreezing cold injury[J].Microvasc Res,1994,47:166-76
[16] Johnson JM,Taylor WF,Shepherd AP,Park MK.Laser-Doppler measurement of skin blood flow:comparison with plethysmography[J].JAppl Physiol 1984,56:798 -803.
[17] Ducharme MB,Vanhelder WP,Radomski MW.Cyclic intramuscular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in the human forearm during cold-water immersion[J].Eur JAppl Physiol Occup Physiol,1991,63:188 - 93.
[18] Medina-Ramon M,Schwartz J.Temperature,temperature extremes,and mortality:a study of acclimatisation and effect modification in 50 US cities[J].Occup Environ Med,2007,64(12):827 -833.
[19] Ren C,Williams GM,Tong S.Does particulate matter modif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cardiorespiratory diseases?[J].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6,114:1690-1696.
[20] BasuR,Feng W,Ostro B.Characterizing temperature and mortality in nine California counties[J].Epidemiology,2008,19(1):138 -145.
[21] Zanobetti A,Schwartz J.Temperature and mortality in nine UScities[J].Epidemiology,2008,19(4):563 -570.
[22] Jiminez-Conde J,Ois A,Gomis M et al.Weather as a trigger of stroke.Dail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incidence of stroke subtypes[J].Cerebrovasc.Dis,2008,26:348-354.
[23] Kettunen J,Lanki T,Tiittanen Pet al.Associations of fine and ultrafine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s with stroke mortality in an area of low air pollution levels[J].Stroke,2007,38:918-922.
[24] Lin C,Amador Pereira L,de Souza Conceicao G,Kishi H,Milani R,Ferreira Braga A 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ischaemic cardiovascular emergency room visits[J].Environ.Res,2003,92:57 - 63.
[25] Qian Z,He Q,Lin HM,Kong L,Bentley CM,Liu W,etal.High temperatures enhanced acute mortality effects of ambient particle pollution in the“oven”city of Wuhan,China[J].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8,116:1172-1178.
[26] ZhangY,Huang W,London SJ,Song G,Chen G,Jiang L,et al.Ozone and daily mortality in Shanghai,China[J].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6,114:1227 -1232.
[27] MS,Ebi KL.Temperature extremes and health: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J].J Occup Environ Med,2009,51(1):13 -25.
[28] Barnett AG,Hansen CA.How might the health effects Projections of future heat-related mortality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of air pollution change when the planet gets warmer?In:Climate Change,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Catastrophes:Fears and Concerns for the Future(GowKM,ed)[M].2009,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137 - 155.
[29] WHO.2009a.Improving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Extreme Weather Heat-Waves EuroHEAT[M].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30] Nakicenovic N,Davidson O,Davis G,Grübler A,Kram T,RovereELL,etal.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A Speci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of the IPCC[M].20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 Kalkstein L,Greene J.An evaluation of climate/mortality relationships in large U.S.cities and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a climate change[J].Environ Health Perspect,1997,105:84-93.
[32] Hayhoe K,Cayan D,Field CB,Frumhoff PC,Maurer EP,MillerNL,etal.Emissions pathways,climate change,and impacts on California[J].Proc Natl Acad Sci U SA,2004,101(34):12422-12427.
[33] AG,Tong S,Clements ACA.What measure of temperature is the best predictor of mortality?[J].Environ Res,2010,110(6):604-611.
[34] IPCC.2007b.Climate Change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 Balloux F,Handley LJ,Jombart T,Liu H,Manica A.Climate shaped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variation[J].Proc Biol Soc,2009,276:3447-55.
[36] Knowlton K,Lynn B,Goldberg RA,Rosenzweig C,Hogrefe C,Rosenthal JK,et al.Projecting heat-related mortality impacts under a changing climate in the New York City region[J].Am J Public Health,2007,97(11):2028-2034.
[37] Hayhoe K,Cayan D,Field CB,Frumhoff PC,Maurer EP,MillerNL,et al.Emissions pathways,climate change,and impacts on California[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04,101(34):12422 -12427
[38] Keatinge WR,Coleshaw SRK,Cotter F,et a1.Increases in plate-1et and red cell counts,blood viscosity,and arterial pressure during mild surface cooling:factors in mortality from coronary and cerebral thrombosis in winter[J].Br Med J,1984,289:1405 -1408.
[39] Medina-Ramn M,Schwartz J.Temperature,temperature extremes,and mortality:a study of acclimatisation and effect modification in 50 US cities[J].Occup Environ Med,2007,64:827 -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