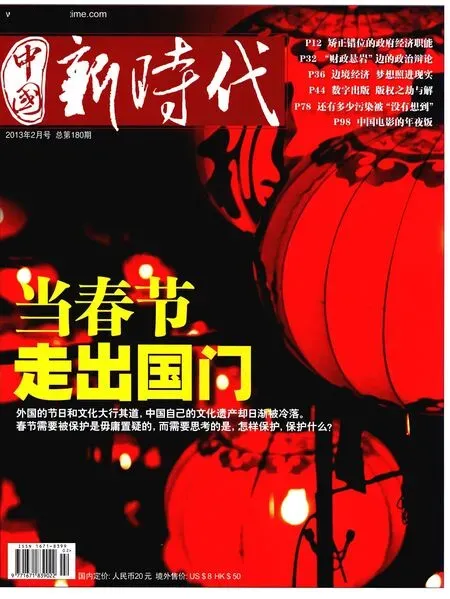日企重來
|文 ·本刊特約記者 齊岳峰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企業此前大舉向海外轉移,離開充滿封閉感的國內以求開辟新出路。支撐日本金字塔型產業結構的中小企業也仿佛追隨大企業的腳步邁向新天地。目前,日企的海外轉移開始避開充滿“政治風險”的中國,轉而向東南亞進發。
早稻田大學教授野口悠紀雄寫過一本書《制造業幻想在毀滅日本經濟》,該書的副標題是——變化的世界,不變的日本。對于中小企業衰敗,大企業拘泥于制造的現象,野口教授直接給出了一個結論:“日本產業已經不適合于現今的世界新條件。”
野口教授并沒有否定日本制造業,而是希望以一種新的形式來變革現有的生產體制,讓企業走進一個新的階段。
亞洲制造業協會首席執行官羅軍表示,日本經濟問題主要是債務問題,如果想要通過經濟增長去解決它的債務問題,就必須發展海外市場,現在中國市場沒有了,就必須尋找另一個市場。
上個世紀70年代,那個讓全世界震撼的日本制造業神話,是否已然走向終結?

日企“抱團”東南飛
曾孕育本田、雅馬哈、鈴木等眾多大企業的制造業基地靜岡縣濱松市面臨著嚴峻挑戰。隨著大企業紛紛將工廠遷至海外,當地中小企業收到的訂單急劇減少。
“單價也一路下滑,再這樣就做不下去了。”深感危機的10家中小企業去年秋天成立業務協會,抱團向東南亞進發。該協會承擔運輸、建設和人才派遣等各種業務。理事長增田弘憲表示:“大家乘上協會這條船,相互扶持向海外進發。”
“三年前這里還是空落落的,瞬間就被填滿了。”在印度尼西亞西爪哇工業園區,負責代銷工業用地的住友商事海外工業區部的飯島淳興奮地說道。據稱,設廠相關咨詢急劇增加使工業用地供不應求。
住友商事一手包辦了勞務對策建議、翻譯以及與當地政府溝通等業務,飯島稱“這使得企業能夠專注于生產”,因此備受歡迎。據悉,泰國和越南的工業園區也面臨同樣情況,尤其是面向中小企業的租賃工廠幾乎一完工就入駐了企業。
此前擔心產業空心化的行政方面也改變了態度,不再對企業的海外轉移保持警惕。濱松市政府轉為支持,稱:“希望企業在海外取得成功,并通過投資和提供工作崗位的形式回報濱松。”市政府同時在研究扶持措施。
全球經濟危機和來自中國市場的壓力,使日本經濟陷入了衰退的通道。為改變困局,日本國內呼吁恢復中日關系正常化的聲音日益強烈。與此同時,日本加速了從中國市場向東南進行產業轉移的步伐。
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日本去年對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凈外商直接投資增加超過一倍,創下1.55萬億日元的新紀錄。2012年1至8月,日本對東盟凈投資達到4,180億日元(這一數據并沒有反映很多投資承諾),4至6月,東盟的凈外商直接投資較上年增加37%。
日本央行國際收支統計顯示,2012年第二季度日本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同比增加約3,800億日元(約合296億元人民幣),超過對華投資的約3,000億日元。據業內人士透露,7月以后日企對東盟的投資也超過了對華投資。有分析稱,“中國風險”為投資轉移的一大原因。中國平均月工資在過去的5年翻了一番,而頻頻發生的勞資糾紛也成為不安因素,加上中日兩國因釣魚島問題長期對立給日本企業帶來的風險,對日關系良好且有市場潛力的東南亞或將正式成為新的投資地。其中,菲律賓是目前吸引日本資金前往的最賣力國家。
中國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是驅動日本企業轉尋他國投資地的重要力量。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中國勞動力成本已高于亞洲其他七國,其中越南比中國低15%至30%,印度尼西亞比中國低40%,而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孟加拉國僅是中國的五分之一。受此影響,2011年度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5萬億日元,而對華直接投資僅為1萬億日元,2012年7、8月,日本對東南亞投資達到1,800億日元,超過了對華投資的1,500億日元。本田汽車已在印尼投資270億日元建設新汽車制造工廠,預定將于2014年投產;豐田在泰國投資169億日元建設新生產基地,預定將在2013年上半年投產;日本最大百貨公司之一的高島屋在未來五年投資東南亞的金額高達350億日元,超過對華投資額的兩倍。

此外,“非中國因素”也是部分日企撤離中國轉投亞洲其他國家的牽引力量。按計劃,到2015年底,中國與東盟將完成自由貿易協定。屆時,東盟國家出口中國平均關稅約為0.1%。而對日企來說,到時候將在越南河內附近生產的產品運往中國廣東,比直接在中國北方和中部生產然后運往南方會更便宜。
日企全面撤出中國的實與虛
無論當前中日關系如何緊張,日本企業內心非常明白,對他們而言,中國市場不僅只有消費空間擴大的意義,更是厚實和寬廣的生產基地。
目前,中國不僅擁有頂級物流和運輸基礎設施,而且市場成熟度和規則正不斷趨于完善,伴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高端領域投入的增加,中國未來作用于企業的技術武裝動力將明顯增強,而東南亞各國的政局動蕩和勞資糾紛等政治風險則要強烈得多。日企若簡單地選擇脫離中國市場將承擔很大的機會成本。
事實上,在部分日企邁開撤離中國步伐的同時,有更多日企正在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資與經營力度。
按本田公司的最新計劃,從2013年起將連續三年在中國市場投放十余種最新車型;三菱重工也將再度拓展在華市場,2012年內在華增設近100家店鋪;另外,日本最大的服裝零售企業優衣庫在華一年增開百家店鋪的計劃正在有序推進,而永旺集團在天津、蘇州、廣州開設大型購物中心的設想也正在熱身。正是企業增量資本的不斷進來,2012年1至9月,日本對華投資仍同比增長了16%。
依照日本相關人士的計算,中日兩國的經濟融合度已達29%。若這個數字超過30%,兩個經濟體就可視為同一個國家。資料顯示,2011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達3,428.9億美元,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對華出口已占日本出口總量的20%。
目前,2萬家日企在華投資存量約有五萬多億美元,深植于機械制造、汽車、精細化工,商業零售等領域,并成為日企海外市場的最主要利潤輸送渠道。不僅如此,按專家估算,日企目前每年保持著約50億左右美元的對華投資遞增規模,其眼熱的就是13.7億人口的消費市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經濟學博士范建軍表示,從周邊能夠“移情別戀”的對象看,俄羅斯是日本企業看好的國家,近期日企在海參崴投資設廠的消息似乎也能印證這一說法。但日俄一日不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就不會存在日企大規模推進在俄投資的可能性。
韓國是日企傳統的投資寶地,但兩國圍繞獨島的爭執使投資風險日益上升,轉向韓國等于自投羅網。至于印度等南亞以及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相信日企一定有自己的判斷——這些國家的投資成熟期當在10年以后。因此,在華日企即使想撤,卻太難;即使能撤,也并不情愿。
日企衰落
過去幾十年,日本企業在資源短缺的局限下,憑借高度細分的產業體系,幾乎統治了整個電子產品領域。它們像團結的群狼一樣一致對外,贏得了世界市場,并向全球輸出管理文化。
但高度集中的財團經濟,嚴重擠壓了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無法為日本經濟注入新鮮血液。而保守的島國思維,也讓日企固執己見,安于現狀。它們沉迷于純制造,創新能力退化。為了固守既有利益,它們錯過了數字時代革命,在智能化浪潮興起時也未能跟上步伐,逐漸被邊緣化。
今天,屬于日企輝煌的一頁已被翻過,索尼、夏普、松下、三洋等創造歷史的企業,正被拋在歷史的車輪之下。為了走出困境,它們開始“去家電化”,卸掉包袱,砍掉“尾巴”,企業之間的整合也日趨頻繁。但病在骨髓的日企要想重生,更需一場文化思潮來顛覆。
企業全球化與經營日本化之間的矛盾
東京大學教授藤本隆宏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日本汽車產業的專家。藤本教授把較多的時間放在了對生產一線的觀察上。在日本中小零部件企業發生了很大變化的時候,“從我個人對大企業的觀察上看,日本廠家的設計部門與一線工程管理的組織能力,并沒有出現崩潰跡象。”藤本教授說。
但是正是這樣的大企業,豐田在大量召回,本田也因為汽車窗戶開關出問題需要召回65萬輛汽車。小絲工業公司為飛機制造的座椅,在做實驗的時候篡改耐火及強度方面的數據。日本航空(JAL)是家服務性企業,前不久申請破產保護時,其負債總額達到23,221億日元,堪稱戰后日本最大的一次倒產。
日航的倒產與國營企業民營化以后不能走向正常的運營模式有關;小絲工業造假是母公司監管不力的一個結果。但豐田、本田出的問題,則在另一個側面讓人們看到了日本制造面臨的巨大挑戰。
日本企業創造了自己的生產管理模式,如豐田有稱之為精益生產方式的“豐田生產方式”。日本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大一些的企業基本上實現了生產按市場需求,在靠近市場的地方建設相關工廠。但記者采訪到的日企工廠有一個與韓國、歐美企業巨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基本上所有日企在華工廠的經營負責人純一色地由日本總部派來,其中大多數總裁不熟悉中國文化,不懂中文語言。
這樣的生產模式讓日本企業戰線拉得越長,人才就越匱乏。日本專門采訪企業的記者說:“日本企業在國外建設的工廠越來越多,于是派出去的人也不斷增加。這些年采訪企業,基本上找不到熟人,就是過去采訪過的人,沒多久又被派到其他國家去了。”
“(大企業)負責采購的人總是在換,新來的人搞不懂我們的生產方法,我擔心他們能敏銳地看出產品質量問題嗎?”品川那家沖壓工廠的老板對記者說。他是覺得自己的質量要大大超過其他廠家,但大企業負責采購的人似乎只管成本,對質量缺少了以前那樣的關注,老板覺得自己的企業在這個時候要吃不少虧。
透過大企業生產井然有序的表象,藤本教授在分析日本大企業出現的問題時說:“這首先在于豐田自己出現了判斷上的錯誤,其組織節奏出現了松弛、過去的強項轉成了弱項。同時還在于豐田的全球化、產品市場生產的復雜化已經超過了其自身的組織能力。”
在這樣的矛盾體制下,數家日本企業同時出問題本來就只是時間早晚而已,而普通人看到的則是日本競爭能力的不斷下降。

日企路在何方
從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業績看,多數日企還是更多地“深陷迷途”,而沒有“柳暗花明”。目前,不僅享譽全球的傳統優勢產業——電子、汽車等在市場中的份額逐漸在縮小,就連逃過金融危機大劫的游戲、動漫等產業也愈發被人看衰——據專業游戲網站gamasutra報道,知名游戲企業Capcom的元老及Game Republic創始人Yoshiki Okamoto 2012年9月曾明確說,日本開發商制作出全球熱銷的主機游戲已愈發艱難,日本主機游戲可能即將走到末路。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宋頌興分析道,從外部環境看,現在更有部分美國對沖基金盯上了日本大型公司。有報道稱,這些對沖基金正購入后者債務相關信用違約掉期,這些公司包括索尼、松下等電子產品生產商及日本造紙、神戶制鋼等大宗商品出口商。
日企走到如今這一步,并非“一日之寒”。除了積弱不振的日本經濟、擾動企業的日本匯率走向和2011年3月日本強震的拖累等因素外,自身創新能力和守舊的管理理念,都在制約著日本企業的前進步伐。同時,2012年9月開始的中日釣魚島紛爭,更讓日本企業“雪上加霜”。
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即便曾引領全球的日本企業如今再怎么“落寞”,他們仍在電子、汽車、鋼鐵等領域掌握著強大的技術實力,并保留著核心的資源。同時,與中國企業不同,不管走在全球哪個國家,日企仍擁有強大的品牌知名度——索尼、松下、日立等無不為外人知曉。
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托于美國的產業轉移,借助機會,將本身的產業強化和提高,很多產業都得到很大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后,美國能轉移的產業沒有多少了,而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產業當時發展起來,給日本很大的壓力。日本長期注重應用技術,對于技術的研究、創新不夠,沒有產業引進,要靠自身的能力來發展,這是擺在日本企業面前的一條必須要走的路。
而且,就未來看,一旦他們改變目前守舊的發展思路,擺脫業務中的累贅,他們仍有希望在未來的產業鏈中繼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