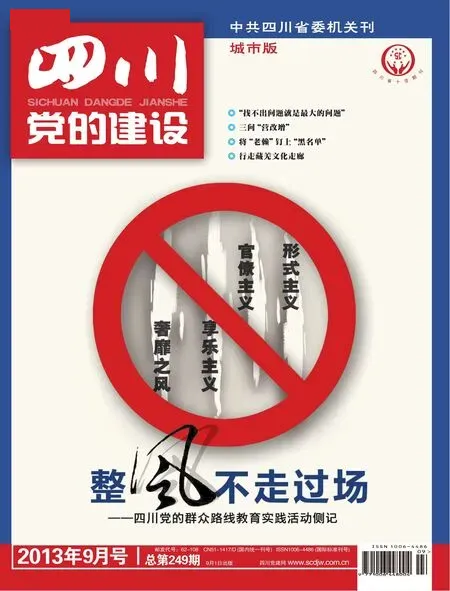行走藏羌文化走廊
□ 文/莊春輝 李妍婕 供圖/莊春輝
行走藏羌文化走廊
□ 文/莊春輝 李妍婕 供圖/莊春輝
“潔凈精微”的唐卡藝術
“唐卡”是我國藏地獨特的、極具魅力的繪畫藝術,在其發展歷程中,涌現出多個不同風格的藝術流派,“覺囊畫派”唐卡以其悠久的傳承歷史和卓越的藝術審美獨成一宗。它起源于佛陀創立的時輪教法,這一門傳統技藝從1027年傳承至今從沒有間斷過,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活態傳承的文化空間。它生長在青藏高原源遠流長的文化之中,與巴蜀文明交相輝映,兩種文化的碰撞孕育出了這樣一顆璀璨明珠。
覺囊唐卡主要有工筆重彩與白描等技法,首先按照《繪畫量度經》標準起稿;其次用色上強調對比,講究色彩富麗,并用點金和其它中和色統一畫面;再次用線條勾勒,既粗細一致、剛柔相濟,運筆有粗有細、頓挫變化,達到傳神動人的效果。華麗、細膩的繪畫風格,使畫作具有濃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類別上覺囊唐卡分為彩唐、黑唐、金唐等,顏料全部采用本地產的礦物原料,經多次研磨,調以膠汁和牛膽汁,畫作上色之后色彩光亮,圖案清晰,久不褪色。因其藝術特點融合印、藏、漢繪畫藝術精粹,畫面的層次和景致關系經過細致、巧妙的構思,配合不同技法,使多維時空和人物關系和諧呈現為一個整體,畫面古樸空靈,藝術審美和繪畫工藝圓滿交融,被唐卡專家譽為“潔靜精微”。
嘉陽樂住仁波切是覺囊唐卡傳承人,他告訴我們,繪畫唐卡如同修習實踐,是磨練、調整、把握自己心性的過程。對于繪制費時數月乃至數年的精細唐卡而言,心緒的散亂會在作品中留下波動的痕跡。誠然,當我們欣賞那一幅幅精美的唐卡作品時,不得不驚嘆作品里人物造型嚴謹但又不顯刻板,構圖疏密有致,色彩鮮麗和諧,富于裝飾性,畫面有一種統一感,又顯得生動活潑。唐卡的題材涉及歷史、風俗、藏醫藥、時輪歷等多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雪域藏地特定歷史時代和人們的社會生活。“畫師的傳統技藝在超越和覺悟中透徹出求真、求善、求美、求慧、求是的靈空境界與價值取向,是他們‘在修行中繪畫,在繪畫中修行’的真實寫照。”
首都師范大學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謝繼勝教授觀賞藝術展后贊嘆道:“覺囊畫派唐卡兼蓄諸家流派之長,既有康區噶瑪噶智畫派線條的流暢與靈動,色彩的鮮明與色調的統一,又有衛藏新舊勉唐畫派人物形象描繪的細膩精準、用色的沉穩厚重和構圖的嚴整雍容,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是精美卓絕的藝術珍品。”
羌笛無怨 春風依舊
岷江河畔,白云橫穿峽谷。
晨起的羊群,像一朵矮矮的白云穿梭在岷江沿岸的卵石與山坡上。山間小路兩旁的露水,浸濕了理縣羌族漢子楊平挽起的褲腿。只見他一個箭步跨上一個大石包,迎著山谷中風來的方向,取出腰間的羌笛,用手指捏住笛身,兩排管,六個孔,七階音,兩腮鼓起,綿延婉轉的笛聲悠悠響起……
關于羌笛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很久以前,上天派了一男一女來到人間。男女間有河相隔,無法見面。于是男子吹著羌笛,女子吹著口弦,以托相思。對羌笛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故本四孔加以一。”由此可知:羌笛在漢代就已經流傳于四川,據說是由南遷的羌人從西北地區帶到今天的岷江上游。而之后唐代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寫下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不朽佳句,讓世人對羌笛充滿了好奇。
羌笛是用當地高山上生長的油竹制作而成,先將兩根長約15~20厘米、直徑1厘米的油竹削成方狀,兩管并列后用絲線纏繞捆扎固定;接著在兩個管面上各制出6個大小一致,間距相等的發音孔;最后在管頭的一端各插一根竹簧管哨即成。它有十余首古老的曲牌,常演奏的曲目有《折柳詞》《思想曲》《莎郎曲》等,笛聲一出,悠遠蒼涼,像在哭訴著哀傷的情思,常給人以虛幻迷離、動人心魄之感。由于羌笛在羌人生活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因而它成為了羌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在中國音樂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譽為“民樂之父”。
“羌笛不同尋常的演奏方法需氣沉丹田,讓氣流在鼻腔與口腔間自由循環。因演奏者需鼓起雙腮,民間稱之為鼓腮換氣法。”在演奏中,一曲音樂不論長短,一氣吹成,絕不停頓換氣。理縣羌笛演奏傳承人楊平告訴記者,2002年他深入高山羌寨,向民間羌笛老藝人虛心學習羌笛演奏技藝,剛開始,演奏一首曲目,他要換氣多次。兩年后,楊平習成鼓腮換氣法,并在不斷的探索中嘗試著將羌笛進行革新。
2009年7月,作為羌笛展示者,楊平隨羌族音樂風情史詩舞臺劇《羌風》表演團隊赴京巡演,楊平特意創作了羌笛曲目《出征》,“地震中一些羌笛傳承人遇難,讓羌笛表演瀕臨滅絕。萬幸的是,更多人開始關注羌笛,關注羌族文化。”一曲《出征》悠揚響起,舞臺上,楊平的眼角濕潤了,舞臺下,觀眾潸然淚下。
穿越歷史的文化工程
在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城50公里的茸木達鄉境內,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寺廟——棒托寺。該寺以規模宏大的石刻藏文大藏經堆而著稱。
棒托寺石刻大藏經是用鐵器等金屬工具將卷帙浩繁的藏文大藏經整套逐字逐句鐫刻在一塊塊石板上,它不同于藏族聚居區普通形成的嘛呢堆,它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用不規則石板正反兩面精心鐫刻后,再按經文類別和順序頁碼壘疊成的長方形石經高墻。據測算,那散布在8座巨型佛塔之間的石經高墻,是用80多萬塊不規則的石板刻制、壘砌而成的,具有極高的文物和學術研究價值。
走進棒托古剎,就像走進了理想的人間凈土與現實交融的世界。整部石經圖文并茂,素雅別致,散發著幽幽的古樸氣息,它們跨越明、清兩代至今,積600年山川靈氣和信眾虔誠之心于一體,有著極深厚的文化積淀。
而現在藏經石刻技藝融精湛的石刻技藝和傳統繪畫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石刻彩繪。通過就地采選石質相對堅硬的天然板巖青石作原材料,不改變石材自然形狀,對邊、面破碎的部分進行必要的處理后,根據石材的大小進行佛菩薩構圖,勾勒出人物形象。
藝人依照精描的人物、文字、圖案造型,采取線刻、陰刻、陽刻、減地陽刻、淺浮雕等多種手法進行線條雕刻。然后因材使刀,巧妙加工,使人物造型準確,線條優美流暢,如行云流水。最后將已雕刻完的石刻畫面通刷一道白色顏料作為基色,待基色干定后,再開始繪染,繪染遵循藏族傳統繪畫的基本規范,多使用紅、黃、藍、白、黑、綠六種原色,一般不使用中間色,以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