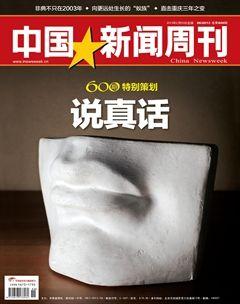民主“麻煩”
黃艾禾 袁野
2006年的時候,我們聽說了一個新聞:北京一個叫恒昌花園的小區,業主們準備罷免他們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這引起了我們很大興趣,因為在當時,時見于新聞媒體關于城市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報道,都是在為業委會加油撐腰。
再往前若干年,中國城市中沒有過“業委會”這個新鮮事物,只有街道組織的“居委會”。當業主們付了高額的房款入住新家后,發現自己的許多權益并不能得到保護,特別是開發商遺留的許多問題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卻找不到相應的部門去申訴。小區的業主們開始推選出自己的代表維權,這就是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初起。
我們后來在報道中采訪過的一位第一代業委會的“元老”,舒可心,就是這樣走上了這個舞臺。他曾經帶領著他的伙伴們在開發商的門前靜坐施壓,贏得了聲譽。他們是一種象征:中國的民眾開始有了維護自己權益的自覺意識,并且靠自身的力量來自主維權,這難道不是一種真正的民主萌芽嗎?
到了2003年,建設部頒布《物業管理條例》規定,在一個小區中,業主大會應當代表和維護物業管理區域內全體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的合法利益,業主大會的決定對物業管理區域內的全體業主具有約束力。從那以后,業委會在中國城市的小區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
但到了2006年,現實情況就讓人看不懂了:這樣拼著命為民眾“打天下”的業委會,竟然會被當初選他們的民眾所拋棄?編輯部的選題會上大家討論熱烈,覺得這是讓人們理解民主制度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都市中的民主“麻煩”
采寫這組報道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當時與舒可心的幾次深談讓我們印象至為深刻。他將業委會所從事的工作,比做是一個民主的課堂——這份工作在教給大家怎么開會,怎么做決定。說到底,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詞匯,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舒可心說,單是開會這件事就非常有學問。他們開會常常湊不齊人。在許多業委會,湊不齊人就由業委會主任一人說了算,這樣一來民主規則就漸漸被架空。舒可心想的辦法,是送書面議題給所有業委會成員(一共五人),請他們寫好意見返回給業委會信箱。如果兩天沒見意見返回,則視為不同意。如果得到了四票同意,就是業委會的決議。
“所以我們業委會是很容易出決議的。”舒可心說。這讓人聯想到前不久的一本很引人注目的新書《可操作的民主》,談的就是開會怎么開,主持人怎么主持,每個成員怎樣發言,怎樣才能又保證每人的權利,又能讓會議開得有效率。民主是人人都向往的事,但實現民主的過程卻要摸索學習。
而恒昌花園小區業委會主任何東寧的下臺,很大的原因是業主們認為他做事獨斷專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對何東寧進行了回訪,他承認自己常常會在許多事情上個人拍板做主。“難道做每一件好事都征詢:你同意嗎?這種想法不是很可笑嗎?與其花時間召開會議,我用這個時間三封找錢的催款信都發出去了……說來可悲啊,大家不清楚是業委會做的好事,80%都是我做的。但大家不了解我,不了解業委會。”何東寧如今依然感到非常委屈。
談到民主的效率,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法學博士毛壽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實行民主,實際上就是決策過程要慢,但是一但決策通過了,執行效率就會很高。
這也就是我們這組文章的大題目《都市中的民主“麻煩”》的由來。
這一組報道在2006年8月14日作為封面文章在本刊刊出后,被廣泛轉載,特別是許多討論房產與物業的網站全文轉發。第二年的5月23日,《都市中的民主“麻煩”》獲得了亞洲出版業協會2007年卓越新聞獎中的“卓越深入報道”獎。
依然走在路上的業委會
在2006年我們寫作這組文章時,北京市政協關于小區物業管理的調研報告指出,全市3077個居住小區物業管理項目中,按照《物業管理條例》成立的業主大會有360個,僅占住宅物業項目的11.7%。到今天,據估計北京的居民小區大約有5000個,而在我們近日再次采訪任晨光時,他估計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成立了業主委員會。
時隔近7年,任晨光現在的身份,是北京市業主委員會協會申辦委員會召集人。這個北京市業主委員會協會從2006年就開始申辦,到現在也還沒有申辦成功,所以一直以申辦委員會的身份在開展活動。召集人一共四人,都是曾任或者現任的小區業主委員會的負責人。
當年在采訪中,許多受訪的業委會成員,對業委會事務的思考已遠超出房產物業,他們實際是看到了在小區業委會的碰撞與羈絆行進中,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也在生根與成長,中國的民主之路會有自己的獨特路徑。任晨光所代表的新一代業委會成員們,已經自覺地開始互相聯絡,試探進入街道居委會、競選各級人大代表。
2006年,任晨光曾進入到居委會,成為健翔園社區居民會議秘書長,擔任此職務至2009年。這是一個別的小區沒有的職務。居民會議與居委會的關系,實際上有點像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與人大常委會的關系,前者是決策和權力機構,后者是前者的執行機構,前者對后者實施監督。
但是,“三年下來,沖突太大”,任晨光說。2009年居委會重新選舉,街道辦通過各種手段取消了居民會議秘書長制度,居委會再次回到2006年之前無居民會議監督的狀態。
任晨光認為,導致居民會議秘書長制度被取消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自下而上的自治與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制的沖突。這樣的沖突,現在也廣泛地體現在自治的村民委員會和鄉鎮一級政府的關系中。
而且目前這樣的沖突普遍缺少司法救濟渠道。2009年的時候,針對街道辦的做法,任晨光等曾去區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得到了區政府的支持,但這樣的支持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
為什么到了今天成立業委會的小區比例還是這樣低?這其中一個障礙是,北京市規定業委會成立前的籌備組的組長必須由街道辦指定。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將業委會置于街道辦的控制之下,如果街道辦不支持某個小區成立業委會,籌備組不作為,那么小區業委會就無法得以成立。
另一個障礙是《物權法》中規定,業主共同決定須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業主同意才能生效。任晨光認為這個比例過高。如他所在的健翔園有869戶住戶,要召集到一半的業主集體開會都很困難,更別說獲得一半的業主的同意。他認為應根據“二八原理”——社會活動中只有兩成的人是積極參與者,修改這樣的規定。
看來,六七年時間過去,小區業委會在成長道路上依然行進艱難。任晨光說:“當時我們估計得比較樂觀,沒有想到有很多技術問題需要解決。”但是任晨光也并不氣餒,“業委會內部有矛盾很正常,這些矛盾也促使了業委會成熟。在沖突的過程中,大家慢慢學習,慢慢形成了規則。”
他說,現代新型的小區業主關系,是中國大陸民眾沒有經歷過的,有沖突很正常。在這個解決沖突、自行學習的過程中,任晨光重視起了對會議規則的研究。他現在也在業主委員會中推廣和普及“議事規則”——來源于《羅伯特議事規則》等西方經典議事著作中的方法。
他總結了十條左右的常用議事規則,用于對業主委員會的培訓。這些規則包括:“主持人在會議中不得對討論的議題表態”,“發言限時限次”,“對上一個發言人持反對意見者有優先發言權”,“發言人必須面對主持人,而不是爭辯方”,“發言不得懷疑他人動機”等等——這些規則與《可操作的民主》一書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