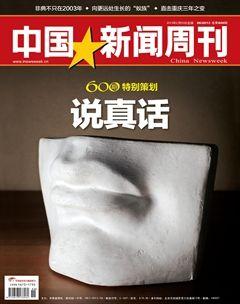公共利益呼喚積極公民
秋風
在當代中國,公共利益有時遭到廣泛而嚴重的侵害,但多數時候卻是公共利益無人維護。人們經常會因此而思考,中國怎么啦?或者中國人怎么啦?
公共利益的顯著特征是,利益的主體是公眾,也即數量較大而相互之間沒有聯系的一群人。公共利益遭到侵害,也就是意味著,眾多個體的權利和利益遭到侵害。很多人期望,這些權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個體應當起而抗爭,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
但在這種情形下,會出現制度經濟學充分討論的兩個相互關聯的難題:第一個是“搭便車難題”:我的權益確實遭到了損害,但維護權益是要付出代價的。我要計算其中的成本-收益。所幸,其他人也遭受了損害,如果其他人起來維權,我也可以順便維護自己的權益。于是,每個人都等待其他人行動,準備搭別人的便車。結果,所有人都在等待,而無人出頭維護權益。
第二難題是“集體行動的困境”:既然一群人的權益遭到侵害,侵害者的力量比較強大,要維護權益就得一群人集體行動。但如果人數足夠多,集體行動就沒有辦法展開,因為,每個人都會預期,從集體行動的結果中,自己只能得到不那么顯著的收益,自己干嗎要費力氣參與集體行動?
在當代中國社會,可以隨時觀察到上述兩種心態。于是,中國就出現了這樣的情形:大量民眾的利益,也就是公眾利益,遭到廣泛、嚴重而持久的侵害,卻沒人起而維護自己的權益。但這絕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如何糟糕,也不是因為民眾缺乏權利意識。權利只是利益的法律表達,民眾不可能對利益不敏感,也不可能不知道權利的價值。問題的關鍵在于,他知道,但不愿行動。因為,他太理性了,他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理性經濟人”。
經濟學家早就明確指出,“搭便車難題”和“集體行動的困境”其實都是因為人們就是“理性經濟人”。當下中國之所以存在著公共利益無人維護的情形,恰恰是因為,當代之國人太會算計了,對個人行為之成本-收益的計算過于精明了。恰恰是這樣的人,在自己權益遭到損害時,選擇忍氣吞聲。聰明人的精明選擇導致公共利益無人維護。
個體的權益必須自己維護,公共利益必須公眾來主張、保護和擴展。但公眾要具有這樣的行動能力,就至少需要公眾中部分人之自覺。但我所說的自覺,不是時下流行的權利的自覺,更不是人人本就具有的利益的自覺,而是君子的自覺。當國民中成長出一個君子群體,公共利益也就有了守護者、捍衛者、主張者。回過頭來看,過去十年發生的維護公共利益的每一事件中,都活躍著君子群體。
那么,君子是什么?孔子給君子下過一個十分簡單的定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里的“小人”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理性經濟人”,他關注于自己的、當下的、看得見的、主要是物質的利益。君子則喻于義。“喻于義”并不等于否棄利,只是說,在利之上,君子還喻于義。義者,宜也。事各有其理,順其理,則事可成。此理對人提出特定的行為要求,即構成“宜”,也即“義”。人當“義”而行,則順事之理,而可成事。與小人不同,君子“見義”勇為,甚至殺身成仁,不計較自己之行動是否能夠獲得足夠收益。
因此,一個人若是君子,面對個體權益遭受侵害,就會起而捍衛自己的權益,而不計較自己的得失。這樣的行為本身就具有公共性。更為重要的是,如此君子可起到示范作為,給其他人以勇氣,讓他們同樣起而捍衛自己的權益。
其實,儒家所說的君子,就是西方共和主義理論家們所說的“積極公民”。君子具有一定的道德意識,具有比較強烈的是非感,因而對于權利、對于正義、對于公共利益較為敏感。同時,他有具有一定的合群能力,組織分散的人們維護自己的權益。
當代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就是,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君子嚴重匱乏。因此,在大量公共利益遭到嚴重侵害的場合,每個人都有所不滿,但每個人又都束手無策、逆來順受。在有些情況下,人們實在無法忍受,起來維權,卻通常采取混亂而暴烈的方式,這種方式未必能夠解決問題,反而招來很多麻煩。原因同樣在于,其中缺乏君子,因而缺乏組織,而沒有組織的維權,通常會趨向非理性。
于是,公共利益獲得有效維護之關鍵,就在于國人之君子意識的覺醒。君子的權利意識必然比較敏銳,君子具有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君子維護權利的能力也比較強。這樣看來,傳統之復興實有助于養成積極公民,有助于公共利益之維護。可以說,在當下中國,君子之養成實為優良治理秩序形成的關鍵,因為,制度本身也要靠分散在社會各個層次、領域的君子群體之仁、智、勇,方有可能構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