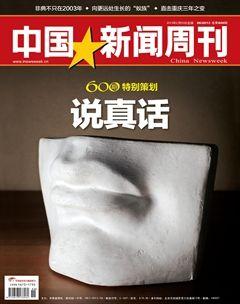改革就是還權于民
關于權利平等,先從我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說起。
上世紀50年代讀小學,一女教師偶然聽說父親的名字,即詢問父親的近況。回家后問父親,他終于想起:“她是我讀小學的同桌,校董的女兒!”
父親不是出身世家,而是底層移民子弟。那時尚未有社會屏蔽,誰也沒有剝奪他進入這座城市的小學受教育的“權利”,他是與校董的女兒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他此后的經歷也說明,通過“文化翻身”,可以完成從移民子弟融入上海文明社會的過程。到上世紀80年代,我突然發現這一故事已無法復制。新時期進入上海打工的兩代家鄉民工,都被同一道戶籍門坎絆住,被隔離在都市生活之外。即使是在同一個城市納稅十年、二十年,農民工的子弟還是農民工,“同桌的你”不再屬于校董的女兒與農民工的兒子。
上世紀90年代,我在廣州受聘為一家農民工子弟小學的名譽校長,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接受的唯一一個社會職銜。那一天,我提議與這個學校的“校董”一起打開校門,讓等在門外多時的孩子提前入校。門開處,幾百個孩子歡蹦亂跳涌進校園,寂靜的校園剎那間充滿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我很有“成就感”。下午與教師座談,他們的發言使我一下子冷靜下來:即使這些孩子上了學,是否能及時融入社會還是問題,升學、就業、婚姻,每一道坎都有他們邁不過去的障礙。
又過十年,為我裝修房子的一位農民工,轉移到另一小區接著給別人裝修。一天深夜,他打來電話,請我無論如何幫忙,把車子開出來一趟,送他進小區。原來他夜半返回,門衛見他衣衫臟舊,死活不讓進。情急中,他想起我這里有車,請求幫忙。車到后,他示意我停遠一點,以免門衛發現破綻;上車后坐到后座,翹起二郎腿拿起報紙作首長狀,享受了門衛行注目禮放行的待遇。
在這個“悶聲大發財”的新時期,中國這桌現代化跨世紀大餐,坐上去享受的人背影憧憧,這桌大餐買單者,不是那些坐著的,恰是那個站著的——農民。如果農民是牛,我們從這頭牛身上剝下過兩張皮,目前在剝第三張皮。陳毅談國共決戰,江山何來,曾詩性大發:“淮海戰役是五百萬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姑不論其他,即此而言,將軍承認了第一張皮。江山到手,進城大搞工業化,原始積累來自何方?梁漱溟曾為此上書,來自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來自“內卷式殖民地”——農業、農村和農民,這是第二張皮。上世紀70年代后期改革開放,國有企業全面癱瘓,兩億農民與幾乎等額的外資、港資、臺資相遇,終于攀上GDP世界第二的高峰,是土地財政以及億萬農民進城打工苦干出來的——這就是目前剝的第三張皮。在此長達六十年的歷程里,農民的政治權利是如何進步的呢?
上世紀90年代末三農危機凸顯,南方周末記者來訪,我先請他做一個簡單算術題,八分之一大,還是五分之三大?他說是五分之三大。我說,那你就找到了三農危機的根源。什么是五分之三?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南方北方吵得一塌糊涂,最后達成妥協:南方黑奴計入各州選舉人口,每一個男性成年奴隸計為五分之三人。什么是八分之一,1954年選舉法規定:城鄉人口選舉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八比一,即農民的選舉權是城市居民的八分之一。
此后的農民政治權利即以此為起點,緩慢進步:1979年少數民族自治地區突破八比一,進入到四比一、五比一,其他地區還是八比一;1982年選舉法修訂,允許農村地區鎮級建制及大企業職工進入到四比一;1995年再次修訂,全國統一為四比一;最后是2010年,這一比例進步終于實現為一比一。
數據上的進步,來之不易。但究其實際,如何真正代表農民的權利、如何真正當好代表,還是值得檢討。
中國已經成為人口流動量最大的國家,每年春節,鐵路、公路等運輸部門將高達三億流量的旅客輸送回家,幾乎是把西歐的全部人口來回搬動兩次。我因此而同情年年挨罵的鐵道部。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人口堰塞湖最多最有效的社會,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堰塞湖,將億萬人口分割阻遏在這一岸或那一岸。我們之所以慶幸還能安享城市文明,還能嘲笑印度的種姓制殘余及其城市骯臟雜亂,是依靠維穩,再加更多倍數的城管人員。
我們承認改革的進步,但僅有經濟改革是不夠的,還要有政治體制改革;有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夠,還要有社會改革。社會改革不是覆蓋性社會治理或恩賜性還利于民。改革不是做加法,而是做減法。經濟、政治、社會改革,所有改革的本質含義歸其一,是還權于民。
(作者系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