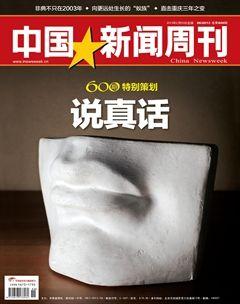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超級女聲”:關于民主的解讀盛宴
萬佳歡
湖南衛視常務副總監李浩匆匆地從會議室里走出來,看起來有些疲憊。這是個周六,他頭一天晚上才跟著《我是歌手》錄到半夜,剛剛的會議內容則是討論2013年湖南臺另一檔真人秀節目《中國最強音》的事情。
《中國最強音》購買自風靡美國的《X factor》,它的總導演是湖南電視臺“超級女聲”最早的參與發起者之一廖珂。“超女”的另一名重要導演洪濤,正在緊張錄制目前熱播的《我是歌手》。
最早參與超女的一眾元老如今都已是電視娛樂界的重要力量。總導演王平現任湖南廣播電視臺副臺長,主要負責海外業務;最早發現《美國偶像》并提案做“超男”的導演夏青將擔任《中國最強音》的藝術指導;當年成都唱區的導演易驊成為深圳衛視副總監;后來加入“快樂男聲”制作團隊的龍丹妮,更成為天娛公司的領軍人物。
2005年,就在李浩身后那間會議室,時任湖南臺總編室主任的他每天都要跟這批導演一起開上一個半小時的“超女”主題會議。他們策劃的這檔節目在那一年有15萬人參加,更把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帶入了集體狂歡狀態。
“超女”席卷知識界
“超女究竟代表了什么?” 2005年9月,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中國新聞周刊》舉辦的“大眾流行文化與價值重構”論壇上發問。她得出的結論是,“也許她們是我們新的社會環境中一種生活方式的代表。生活中新工具所傳導出的熱流,正在影響和改變我們的生活。”
此前幾個月,《超級女聲》引發了中國電視史上前所未有的娛樂風暴。這檔節目收視率最高時竟達到15%,與《新聞聯播》持平。除了普通電視觀眾,這股風暴還席卷了眾多社會精英及知識分子,他們與十多萬參賽者、百萬超女粉絲和數億普通觀眾一起,成為那場狂歡的參與者。
就連剛剛回國的哲學家李澤厚也看了最后一場“超女”比賽,他在從機場到家的路上聽說了這個節目,因為“朋友和學生都在談‘超女,而且都給了肯定的評價,”他在《中國新聞周刊》論壇上說。
彼時,不同觀眾對“超女”的興趣點各不相同:有的觀眾對李宇春、張靚穎等草根選手的成長軌跡感到親切;有的觀眾熱衷于毒舌評委們的尖酸刻薄。而更多的學者則看出了不同的味道:無門檻參賽、直接讓觀眾參與并賦予其前所未有的決定權,使這個節目擁有了更多審視、評判和解讀的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周濂受邀參加《中國新聞周刊》論壇之前發現關于這個話題的解讀和評論已有十幾萬字,而且都出自文化評論家和學者之手。這些文字大多集中于探討超女的價值、社會含義和公共意義。
就在這些評論和解讀里,“超女”漸漸從一檔單純意義上的娛樂節目,變成了一個充滿各種意義投射的、復雜的社會議題。
“超女式民主”
事實上,在海選階段,媒體對“超女“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評委的刻薄言論、“成都萬人逃學報名” “紅衣教主”等遠離音樂節目的社會話題,直到一批水準較高的歌手出現,媒體才集中報道“超女”們的經歷故事和音樂素養。
而學界對“超女”越發豐富的解讀很快也引起了媒體的興趣。一些學者對“超女”持樂觀態度。哲學家李澤厚在《中國新聞周刊》論壇中指出,“超女”這類娛樂形式“以一種青春的、富有個性的、無拘無束的方式,為這種群體性的無意識的壓抑,提供了一種非常健康的宣泄渠道”。他把這種新的文化態度稱為“轉換性的創造”。
而一些人的觀點則相對悲觀。學者秋風認為,在社會觀念的舞臺上得有一個平衡,“不能說這個社會好像全是木子美,然后就一路這么狂奔下去,我覺得需要某個東西把它往回拉一些。”

除此,“超女”還引出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概念——“超女式民主”。有評論指出,“超女”的短信投票首開“文化民選”先河,是對民主的推動,中國新生代的民主與理性精神從中可窺。
但反方觀點很快出現。2005年8月,學者許紀霖列舉種種疑點,認為將“超女”想象為一場民主的預演、預示“民主時代的來臨”有點無稽之談,“超女式民主”只是一種民粹式民主。
崔衛平發文稱,許紀霖的主張需要商榷——無論如何,民眾短信投票、選出冠軍的“娛樂民主”改變了民主總是與精英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印象,各路粉絲“所享受的投票空間是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沒有享受過的”。
很多學者由此進一步提出,“政治民主”和“娛樂民主”的區別需要辨明……爭論一步步發酵,而媒體也基于這些觀點對“超女”進行闡釋。《鳳凰周刊》發表文章,指出“超女”是“一次民主的娛樂狂歡”;新加坡《聯合早報》則多次基于“超女”談論民主和民主進程。
“超女”作為一檔娛樂節目竟出人意料地與政治話題聯系在一起。一些觀眾由此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即使他們也許還不明白“民主”究竟是什么——自己的每一次短信投票原來都是一次民主行為,瘋狂參與“超女”的行為似乎也變得嚴肅起來。
不應承載之重
遭遇如此大規模的過度解讀并不是“超女”主創方湖南衛視所期待的。
2003年,“超女”的前身兼“試驗品”《超級男聲》最早出現在湖南電視臺娛樂頻道。土氣的男孩們滿臉油光地開唱,一開始鮮有人關注。湖南衛視高層領導之所以將幾期“超男”節目送上衛星頻道,并在第二年正式開選“超級女聲”,只是想讓湖南衛視的娛樂內容得以豐富。而無門檻、短信投票等方式也是為了更多的民眾參與和提高收視率。
2005年,“超女”驟然火爆對湖南臺來講本應求之不得,但學界的過度解讀反而讓湖南衛視內部措手不及。
“一些強加的、政治化的東西是‘超女不應該承載的,”湖南衛視常務副總監李浩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湖南臺專門成立了“輿情小組”,收集各路消息、觀點,寫成《輿情日報》,每日一冊,并在 “超女例會”上進行專門研究。在2005年“超女”結束三個月后,《中國新聞周刊》曾推出關于“超女”的封面報道,其中《一個電視娛樂節目引發的社會綜合征》一文分析,當一檔“新鮮的純粹的”節目出現時,觀眾、媒體、學者、領導以及社會都“猝不及防”,各方的反應“過度亢奮、過度敏感,無論觀眾還是媒體幾乎都陷入了瘋狂”。文章更進一步得出結論:“需要調整的或許不是節目,而是看節目的心態……其實,它只是一個讓觀眾樂了、讓媒體和主辦方賺了的電視娛樂節目。”
2006年,“超女”的開動比前一年晚了40多天,參賽選手年齡也被限制在18歲以上。同年6月,《中國新聞周刊》又一次刊載關于“超女”的封面報道, 形容這一年的“超女變得更像一個淑女”,評委也不再毒舌,這“既來自于主管部門的‘規范,也來自社會輿論的‘教化”。
在“后超女時代”,雖然廣電總局出臺了各類規范,但由“超女”引發的娛樂選秀風潮還是一直持續至今。從綜藝選秀到職場選秀,各類“拓展版本”不斷涌現。
但觀眾對于這類節目已經更加理性。對于2012年的《中國好聲音》以及2013年初湖南臺新節目《我是歌手》的關注更集中于音樂和歌手本身。
如果人們此刻冷靜回望,就能發現當年對于“超女”的過度解讀裹挾了太多知識界的美好愿望,但那些愿望確實不是一檔娛樂節目能夠完全承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