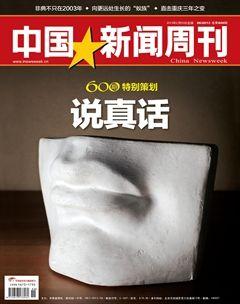逃離德黑蘭:中情局欠好萊塢的一份情
朱靖江
一部電影能否在時代的洪流中充當起弄潮兒的角色,恰當的題材、合宜的時間以及主創者的修為能力,都會起到相應作用。近段頒獎季中風生水起的影片《逃離德黑蘭》,似乎正搭上了好運直通車。
《逃離德黑蘭》是美國“演不太優則導”的代表人物本·阿爾弗萊克自導自演的第三部作品。這位內心世界遠比面部表情豐富的好萊塢才子,重拾他在大學期間荒廢了的中東關系史,將一段中央情報局與好萊塢電影人聯手搭救被伊朗革命怒潮圍困的美國人質的歷史事件,以一種極具張力的敘事方法展現在銀幕之上。
以題材而論,《逃離德黑蘭》是讓每一位電影編劇和導演都為之心動的故事——用“拍攝電影”來搭救陷入絕境的人質,的確是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后無來者的神來之筆。本·阿爾弗萊克飾演的中情局特工托尼·門德斯出此險棋,居然僥幸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與好萊塢著名化妝師約翰·錢伯斯在偽造身份、營造假象方面足以亂真的布局,另一方面,或許也和伊朗社會對電影持相對寬容的態度有關,若非如此,便很難解釋在時局如此敏感之際,伊朗當局竟會允許一支好萊塢電影攝制組入境選景,原本殺氣騰騰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兵竟會因撥打了一通可疑的制片公司電話印證說法后,便慨然讓這七名拿不出入境憑證的西方人登上飛機,揚長而去。
以時機而論,《逃離德黑蘭》在當下美伊關系嚴峻的情勢之下,自然會贏得更多青睞。電影既追憶了一場三十年前的傳奇往事,又與當代叵測的時局緊密勾連,正適合人們看著銀幕上一幕幕驚險故事,再掃一眼伊核問題的最新報道。
在電影的藝術價值上,《逃離德黑蘭》頗具爭議性。貶抑者指其乏味無趣,人物塑造頗為臉譜化與概念化,譬如本·阿爾弗萊克塑造的特工門德斯總是一臉郁悶的表情,乃至有人嘲笑說,當他昔日的伙伴馬特·達蒙主演了一部又一部《諜影重重》的時候,阿爾弗萊克卻主演了一部又一部“心事重重”。為了表現特工門德斯“人性”的一面,阿爾弗萊克為他設計了分居的妻子和可愛的兒子,這不但成為他取信于美國人質的“真憑實據”,還將他與那些兇惡的伊朗民兵區分開來——后者不但蓄著塔利班式的大胡子,還當街殺害那些有著通美嫌疑的普通民眾。當然,最令人質疑的莫過于影片結尾時伊朗士兵開汽車追飛機的場景——這種“最后一分鐘營救”式的橋段早在1941年《北非諜影》時就顯得有些落伍,居然又出現在了剛剛贏得“金球獎”和“美國導演公會獎”的影片當中。
與批評的聲音相比,《逃離德黑蘭》同樣也收獲了不少美譽,至少在不可能前往德黑蘭拍攝的情況下,影片相當完美地再現了伊斯蘭革命之后的伊朗時局,讓觀眾頗為信服地進入電影營造的時空之中,感受這場營救行動的緊張與懸念。當然,本·阿爾弗萊克也試圖將一種反思、批判的精神,投射在美國屢屢失利的中東政策上。接下來就要看另一場美國的外交噩夢——駐利比亞大使在班加西遇襲身亡事件,何時能納入好萊塢導演們的創作藍圖之中了。
影片推薦本·阿爾弗萊克的代表影片
《心靈捕手》
講述了麻省理工學院數學教授藍波公布了一道難解的數學題,卻被年輕的清潔工威爾解了出來。可是威爾卻是個問題少年。教授藍波為了讓威爾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浪費他的數學天賦,請了很多心理學專家為威爾做輔導,讓他一點點敞開心胸。
《城中大盜》
美國東部,位于波士頓近郊的查爾斯城,愛爾蘭裔的工薪階層占有很大比例,貧困的生活條件讓人們鋌而走險,銀行搶劫案時有發生。有一天早晨,銀行經理人克萊爾·吉塞遭遇一伙劫匪,她被劫持為人質。奇怪的是,克萊爾最終意外生還,似乎這個早晨的變故從未發生過一樣。一天,她邂逅了高大英俊的男子道格·麥克雷,奇妙的緣分就此展開,兩人的命運也由此改變
《失蹤寶貝》
美國小鎮上,四歲女童阿曼達突然失蹤,她的姨媽和姨夫找到私家偵探Patrick Kenzie調查外甥女失蹤的案件。Patrick Kenzie和女朋友兼工作搭檔Angela開始了艱難的調查。隨著調查的越發深入,他們發現阿曼達的母親是一個地道的癮君子,她對毒品的關心程度似乎遠勝于女兒的失蹤,調查圍繞她展開之后,毒品販子、詐騙犯、虐童者漸漸浮出水面……但是阿曼達的名字卻越來越遙不可及,Patrick Kenzie也站在了道德的十字路口,開始思考怎樣才算是“伸張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