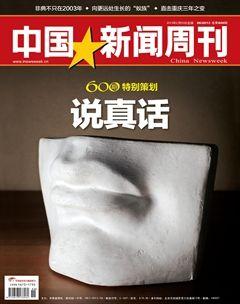心理原罪
我所在的大學心理咨詢室新生篩查工作做得特別笨,全校3000多名新生每人都要就自己的心理問卷結果跟咨詢師面談至少5分鐘,如果是高分,再優惠10到20分鐘。所以每年的篩查季里咨詢師們為防止“吐血而亡”都想出一些招來對問題學生快速鑒別。
所謂高分生,就是有可能存在一定心理問題的學生。約談高分生的時候,多數情況下我邊慢慢啟發,邊細致入微地觀察他們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但有時實在太累或門外等候的人太多,我就單刀直入問三個問題:是獨生子嗎?父母關系怎么樣?是誰帶大的?這三個問題的目的是看看他們是否有“原罪”,如是,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好甄別。
什么叫“原罪”?舉例說,如果一個女孩回答說,“我家有5個孩子,我是最小的,上面有4個姐姐”,就知道她媽媽生她的時候有多失望,而她又多想變成男孩,接下來就不用問她為什么把頭發搞那么短。
如果一個抑郁分高且在“你是否有自殺念頭”一題選了肯定答案的高富帥說,“我不了解我的父親,我7個月大的時候他們離婚了”,你就體諒高富帥也有理由抑郁,尤其當他還是個嬰兒時吃到的是乳汁和眼淚的混合食品;高富帥也有理由想死,尤其他的出生本身就不是愛的結果而帶著某種天然的“非法”性。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寄養史。高校中有自殺風險的十類高危人群中,一類就是有寄養經歷的,而這一項往往被人忽略。通常來說,寄養發生的時間越早,持續的時間越長,長大后不開心的可能就越大。給祖父母養也是寄養,沒有證據表明祖父母養大的孩子就會比給別的寄主養大的孩子略好。小鴨子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若是人類飼養員,它就認人作父。但人類不這么干。母親本來是天然客體,如果天然客體不能親自養育孩子而由其他替代性客體養育,孩子能否與這個替代性客體建立親密關系基本是老天說了算。所以很多養育只是讓孩子活了下來,但是從心理上屬于無效養育。心理上沒被養育過的意義在于,他沒學過怎么建立親密關系,沒學過愛,所以他將很難得到幸福,除非他是天生會愛人的不世奇才。
寄養發生在6歲以前,在我看來就應該算是“原罪”。如果是3歲以前,甚至1歲以前,假如這個孩子長大以后心理出現問題,幫助他就會很難,甚至完全幫不到。在孩子眼里,他被最該愛他的人拋棄了。怎樣才能讓他相信自己是有價值、可愛的人?喬布斯一輩子都在證明這個,我不知道他到末了相信了沒有。
我注意到一個班長,全班29人,實到28人,他還是覺得班級缺乏凝聚力,很自責。后來在約談高分學生時見到了他,我一點也不奇怪。追問下,他抱怨起大學同學和高中不一樣,各顧各的,似乎對班級活動,對他這個班長不是那么熱心,他也慢慢心寒下來。他說一出生就被送到爺爺奶奶家養,直到上初中才回到父母身邊。在高中,他是學校里一呼百應的人物。現在,在離家千里外的北京,他日夜渴念的是友誼,以他為中心的友誼。
有個聲音酥甜的南方女生,坦承同學關系不好,有人在群里說她虛偽,裝純,勾引男生。她的父母算是有錢的,在另一個城市做著不小的生意。她從小上的是全托管的貴族學校,后來父母又把她送到北京念書,住過親戚家,還有幾年住在老師家里。我相信同學說她的那些,但不如此她沒有別的路。她是那樣長大的,像一條喪家犬,她只是裝得像一條家犬,以便得到一些家犬的對待。
還有一個姑娘,上邊兩個姐姐,下邊一個弟弟,父母都是沒有文化的打工者。這對夫妻在城市里每生下一個女兒,都會堅持撫養到5歲,然后送回老家給爺爺奶奶帶,只有兒子一直帶在身邊。最小的女兒也在5歲時,由從小生活的大都市被拋到了農村。她水土不服渾身出了很多疹子,疹子爛了,腿疼得走不了路,她淚眼婆娑望著奶奶說“婆婆抱我”,奶奶說,“婆婆老了,抱不動你,自己走吧。”病越來越重,媽媽終于來抱她了,只是把她留在身邊一年又送回村子,比起兩個姐姐,她算是賺到了。今年她18歲,因為人際問題尋求心理幫助。
這個冬天還沒過去的時候,長大了的留守兒童終于批量地走進了我的咨詢室。雖然早知道有這么一天,但真見面時還是相見恨早。曾有同行預言,要不了多久,前留守兒童會像悲傷的潮水漫過大學心理咨詢室的屋頂。如果是真的,我并不怕這個結局,我甚至期盼著它的發生,至少在大學里,心理咨詢對學生是免費的。但我嚴重懷疑有多少留守兒童最終能跨越無效養育的漫漫長途抵達某一個大學。
(作者系林紫心理機構北京中心副主任咨詢師)